荷曼·柯赫提示您:看后求收藏(350中文350zw.com),接着再看更方便。
我服了药。开始那几天没什么反应,附的说明书上也是这样写的,几周后才会显示出效果,可我还是注意到了,克莱尔在过了头几天之后,就开始用异样的眼光看我了。
“你感觉如何?”她一天问我好几次。我总是回答:“挺好。”这不是在说谎,我是真的感觉很好。我很享受这种改变,尤其是再也不用每天站在讲台前了:那么多颗脑袋望着我,一整节课,然后下一节课又来一批新的,周而复始,一节接一节。没有站过讲台的人是不会明白的。
过了还不到一周,比事先说的提前了,那些药渐渐开始起作用了。我没料到会这样。我害怕过,最怕的就是这药会产生我自己察觉不到的效果——改变人个性的效果。这就是我最大的担忧:我的个性会遭到侵犯。虽然对我周围最亲密的人来说,也许我会变得让他们更容易忍受一些,但是不知在何处,在路上我就会迷失自己。我读过药品说明书,里面坦白地提过一些令人相当不舒服的副作用。如果只是“恶心”“皮肤干裂”和“胃口下降”,或许人们还能活下去,可里面还提到了“焦虑不安”“呼吸急促”和“记忆力衰退”。“这真是好多记重锤啊,”我对克莱尔说,“我会服药,因为我别无选择。但是你得向我保证,如果发现情况不对,你得立刻提醒我。比如,如果我变得健忘或者行为古怪,你得跟我说,然后我就即刻停药。”
可我的担忧似乎并没有道理。那是一个周日的下午,在我服完第一批剂量的药之后大约五天,我躺在客厅的沙发上,腿上放着内容特别丰厚的周六报纸特刊。透过玻璃拉门我向花园里看,刚好开始下雨。本来是那么蔚蓝的一片天,还有白云,现在竟然刮起大风来。我得在这儿补充一下,我的家,我的客厅,还有最主要的是我在这座房子、这间客厅里存在的事实,在过去几个月里经常使我感到恐惧。这种恐惧,与许多其他人在这屋子里存在,以及我在可与此相比的其他房子和客厅里的存在,有直接的关系。尤其是当晚上夜幕降临时,当每个人——说得通俗点——都“在家”时,这种恐惧很快就会占上风。躺在沙发上,我的视线可以穿过灌木丛和树枝,辨认出街对面闪着灯火的窗户,不过很少看得清那儿是否真的有人,但是亮灯的窗户暴露了他们的存在——正如我家亮着的窗户暴露了我的存在一样。请不要误解,我不是害怕人本身,不是怕人这个物种,置身于人群中时,我并不会感到低落和压抑。我也不是那种在舞会上与世隔绝、谁都不愿与其交谈的怪物,反正无论有没有人跟他说话,他的肢体语言都一样没有变化。不,不是这些,是别的。跟人们在他们的客厅里的有限的存在有关,在他们的房子里、小区里,在他们的包括街道在内的区域里,这里的一条街机械地通向另一条街,一个广场跨过一条街机械地与另一个广场相连,诸如此类。我有时候晚上就这样躺在我们的客厅的沙发上,想着这样的一些事。然后会自己告诫自己,不该想这些事,尤其不要想得太远了,但是从未成功过。我还是一直想这些事,直到尽头,直到最终的结局。到处都有这样的人,我想,在同一时刻也躺在相似的客厅里的沙发上。马上他们就上床了,来去翻滚几下,或者对自己说点好听的。或者他们固执地沉默,因为刚刚吵完架,两个人谁也不想先服软认输。然后灯灭了。我想到时间,逝去的时间,为了更精确地了解,一个小时究竟能有多么无穷无尽、无边无际,多久、多黑、多空。这样想的人,只有光年才能把他吓倒。我想到广大的人群。不是人口过多,或者污染,或者未来还有没有足够的食物供给所有人等方面,而是仅仅想到人群本身,现在到底是三百万还是六十亿?有没有什么特定的意义?一想到这里,心里就立刻有一种不适感蔓延开来。我想,这个世界上的人并不一定是太多,而只是很多。我想到我班级里的学生。他们个个都处在“被迫”中:一旦被生到这个世上,他们就必须继续前行,就必须走完这一生,而在这个过程中,连一个小时都有可能让人难以忍受。他们必须找工作、结婚、生子,他们的孩子也得在学校里上历史课,即使不是由我教。站在某种角度来看,只能看到人类的存在,而无法再辨认出个体。是这,让我感到压抑。撇开我腿上一直没被阅读的报纸不说,从我的外部来看,别人不一定能察觉。“你想来杯啤酒吗?”克莱尔问道,手上拿着一杯红葡萄酒走进客厅。我现在得说“嗯,好的”,并且不能让我的声音听起来太怪异。我很怕自己的声音听起来会像刚刚醒来还没开口的人一样,或者就是像一个古怪声音,不是我的,一个吓人的声音。克莱尔就会扬起眉毛问:“有事吗?”而我当然会否认,会摇头,可是会因为摇得太猛而恰恰把我自己给出卖,并且还用古怪的、吓人的、与我本来的声音大相径庭的唧唧的尖声回答:“不,没事。会有什么事呢?”
然后呢?然后克莱尔就会走过来,坐到沙发上,用手拉起我的手,很可能还会用一只手抚上我的额头,像看看一个孩子是否发烧似的。这就来了。我知道,通向正常的大门完全敞开着。克莱尔会再问一遍是不是真的没事,而我就会再次摇摇头,不过不会太猛。开始她还会有点担心,不过很快就会没事了:毕竟我的反应确实正常,我的声音不再尖锐,对她的问题也能轻松对答。不,我只是自己在胡思乱想。想什么?我已经不知道了。嘿,你知道你坐在这儿,报纸放在腿上,已经有多久了吗?一个半,也许两个小时了!我一直在想花园的事,也许在我们的花园里建一个小房子会是个不错的主意。保罗……嗯?人们不会光想花园想一个半小时。是的,当然不会,我是说,也许我在前一刻钟里想的是我们的花园。但是在那之前呢?
在这个周日的下午,在我和校心理专家的谈话后一周的下午,我第一次看向花园,什么别的事都不想。我听到克莱尔在厨房里忙,嘴里还跟着广播哼着个旋律,是一首我不知道的歌,但是里面不停地重复出现“还有我的小花朵”。
“你笑什么?”不一会儿,她一手拿着一个杯子走进客厅,问道。
“就笑笑。”我说。
“这是什么意思,就笑笑。你真得看看自己的样子,呆呆直视的样子,好像刚刚皈依的薄伽梵,近乎极乐的状态。”
我看着她,感到一种惬意的温暖,像盖着鸭绒被一样。“我刚刚在想……”我刚准备开始,忽然又想到了别的事上。我本想说再要一个孩子之事。在过去几个月里,我们都没有提起这个话题。我想到年龄差的问题,最好是不要超过五岁。这也就是说,要么现在,要么就彻底不要了。可是尽管如此,在我内心深处还有一个声音在说,现在这时候不合适,也许再过几天,就是不要在这个周日的下午,在药效刚刚开始发挥出来的时候。
“我刚刚在想,在我们的花园里再建一个小房子应该不赖吧。”我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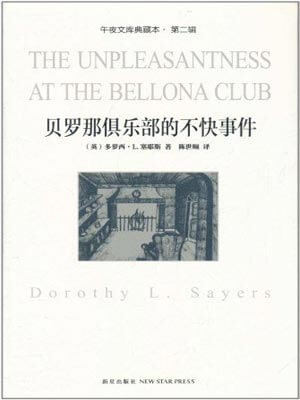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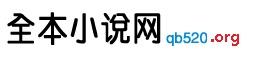
![[陆小凤]士子风流](https://image.51jpg.com/645/645406/645406s.jpg)