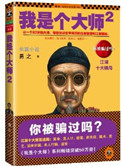斯蒂芬·金提示您:看后求收藏(350中文350zw.com),接着再看更方便。
一九八五年五月二十九日下午,贝弗莉·马什在纽约州上空又笑出声来。她赶紧用双手捂住嘴巴,生怕别人觉得她疯了,但就是停不下来。
我们那时也常常笑,她想,这又是一个回忆,一道黑暗中的光。尽管我们一直处在恐惧中,却依然止不住想笑,就像现在一样。
坐在她旁边靠走道那个座位的是一个留着长发的年轻男人,长得很好看。班机两点半从密尔瓦基起飞之后(到现在已经快两个半小时了,中途在克里夫兰和费城停留),他已经好几次向她投来爱慕的眼神,但很尊重她,知道她显然不想说话。两人曾经交谈过几句,但她的回答总是客气而简短。年轻男人于是打开手提袋,拿出一本罗伯特·勒德拉姆<a id="z53" href="#bz53">53</a>的小说读了起来。
这会儿他合上书,手指卡在读到的地方,关切地问:“你还好吧?”
贝弗莉点点头,试着摆出严肃的表情,但又忍不住笑了。男人微微一笑,显得困惑而好奇。
“没事。”她说,再次想让自己严肃起来,却还是没用。她越想严肃,脸就越不受控制,就像从前一样。“我只是忽然想到自己连搭的是哪一家航空公司的班机都不晓得,只记得机、机侧有一只大鸭、鸭子——”但这念头太荒唐了,让她开始哈哈大笑。周围乘客纷纷转头看她,有些人还皱起了眉头。
“共和。”年轻男人说。
“什么?”
“你现在在天上,以七百五十公里的时速腾云驾雾,这都是共和航空的功劳。椅背置物袋里的KYAG手册是这么写的。”
“KYAG?”
年轻男人从置物袋里抽出一本手册(封面确实有共和航空的商标),里面有逃生门的位置、飘浮设备的位置、氧气罩使用说明和坠机滑梯逃生姿势。“Kiss-your-ass-goodbye,滚蛋手册。”他说,这回两人都哈哈大笑。
贝弗莉忽然想,他真的很好看。这是个新想法,有恍然大悟的味道。人在睡醒之际开始有一点意识时,常常会察觉这种事。他穿着套头毛衣和褪色的牛仔裤,深金色的头发用皮绳系在脑后,让她想起自己童年扎的马尾。她心想:我敢说他的老二肯定和大学生一样清新温柔,长度够用,又不会粗得傲慢。
她又笑了,完全克制不住。她发现自己连手帕都没带,没办法擦拭笑到流泪的眼睛。想到这一点让她笑得更厉害了。
“你最好节制一点,不然空乘会把你扔下去。”年轻男人正色道,但她只是摇头大笑,笑得腰和肚子都痛了。
他递给她一条干净的白手帕。她接过来用了。不晓得为什么,但这么做总算让她找回了自制,但还是无法立刻停止,只是变成了微弱的抽搐和喘息。她不时想起机身上的大鸭子,立刻又是一阵咯咯的笑声。
过了一会儿,她将手帕还给他,说:“谢谢。”
“天哪,女士,你的手怎么啦?”他握着她的手关切地问。
她低头看见自己指甲断了,是她将梳妆台推倒在汤姆身上时弄断的。想起这事让她心中一痛,比指甲受伤还严重。她立刻止住笑容,将手从对方手中抽走,不过动作很轻。
“我在机场被车门夹到了。”她说,想起自己如何为了汤姆对她所做的事而撒谎,为了父亲留在她身上的瘀青而撒谎。这是最后一次吗?是她最后的谎言?是的话该有多好……简直好得不可思议。
她脑海中浮现一个画面,一名医生走进病房对癌症晚期的病人说:X光显示肿瘤在缩小,我们也不晓得原因,但就是这样。
“那一定疼得要命。”年轻男人说。
“我吃了阿司匹林。”她说着又翻开机上杂志,但对方可能发现她已经翻阅过两次了。
“你的目的地是哪里?”
她合上杂志,微笑着对他说:“你人真的很好,但我不想聊天,可以吗?”
“好吧,”他报以微笑,“不过,到了波士顿之后,你要是想为了机侧的大鸭子喝一杯,我请客。”
“谢谢你,但我要赶另一班飞机。”
“老天,我早上读的星座运势有这么不准吗?”他重新翻开小说,“不过,你的笑声很好听,很容易让男人爱上你。”
她又翻开杂志,但发现自己一直盯着残缺不全的指甲,而不是介绍新奥尔良景点的文章。有两根指甲底下有紫色的瘀血。贝弗莉在心里听见汤姆站在楼梯井的位置对她大吼:“我要杀了你,贱人!
你他妈的贱人!”她打了个冷战。在汤姆眼中,她是贱人。在那群女裁缝眼中,她是贱人。她们在大秀之前犯下大错,搞砸了贝弗莉的作品。但在汤姆和可恶的女裁缝闯进她生命之前,她在父亲眼中早就是贱人了。
贱人。
你这个贱人。
他妈的贱人。
贝弗莉闭上眼睛。
之前逃离卧室时,她的一只脚被香水瓶碎片割伤了,这会儿比手指还要痛。凯给了她一个创可贴、一双鞋和一张一千美元的支票。早上九点一到,她立刻去水塔广场的芝加哥第一银行兑现了。
尽管凯再三反对,她还是在空白打字纸上画了一张千元支票。“我曾经读到银行只要是支票都得收,不管写在什么上头。”她对凯说,但声音似乎来自别处,可能是其他房间的收音机吧,“有人就曾兑现过一张支票,是写在炮弹上的。我想我是在《百科事典》里读到的。”她顿了一下,露出不安的笑。凯严肃地望着她:“如果我是你,就尽早兑现,免得汤姆想到要冻结账户。”
她不觉得累(但她知道自己现在还能保持清醒,完全是靠意志力和凯准备的黑咖啡),昨晚的经历好像梦境一般。
她还记得三名青少年跟在她后头大叫、吹口哨,但不太敢靠近。她记得在路口看见7-11便利商店招牌的灯光洒在人行道上时,那份如释重负的感觉。她走进便利商店,让那个满脸青春痘的店员看她旧上衣里面,说服他借给她四十美分打电话。这不难,反正她本来就穿成那样。
她先打给凯·麦考尔,凭记忆拨的号码。电话响了十几声,她开始担心凯跑去纽约了。就在她打算挂掉时,凯终于接起电话,用昏昏欲睡的声音呢喃道:“不管你是谁,最好是有要紧事。”
“凯,我是贝,”她说,迟疑片刻,她决定豁出去了,“我需要帮忙。”
电话那端沉默了半晌,之后凯再度开口,语气完全清醒了:“你人在哪里?出了什么事?”
“我在斯特里兰大道和某条街拐角的7-11。我……凯,我离开汤姆了。”
凯立刻激动地回答:“太好了!你总算离开他了!耶!我去接你!那个浑球!狗屁!我会开他妈的奔驰车去接你!还要请四十人大乐队庆祝!还有——”
“我会搭出租车。”贝弗莉说,汗湿的掌心里握着另外两枚十分硬币。她看了便利店后头的圆镜子一眼,发现青春痘店员正全神贯注、如痴如醉地盯着她的屁股看。“但我到了之后,你得帮我付钱。我身上没钱,一毛都没有。”
“我会给司机五美元当小费,”凯高声说,“这真是尼克松下台之后最棒的消息了!小姑娘,你马上给我过来。还有——”她顿了一下,等她再开口时,语气变得很严肃,而且充满关爱,让贝弗莉差点掉下泪来,“谢天谢地,你终于做到了,贝。我是说真的,谢天谢地。”
凯·麦考尔之前是设计师,嫁了个有钱人,离婚后钱更多了。她在一九七二年发现了女权主义运动,大约三年后认识了贝弗莉。当时她备受欢迎,同时也充满争议,人们指责她靠着沙文主义的陈腐法律榨干了她那从事制造业的丈夫,才跑来拥抱女权主义。
“听他们放屁!”凯有一回这么对贝弗莉说,“说那些话的人没一个要和萨姆·查柯维兹上床。
老萨姆的口头禅就是冲个两下爽爽射一发。他只有一次超过七十秒,就是在浴缸里打手枪那一回。我又没有红杏出墙,只是请他事后埋单而已。”
她写了三本书,一本讲女性主义和职业妇女,一本讲女性主义和家庭,另一本讲女性主义和灵性。
前两本还挺畅销的,但第三本书出版三年后,她就有点走下坡路了。不过,贝弗莉觉得她其实松了一口气。她的投资收获颇丰(她有一次对贝弗莉说:“幸好女性主义和资本主义不是死对头。”),如今是个有钱的女人,在城里有独栋公寓,在乡下有别墅,还有两三个男宠。那几名壮汉在床上和她旗鼓相当,但打起网球就不是对手。“只要他们球技一进步,我就甩了他们。”她说。凯显然在开玩笑,但贝弗莉一直觉得搞不好是真的。
贝弗莉叫了辆出租车。车到之后,她提着行李箱挤进后座,将凯的地址交给司机,庆幸终于摆脱了便利店店员的目光。
凯就站在车道尽头等她。她身上穿着法兰绒睡袍,罩着貂皮外套,粉红色绒毛拖鞋上缀着大毛球。
不是橘色毛球,谢天谢地,否则贝弗莉可能又要对着暗夜尖叫了。到凯家的这一路很怪:往事不断回到她脑海中,回忆迅速而清晰地涌入,令人害怕,仿佛有人驾驶巨型推土机在她脑海中挖掘连她自己也不知其存在的墓园,只不过挖出来的不是尸体,是人名,她多年未曾想起的人名,例如本·汉斯科姆、理查德·托齐尔、格蕾塔·鲍伊、亨利·鲍尔斯、埃迪·卡斯普布拉克……还有威廉·邓布洛。尤其是威廉,他们那时和其他孩子一样叫他结巴威,这是小孩间的直率,也是残忍。贝弗莉当时觉得他长得好高、好完美(在他还没开口说话之前)。
人名……地点……发生过的事。
回忆时冷时热,她想起排水道里的声音……还有血。她尖叫,他父亲揍了她。她父亲——汤姆——
她快哭了……凯正在付钱给司机,给的小费多得让对方惊呼:“女士,真是谢谢您!哇哦!”
凯带她进房,让她冲澡,然后给她一件浴袍,帮她泡咖啡,检查她身上的伤,用红药水涂抹她脚上的割伤,然后贴上创可贴。她在贝弗莉的第二杯咖啡里倒了很多白兰地,逼她喝得一滴不剩。之后,她为自己和好友各弄了一块半熟的牛排,还煎了新鲜蘑菇当配菜。
“好了,”她说,“到底出了什么事?我们需要叫警察,还是把你送到雷诺蹲牢房?”
“我没办法多说,”贝弗莉说,“讲起来太荒谬了,但主要是我的错——”
凯重重一拍漆木餐桌,木头发出有如小口径手枪射击的声音,吓了贝弗莉一跳。
“我不准你这么说。”凯说。她双颊泛红,棕色眼眸闪闪发亮。“我们认识几年了?九年?十年?我要是再听到你说是你的错,我就要吐了。这一回不是你的错,上回不是,再上一回也不是,从来不是你的错。你知道吗?你的朋友几乎都认为他迟早会让你全身打石膏,或是杀了你。”
贝弗莉瞪大眼睛望着好友。
“如果发生那种事,那应该算你的错,竟然任由它发生。不过你终于离开了,谢天谢地。你现在指甲断了一半,脚也割伤了,还有皮带的抽痕,别跟我说是你的错。”
“他没有用皮带。”贝弗莉说。她又不自觉地撒谎了……因为羞愧脸颊不由自主地红了。
“既然已经离开汤姆了,也不必说谎了。”凯柔声说。她凝视着贝弗莉,眼神里充满关爱。贝弗莉垂下眼睛,感觉咸咸的泪水流进了喉咙。“你想骗谁啊?”凯问,语气依然温柔。她隔着桌子握住贝弗莉的双手。“墨镜、高领衫和长袖……你可能骗得了一两个买家,但骗不了朋友,贝,骗不了爱你的人。”
听到这里,贝弗莉哭了,哭了很久,很伤心。凯握着她的手。上床前,贝弗莉将能说的经过都告诉了凯。她童年在缅因州德里镇长大,那里有个朋友打电话给她,提醒她很久之前许下的承诺。他说实现诺言的时候到了,她会回来吗?她说会,接着汤姆就开始惹麻烦了。
“什么承诺?”凯问。
贝弗莉缓缓摇头:“我不能说,凯,虽然我很想。”
凯思忖片刻,点点头说:“好吧,也对。等你从缅因州回来,打算怎么处置汤姆?”
贝弗莉愈来愈觉得自己去了德里就回不来了,因此只回答:“我会先来找你,我们一起商量对策,如何?”
“当然好,”凯说,“这是承诺吗?”
“只要我回得来,”贝弗莉心平气和地说,“就会做到。”说完她紧紧抱住凯。
她拿着凯的支票兑来的钱,踩着凯的鞋,搭乘北上密尔瓦基的灰狗巴士班车,因为她怕汤姆会去奥黑尔机场找她。凯陪她去银行和车站,途中不停地劝阻她。
“奥黑尔到处都是安全人员,”她说,“你不用担心他。只要他靠近你,你就放声尖叫,叫到脑袋掉下来为止。”
贝弗莉摇摇头:“我想彻底避开他,所以只能这么办。”
凯眼神锐利地望着她:“你怕自己会被他说动,对吧?”
贝弗莉想起他们七个人站在河中央,想起斯坦利手里那块可乐瓶碎片映着阳光闪闪发亮。她想起斯坦利用碎片轻轻划破她掌心时的刺痛,想起他们手牵手围成一圈许下承诺:要是它再出现,他们都会回来……回来彻底杀死它。
“不是,”她说,“在这件事上我不会被他说服,但他可能会伤害我,不管有没有安全人员。你没看到他昨晚的样子,凯。”
“我已经看腻他了,”凯皱着眉头说,“那浑球只是披了一张人皮罢了。”
“他疯了,”贝弗莉说,“安全人员可能拦不住他。搭车更好,相信我。”
“好吧。”凯勉强说道。贝弗莉觉得很有趣,凯显然对不会有冲突和大吵大闹感到很失望。
“支票记得快点兑现,”贝弗莉又叮咛一次,“免得他想到冻结账户。你知道他一定会的。”
“没问题,”凯说,“要是他敢这么做,我就拿着马鞭去找这混账,叫他给老娘爽一下。”
“离他远一点,”贝弗莉厉声说,“他很危险,凯,相信我。他就像——”像我父亲,她颤抖的双唇原本要这么说,结果却只吐出:“就像野人。”
“好吧,”凯说,“放轻松,亲爱的,去实现诺言吧,不过记得想一想你的未来。”
“我会的。”贝弗莉说,但她撒了谎。她有太多事情要想,比如她十一岁那年夏天发生的事。比如给理查德·托齐尔示范怎么让溜溜球睡觉。比如下水道里传来的声音。还有她看见的那个东西,那个可怕至极的东西。直到她站在隆隆作响的灰狗巴士的银色车身旁最后一次和凯拥抱,她的心还是不太想让她看见那个东西。
机身画着大鸭子的飞机开始从波士顿上空缓缓下降,她的心思再度转向那件事……转向斯坦利·乌里斯……那张明信片上的匿名诗……那些声音……以及她和那东西对看的那几秒,感觉没有尽头的那几秒。
她低头望向窗外,心想德里有一个恶魔在等她,汤姆的坏和那东西比起来根本不算什么。唯一的好消息是威廉·邓布洛也会在……很久很久以前,一个名叫贝弗莉·马什的十一岁女孩曾经爱着威廉·邓布洛。她还记得那一张背面写着情诗的明信片,记得她曾经知道作者是谁。她现在不记得了,也不记得那首诗写了什么……但她想应该是威廉写的。没错,可能是结巴威。
她忽然想起跟理查德和本去看恐怖电影的那一天。那是她第一次约会。她是和理查德开玩笑的,那时她在街上都用这招保护自己。但她心里其实很感动,很兴奋,又有一点害怕。那真的是她第一次约会,虽然对象有两个,不是一个。理查德付了钱,就像真正的约会一样。之后他们被那几个混混追……
下午他们在荒原玩……威廉·邓布洛带了另一个孩子过来,她忘了他的名字,但记得威廉看她的眼神,还有蹿过她内心的电流……那道电流温暖了她整个身躯。
她记得自己穿上睡袍到浴室洗脸刷牙时,正在回想这些事情。她心想晚上一定很难睡着,因为有太多事情要想……而且要用好的方式想,因为他们看起来是好孩子,可以一起厮混,甚至值得信任。
那真好。那真的……呃,像是天堂。
她一边想着这些事情,一边拿起毛巾凑近洗手台准备接点水。那声音忽然从排水管里传了出来:
“救命……”
贝弗莉吓得后退几步,干毛巾掉在地上。她微微摇头,仿佛想甩掉那声音,接着再度凑向洗手台,好奇地窥探排水管。她家是四房公寓,浴室在最里面。她隐约听见电视里在播西部电影。播完之后,她父亲通常会转到棒球或摔跤节目,然后在安乐椅上呼呼大睡。
浴室壁纸图案是青蛙卧在莲花上,画得很丑。底下的灰泥鼓胀起来,搞得壁纸图案也凸起歪斜。
墙上到处是水渍,有几处壁纸甚至剥落了。浴缸爬满锈斑,马桶座龟裂了,洗手台上方一个四十瓦的灯泡插在陶瓷座上。贝弗莉还记得(但印象很模糊了)那里之前有灯罩,但几年前破了,之后就没再补上。塑料地板的图案已经褪色,只有洗手台下方的还看得见。
这间浴室不是什么令人开心的地方,但贝弗莉从小到大用习惯了,根本不会注意它的模样。
洗手台也沾满水渍,排水管口就是中间嵌个十字的圆环,直径约五厘米。之前本来有镀铬粉饰,但也早就消失了。橡皮塞子用链子拴着,缠在冷冷的弧形龙头上。排水口和水管一样黑不见底。贝弗莉凑过去,头一回闻到底下传来一股淡淡的臭味,有点像鱼腥味。她嫌恶地微微皱起鼻子。
“救命——”
她倒抽一口气。是声音没错。她之前以为是管子震动……或她自己的想象……或是电影的后遗症。
“救命,贝弗莉……”
贝弗莉觉得忽冷忽热。她刚才把头发上的橡皮筋拿下来了,此刻头发有如闪亮的瀑布般披在肩上。
发梢似乎僵住了。
在意识到自己想要回应之前,她已经凑到洗手台边,稍微压低声音说:“哈喽,里面有人吗?”
排水管里的声音感觉很稚嫩,可能是刚学会说话的小婴儿。贝弗莉虽然手臂起了鸡皮疙瘩,头脑却在寻求合理的解释。她家住的是集合公寓,有五户,他们住在一楼的后面。也许是某一家的小孩在玩,对着排水管说话,声音走调了……
“有人在?”她对着浴室的排水管问,声音稍微大了一点。她忽然想到要是父亲这时走进来,肯定会觉得她疯了。
排水管里没有人回应,但难闻的味道似乎变重了,让她想起荒原的竹林和竹林后方的沼泽,想起凝滞辛辣的烟气和想让你鞋子和脚分家的黑泥。
重点是,公寓里没有小婴儿。本来,崔蒙特家有一个五岁的小男孩和两个小女孩,后者分别是三岁和六个月大。崔蒙特先生原来在崔克大道的鞋店工作,但前阵子失业了,缴不出房租,于是就在暑假前不久,他们全家坐上崔蒙特先生老旧生锈的别克轿车,从此消失无踪。斯奇普·波尔顿住在二楼的前面,但他已经十四岁了。
“我们大家都很想见你,贝弗莉……”
贝弗莉伸手按着嘴巴,吓得睁大了眼睛。那一瞬间,就那么一瞬间,她感觉自己看见里头有东西在动。她忽然发现,自己的头发分成两大绺垂在两边,发梢靠近(非常靠近)排水口。她本能地直起身子,将头发拉远。
她看了看左右。浴室的门紧闭着,电视声隐约可闻,夏延·博迪正在警告坏人弃械投降,免得自找苦吃。浴室里只有她一个人。当然,还有那个声音。
“你是谁?”她压低声音对着洗手台说。
“我是马修·克莱门茨,”那声音轻轻说,“小丑把我抓到水管里,我死了,它很快就会来抓你了,贝弗莉。还有本·汉斯科姆,还有威廉·邓布洛,还有埃迪——”
她举起双手捂住脸颊,眼睛不断睁大、睁大。她觉得身体愈来愈冷。那个声音开始变得喑哑苍老……不过依然带着腐败的欢愉。
“你会和好朋友一起在这里飘,贝弗莉,我们都在这里飘。跟威廉说乔治向他问好,跟威廉说乔治很想他,但很快就会见到他了。跟他说乔治某天晚上会在衣柜里,眼睛缠着一根钢琴丝,跟他说—
—”
那声音忽然开始打嗝,一个亮红色的泡泡从排水管里冒出来,破了,溅得肮脏的陶瓷洗手台满是血滴。
喑哑的声音愈说愈快,而且不断变化。一会儿是小孩子的声音,一会儿是少女的声音,接着又变成(真可怕!)贝弗莉认识的女孩……维罗妮卡·格罗根。但维罗妮卡已经死了,被人发现陈尸水沟—
—
“我是马修……我是贝蒂……我是维罗妮卡……我们都在这里……跟小丑一起……还有怪物……还有木乃伊……还有狼人……还有你,贝弗莉,我们在这里和你做伴,大家一起飘,一起变形……”
排水管突然喷出一股鲜血,洒在洗手台、镜子和青蛙莲花壁纸上。贝弗莉吓得大叫,声音又急又尖。她往后退去,撞到门又往前弹。她抓住门把将门打开,冲到起居室,她父亲正要起身。
“你他妈的怎么回事?”他皱着眉头问。家里今晚只有他们两个,贝弗莉的母亲在格林餐厅工作,下午三点到晚上十一点上班。格林餐厅是德里镇最好的餐厅。
“浴室!”她歇斯底里地大喊,“浴室,爸爸,浴室里——”
“有人在偷窥你吗,贝弗莉?”他用力抓住女儿的胳膊,指甲掐进了肉里。他面露关切,但却像要吃人一样可怕,丝毫不会给人安慰。
“不是……洗手台……洗手池里……那个……那个……”她话还没说完就歇斯底里地哭了出来。她的心脏在胸膛里剧烈跳动,感觉就要窒息了。
艾尔·马什露出“天哪,现在是怎样”的表情,将女儿甩到一旁走进浴室里。他在里头待了好久,贝弗莉又开始害怕。
接着,她听见了父亲的咆哮:“贝弗莉,你这个小鬼,给我过来!”
她不可能抗命。就算站在悬崖边,父亲要她跳下去(马上跳,小姐),她也会下意识照做,在理智阻止她之前就跨出那一步。
浴室的门开着。她父亲站在里面,身材魁梧,遗传给贝弗莉的赤褐色头发已经开始变得稀疏了。
他还穿着灰色工作裤和灰衬衫(他在德里镇医院当清洁工),两眼狠狠瞪着贝弗莉。他不烟不酒,也不寻花问柳。我有家里的女人就够了,他曾经这么说,脸上闪过一抹神秘的微笑。那抹微笑没有让他神采飞扬,反而显得他的脸更加阴森。就像浮云匆匆掠过,在砾石地面留下一道阴影。她们照顾我,当她们有需要,我就照顾她们。
他看见贝弗莉走进浴室,便问:“这里面他妈的是怎么搞的?”
贝弗莉觉得喉咙像被石片划了一下,心脏狂跳。她觉得自己就要吐了。镜子上有几道长长的血痕。
洗手台上方的灯泡上也有血。她闻得到血被四十瓦灯泡烤熟的味道。血从陶瓷洗手台侧面流下来,滴在塑料地板上形成大圆点。
“爸爸……”她哑着嗓子低声说。
他满脸嫌恶(他经常如此)地转过头去,开始在血迹斑斑的洗手池里洗手,洗得轻松自在。“拜托,小姑娘,你说话啊!你刚才把我吓死了。拜托你解释一下行吗?”
他站在洗手台前洗手,贝弗莉看见他的灰裤子贴着洗手台边缘,沾到了血。要是他的头碰到镜子(现在很近),血就会沾到他身上了。她喉咙里噎了一声。
她父亲关上水龙头,抓了一条沾了两滴血的毛巾开始擦手。她看着父亲,看他将血抹到粗大的指关节上和掌纹里,觉得自己就快晕倒了。她看见他指甲上沾着血,有如罪恶的印记。
“怎么样?我还在等你开口呢。”他将沾了血的毛巾扔回横杆上。
浴室里有血……到处都是……但她父亲却看不见。
“爸爸——”她不知道接下来会发生什么,但父亲打断了她。
“我很担心你,贝弗莉,”艾尔·马什说,“我感觉你好像永远长不大,成天跑来跑去,也不见你做家务。你不会煮饭,也不会缝纫,不是埋在书本的虚幻世界里,就是做白日梦,胡思乱想。我真的很担心。”
他说完忽然大手一挥,狠狠打在她屁股上。贝弗莉痛得大叫,眼睛盯着父亲。他粗浓的右眉毛上沾了一小滴血。我要是再看下去一定会疯掉,那就无所谓了,她心里隐隐想道。
“我真的很担心。”他说完又打了她,力道更重,打在胳膊上。贝弗莉痛得大叫一声,胳膊失去了知觉。明天那里一定会出现黄紫色的瘀青。
“非常担心。”他的拳头朝她腹部挥去,但在最后一秒钟停住了。她稍微松了口气,弯腰喘息,泪水涌进了眼眶。父亲冷冷地看着她,将沾血的双手插进裤口袋里。
“你该长大了,贝弗莉,”他说,语气变得慈祥而宽容,“不是吗?”
她点点头,脑袋阵阵抽痛。她默默地流着眼泪。要是她大声啜泣,像她父亲说的又开始“哭得像个小娃儿”,他可能就要好好收拾她了。艾尔·马什一辈子住在德里,只要有人问起,他都说自己死后也要葬在这里。有时就算没人问起,他也照说不误。他说他想活到一百一十岁。“我一点不良嗜好都没有,”他有一回对每个月替他理发的罗杰·奥雷特说,“没有理由不长命百岁。”
“好了,解释清楚吧,”他说,“快点。”
“我看到——”她喉头动了一下,感觉很痛,因为她喉咙很干,没有半点水分,“我看到一只蜘蛛,又大又黑。它……从排水管里爬出来,我……我想它可能爬回去了。”
“哦!”他对她微笑,仿佛很满意似的,“是吗?该死!你要是早点告诉我,贝弗莉,我就不会打你了。女孩子都怕蜘蛛。他妈的,你干吗不早说?”
他弯腰凑近排水管。贝弗莉咬紧下唇才没让自己出声警告……她心里有个声音在说话。很可怕的声音,不可能是她自己,一定是恶魔。只要它想,就让他被抓走吧,把他抓走,永远别让他回来。
她吓得躲开那声音。这种念头就算只在心中停留半秒钟,也会让她下地狱。
艾尔瞄了管口一眼,双手压在洗手台边缘的血迹上。贝弗莉拼命忍住,不让自己吐出来。她腹部被父亲殴打的部位隐隐作痛。
“我什么都没瞧见,”父亲说,“这几栋公寓很老了,贝,排水管就跟高速公路一样宽,知道吗?
我当年在那所老高中当工友,马桶三不五时就会有老鼠死在里头,把女学生吓得半死。”想到那些小女生大惊小怪的样子,他就觉得好笑,“通常发生在坎都斯齐格河上涨的时候。不过,自从新的排水系统修好之后,水管里就很少有野生动物了。”
他伸手搂住女儿,抱了抱她。
“好了,现在上床睡觉去,别再想了,好吗?”
她感觉到对父亲的爱。我绝对不会无缘无故打你,贝弗莉。她有一回被打之后大喊不公平,父亲这么告诉她。这么说当然没错,因为他心里是有爱的。他有时会整天陪她,教她做事情,跟她谈天说地或在镇上散步。每回他这么慈祥,贝弗莉都觉得自己的心快要被幸福淹没了。她爱他,很努力地去理解他有必要时时管教她,因为(就像他说的)那是他的天职。艾尔·马什说,女儿比儿子更需要管教。他没有儿子,贝弗莉隐约觉得是她的错。
“好的,爸爸,”她说,“我不会再想了。”
两人一起走进她的小卧室。她的右臂刚才被打了一下,现在痛得厉害。她回头望了一眼,看着沾了血的洗手台、镜子、墙壁和地板。她父亲用过的沾血毛巾歪七扭八地挂在横杆上。贝弗莉想:我怎么可能再踏进浴室一步?神哪,亲爱的神,求求你。我错了,我不该对爸爸有不好的想法,你可以惩罚我,我应该被惩罚。让我跌倒受伤吧,或是像去年一样,感冒了拼命咳嗽,甚至还吐了。但是求求你,神哪,明天早上让那些血消失吧,拜托拜托,好吗?神哪,好吗?
父亲和往常一样帮她盖好被子,轻吻她的额头。他在床边站了一会儿,贝弗莉觉得那就是他的站姿,甚至可以说是他存在的方式:身体微微前倾,两手插在裤口袋里(直到手腕),低头看着她,蓝色眼眸闪闪发亮,那张脸有如巴吉度猎犬的脸,写满忧郁。多年后,就算她早已不再想起德里,心中依然不时浮现一个男人坐在公交车上,或是手里拎着晚餐篮站在角落里的情形。她会看见身影,噢,男人的身影,有时出现在天色将暗之际,有时出现在晴朗风大的秋夜月光下,在水塔广场。男人的身影,男人的规矩和欲望。还有汤姆,当他脱去衬衫,站在浴室镜子前,身体微微前倾,开始刮胡子时,是多么像她父亲。男人的身影。
“我有时真的很担心你,贝。”他说,但语气已经不再困惑或愤怒。他温柔地抚摸她的头发,将她额头上的头发往后拨。
浴室里都是血,爸爸!她差点尖叫着说出来,你难道没看见?到处都是!甚至滴到洗手台上方的灯上烤干了!你难道没看见?
但她没有开口,而是默默看着父亲走出卧室,随手关上门,房间里一片漆黑。她睡不着,直到她母亲十一点半回来,电视都关了,她依然醒着,凝望着黑暗。她听见爸妈走进他们的房间,开始做爱,弹簧床发出规律的声响。贝弗莉曾经听见格蕾塔·鲍伊对萨莉·米勒说做爱跟火烧一样痛,好人家的女孩子绝对不会做(“男人最后会尿在你的小贝壳里。”格蕾塔说。萨莉大叫:“好恶心,我绝不会让男生对我这样。”)。要是真的像格蕾塔说的那么痛,那贝弗莉的母亲很会忍。有一两次,她听见母亲低声叫着,但似乎一点也不痛苦。
弹簧吱嘎声由缓而急,最后快得近乎疯狂,然后停止。房间安静了半晌,接着是低语声,然后是母亲走进浴室的脚步声。贝弗莉屏住呼吸,想听母亲会不会惨叫。
结果没有惨叫,只有水流进洗手池的声响,还有轻轻的泼水声,然后是水流进管子的咕噜声。很熟悉的声音。她母亲正在刷牙。不久,爸妈房间的弹簧床又吱嘎一声,她母亲回到了床上。
过了五分钟左右,她父亲开始打呼。
阴沉的恐惧夺走了她的心跳,扣住了她的喉咙。她发现自己不敢向右翻身,虽然那是她最爱的睡姿,因为她怕会有东西隔着窗户看她。她仰躺着,僵直得像把火钳,眼睛盯着铁皮天花板。最后(不晓得过了几分钟或几小时),她终于勉强睡着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