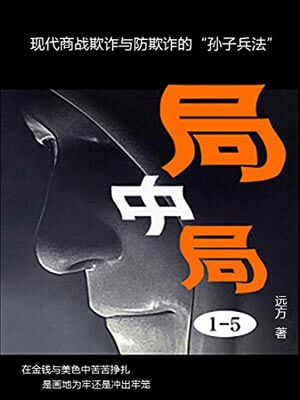第五章 (第5/5页)
加西亚·马尔克斯提示您:看后求收藏(350中文350zw.com),接着再看更方便。
兄弟俩同时看见了他。巴勃罗·维卡里奥脱下外套,搭在椅背上,亮出他的阿拉伯式弯刀。他们走出店门前,不约而同地在胸前画了个十字。克洛蒂尔德·阿门塔一把拽住佩德罗·维卡里奥的衬衫,朝圣地亚哥·纳萨尔高喊让他快跑,他们要来杀他了。她的喊声是那样急迫,将其他声音都压了下去。“一开始他吓坏了,”克洛蒂尔德·阿门塔告诉我,“不知道是谁在朝他喊,也不知道声音从哪儿传来。”不过,当圣地亚哥看见她时,也就看见了佩德罗·维卡里奥,佩德罗一把将克洛蒂尔德推倒在地,赶上了他的哥哥。圣地亚哥·纳萨尔此刻距离自己家还不到五十米,他往大门奔去。
五分钟之前,维多利亚·古斯曼在厨房里将全世界都已经知道的事告诉了普拉西达·利内罗。普拉西达是个坚毅的女人,绝不会让自己流露出一丝恐慌。她问维多利亚·古斯曼,是否提醒过她的儿子。维多利亚有意撒了个谎,回答说他下楼喝咖啡时自己还什么都不知道。就在那时,正在厅堂里擦地板的迪维娜·弗洛尔看见圣地亚哥·纳萨尔从临着广场的大门进了家,登上从沉船上卸下的楼梯往卧室去了。“真的是他,我看得清清楚楚,”迪维娜·弗洛尔告诉我,“他穿着白衣裳,手里拿着什么看不清,好像是一束玫瑰。”于是当普拉西达·利内罗向她追问起自己的儿子时,迪维娜·弗洛尔还劝她放心。
“他一分钟前上楼去了。”她说。
然后普拉西达·利内罗发现了地上的信,但是她没想拿起来看。那场混乱的悲剧过去很久之后,有人读给她时,她才知道那上面写了什么。她透过门缝,看见维卡里奥兄弟正朝前门跑来,手中举着明晃晃的刀。从她的位置能看见维卡里奥兄弟,却看不见自己的儿子,因为他正从另一个角度往大门跑。“我以为他们要冲进来杀人。”她对我说。于是她奔向大门,猛地将门关死。挂上门闩的时候,她听到圣地亚哥·纳萨尔的呼喊,接着是骇人的砸门声,但她以为儿子在楼上,正从自己卧室的阳台上喝骂维卡里奥兄弟。她跑上楼去准备帮他。
她关上大门时,圣地亚哥·纳萨尔还差几秒钟就能冲进来。他用拳头砸了几次门,然后赶紧转过身,准备赤手空拳迎接敌人。“跟他正面相对的时候,我吓了一跳,”巴勃罗·维卡里奥告诉我,“因为我觉得他的脸有平时的两倍大。”佩德罗·维卡里奥从右侧挥着长刀刺过来,圣地亚哥·纳萨尔抬手去挡这第一刀。
“婊子养的!”他骂道。
刀扎穿他的右手掌,一直刺入右肋,只留了刀把在外面。所有人都听到了圣地亚哥痛苦的叫喊。
“我的妈啊!”
佩德罗·维卡里奥抡着屠夫的铁臂抽出刀来,几乎在同一位置砍了第二刀。“奇怪的是,拔出刀来不见血,”佩德罗·维卡里奥向法官供认,“我至少砍了他三刀,但是一滴血也没溅出来。”挨了三刀之后,圣地亚哥·纳萨尔双臂交叉抱住腹部弯下了腰,发出一声牛犊似的呻吟,想要背过身去。巴勃罗·维卡里奥拿着弯刀站在他左侧,给他留下了背上的唯一一道伤口。一股血柱喷出来,浸湿了他的衬衣。“闻起来像他的气味。”巴勃罗·维卡里奥对我说。受了三处致命伤,圣地亚哥·纳萨尔又转过身面朝他们,倚在被他母亲闩死的大门上,不再做任何抵抗,仿佛只想尽一分力帮他们杀了自己。“他不再喊叫了,”佩德罗·维卡里奥告诉法官,“相反,我觉得他好像在笑。”于是兄弟两人继续把他抵在门上,轻而易举地轮流将刀捅进他的身体。他们发现恐惧的另一端是一片耀眼的静水,他们像是在水中浮游。他们听不见整个小镇的嘶喊,看不见所有人正因他们的罪行而瑟瑟颤抖。“我感觉像在骑马飞奔。”巴勃罗·维卡里奥说。但两个人很快就回到现实中,因为他们已经耗光了体力,却觉得圣地亚哥·纳萨尔似乎永远都不会倒下。“妈的,我的表弟啊,”巴勃罗·维卡里奥告诉我,“你都想象不到,杀一个人有多难。”为了一次做个了断,佩德罗·维卡里奥想对准圣地亚哥的心脏,但他几乎砍到腋窝上了,因为猪的心在那个位置。其实,圣地亚哥·纳萨尔没有倒下,只是因为他们的用力砍杀将他钉在了门上。绝望之际,巴勃罗·维卡里奥在他腹部横砍一刀,整副肠子一下涌了出来。佩德罗·维卡里奥也想来这么一刀,但因为恐惧手抖得厉害,一刀砍在大腿上。圣地亚哥·纳萨尔仍然倚着门站了一会儿,直到他看见阳光下自己那泛着蓝色的干净的肠子,才终于跪倒在地。
普拉西达·利内罗呼喊着到楼上的卧室找她的儿子。她蓦然听到不知哪里传来其他人的喊声,于是从朝向广场的窗户探出头,看见维卡里奥兄弟正往教堂跑去。在他们身后紧追不舍的,是举着猎枪的贾米尔·沙尤姆和一些没有带武器的阿拉伯人。普拉西达·利内罗觉得危险已经过去了。她走到卧室的阳台上,这才看见圣地亚哥·纳萨尔脸贴着地倒在大门外,挣扎着想从身下的血泊里站起来。他歪歪斜斜地直起身子,梦游般地迈步往前走,双手捧着垂下的肠子。
他走了将近一百米,围着自家的房子绕了一周,从厨房门进了屋。他头脑依旧清楚,没有绕远沿着大街走,而是从邻居家直穿过来。庞乔·拉纳奥、他的妻子和五个孩子,还不知道门外二十步远的地方发生了什么事。“我们听见喊声,”他妻子对我说,“还以为那是迎接主教的欢庆活动呢。”圣地亚哥·纳萨尔进门时他们正在吃早餐,只见他浑身浸满鲜血,手里托着一摊内脏。庞乔·拉纳奥告诉我,“我永远忘不了那股粪臭味。”不过,据他的大女儿佩罗·阿赫尼达·拉纳奥说,圣地亚哥·纳萨尔还保持着往常的仪态,踱着步子,他那张撒拉逊人的脸庞配上粗硬的鬈发,看上去比平时更加英俊。走过餐桌时他朝他们笑了笑,接着往前穿过卧室,一直出了后门。“我们都吓瘫了。”阿赫尼达·拉纳奥对我说。我的姨妈韦内弗里达·马尔克斯正在河对岸自己家的院子里给鲱鱼刮鳞,看见圣地亚哥·纳萨尔迈下旧码头的台阶,步伐坚定地往自己家走。
“圣地亚哥,我的孩子,”她对他喊,“你出什么事了?”
圣地亚哥·纳萨尔认出她来了。
“他们把我杀了,韦内姑娘。”他说。
他绊倒在最后一级台阶上,不过立刻又站了起来。“他甚至还把沾在肠子上的尘土抖落干净。”韦内姨妈告诉我。他从那扇自六点钟起就敞开的后门进了家,随后脸朝下倒在了厨房的地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