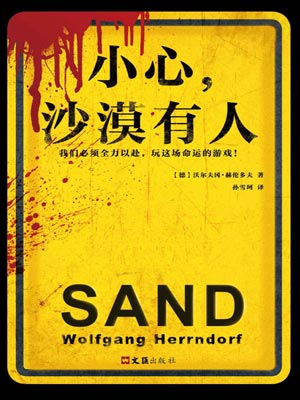郝海龙提示您:看后求收藏(350中文350zw.com),接着再看更方便。
云丛说:「这么想想确实没错。不过言归正传,说到我和廉警官,其实也没有那么熟。去年我爸带我一起去参加了一个慈善晚宴,他作为警界的代表出席了宴会,我爸和他聊了很多,顺便介绍了我们认识。不过现在看来,我爸在学术管理会的工作说不定会和廉警官有什么交集呢。」
之后我们每个人分享了一些自己过往的生活经历。后来听我的高中同学讲到他们上大学时的情形,感觉这有点像大学开学第一天的「卧谈会」。与在大陆上大学的同学相比,唯一的不同是,他们的卧谈会中几乎不可能出现异性。
杯中奶茶喝尽,据今年大陆的高考还有不到四天的时候,我们的大学生活已经开始了。
第二天我们再次在酒店共进早餐。我和怡年订的是上午的航班,餐后提前赶赴机场。梁炯订的是下午的航班,但说要先去给家人买点礼物,并没有与我们同行。童云丛则与我们告别,打车回家。
在回北京的飞机上,我和怡年再次把座位换到了一起。来香港的路上因为有考试要准备,我们配合无间,现在两人都成功通过了测试,心情彻底放松下来,我反倒觉得有些尴尬了。毕竟两年没有见面,很多事情不知该从何说起,何况在我内心深处,我俩的关系还残存着一缕暧昧。表白之前的暧昧让人觉得温暖幸福,表白被拒之后的暧昧则让人不知所措。
怡年似乎也有一样的尴尬,不过她用来处理尴尬的方式是一刻不停地说话。在我们去机场的路上,她就开始喟叹如果不是要办理诸如签注一类的手续,自己根本就不想回去,因为家里只有她一个人。然后我才知道她父母一个是大学教授,一个是同声传译,多少都要和官方机构以及国际组织打交道,一年四季两三百趟航班,在家的时间特别少。而她的同学大都要申请出国,现在正值一些学校面试的关键时刻,基本上也没有人出来陪她玩。
「那不如今天去我家做客,一起吃饭?这几天我们也一起办手续如何?」我试着发出了邀请。
「好啊,如果不麻烦的话,很开心去你家,也顺便看看你的姐姐。」她第一次在路上露出笑容。
「太好了,我让家人准备一下。」我没有想到她会答应地如此爽快,有点喜不自禁。以我对她的了解,在面对类似这样的邀请时,她应该会多少有些踟蹰。现在这种回应只有两种可能:第一,她老早就决定去我家;第二,也许是我对她来说比较特别吧。
我觉得第一种可能性基本可以排除,因为她不太可能预知我会发出邀请,更因为我愿意相信第二种。这看上去很自恋,但我的自恋源自于对她这个人既往印象的感知,因为有这种敏感的感知力,我更愿意称之为自信。
之后的聊天就顺畅了许多。两人各自谈了分别之后经历的种种往事,有些让我们开心,有些让我们难过。在谈论这些事的时候,我突然感觉有些事情真的只能和同龄人谈,也只有同龄人才能理解。比如我们听对方聊起成长过程中经历的种种误会,碰到的困难和挫折,都感同身受。但是这些经历对于那些所谓的经历了大风大浪的长辈来说,不过春风化作的毛毛雨罢了。他们会告诉你要坚强,因为如果你连校园时代的这点小挫折都无法面对,又怎么能面对未来残酷的生活。
每次面对这样的论调,我就会去想,生活也许残酷,但如果能对一个遭遇委屈的孩子多一些关心,至少在事后再做教育,生活的残酷程度难道不会因此小一些吗?
不过想想这些长辈,可能他们也很可怜吧,他们也许只有在教训晚辈的时候才是这样的表现,才能找回一点被残酷的生活消磨殆尽的自尊和自信吧。从这个角度讲,很多时候我们被迫接受这样的「教育」,其实是为了让长辈们自己的生活不那么残酷,大人们觉得他们在含辛茹苦地养育孩子,反过来说孩子又何尝不是在含辛茹苦地「养育」大人?
大约下午一点,飞机在首都机场落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