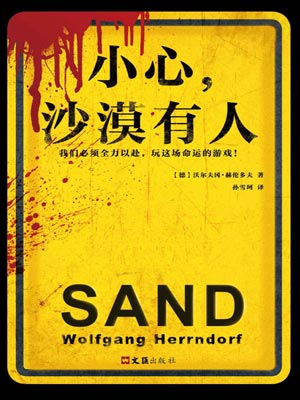约翰·巴肯提示您:看后求收藏(350中文350zw.com),接着再看更方便。
再次到户外溜达感觉还是蛮不错的。彼得的气色跟之前完全不一样了,他像一只牡鹿一样嗅着刺骨的空气。路边的营地飘来缕缕柴火和粪便燃烧的烟味儿,寒冬时节,狂风在空旷的地方呼啸着,这场景会让我终生难忘。每时每刻都带给我内心的宁静,赋予我不屈不挠的精神。军队从亚尔河首次迈向最前线,这是人们执着而疯狂的期望,这种感觉我以前也有过。我不习惯住在城市,在君士坦丁堡的闲散生活让我松松垮垮,疏忽懈怠,但是现在,凛冽寒风吹打着我们,我感觉要随时准备好应对各种危险。我们正处于到东部和边界小山的关键之地,很快我们将会到战争最危险的前线进行战斗,这不是一般的情报任务,而是你死我亡的战场,我们将要踏入战火地带,加入战斗,击垮敌人。我并不是说要与敌人同归于尽,如果我们没有死,也许会一起庆祝敌人的垮台。事实上,我不能把这件事情看作军队和国家之间的斗争。我几乎懒得去想我有没有同情心,重要的是,这是我们四个人和一个疯婆娘之间的较量,军队冲突只不过是我们这场私人较量中的背景而已。
那晚,我们来到一家脏兮兮的旅店,在地板上好好地睡了一觉。第二天,我们顶着鹅毛大雪出发。天气冷飕飕的,我们却士气高涨。玫瑰联盟的一个成员,名字听起来像是侯赛因,他曾经走过这条道,还告诉我这是哪儿,其实他们说了也跟没说一样。整个上午,我们挤在大批部队当中,只能缓慢前行,这少说也有一个旅,他们风风光光,昂首阔步,井然有序,算是我见过最壮观的场面。我必须说我很欣赏土耳其斗士。我记得有个朋友曾赞扬他是一个纯朴的战士。我很遗憾德国没有让他卷入这场肮脏的活动中。他们停下来吃了顿饭,我们也跟着停下来了,午餐就吃几片黑面包,一点无花果干,喝了一瓶特酸的葡萄酒。我和其中一个军官聊了几句,他会说一点点德语,还跟我说他们正向俄国进军,因为在高加索,土耳其已经取得胜利。“法国和英国是我们的手下败将,现在轮到俄国了。”他镇定自若地说道,好像在说教似的,不过他还说自己对战争深恶痛绝。
中午,我们绕过了军队,在开阔通畅的马路上开了几小时的车,这里地形偏向东面,好像朝向大河流域。不一会儿我们碰到一些从东部来的人,个个都是新面孔。第一批伤员,跟每个前线的伤员没什么两样,当然不乏一些装病的人,这些新一批队员,身心交瘁,经常光着脚,好像没跟上大部队,等着挨饿受冻,马路边还有一群军队拖着疲惫的身躯,精疲力竭,后面还有一队踉踉跄跄地尾随而来,他们累得都无力转头看我们,几乎个个都有伤在身,有些伤势严重,大部分骨瘦如柴。要是我那身后的朋友相信土耳其会取得胜利的话,那么他该如何辩解眼前这些可怜的人呢?我还真想不通。他们在战争中已没有回旋的余地了。
就连没有当过兵的布伦基伦都察觉到了这一点。
“这些小伙子真可怜。”他说,“少校,我们得赶紧点,不然会被落下的。”
那是我自己的感受。这场景让我拼命的加速,因为我想到东部有大事正在发生。我估计从安哥拉到埃尔斯伦要花四天的时间,但是现在第二天都快结束了,我们还没有走过三分之一的路程。我拼了命地前行,而这种匆忙正是我们失败的原因。
我说过史蒂倍克是一辆破旧的汽车,方向盘烂的要死,都没有怎么修补过,还有,路面崎岖难行。不久,我们遇到路面上覆盖着厚厚的积雪,天寒地冻,路上还可以看见大型运货马车留下的车辙印,坑坑洼洼,摇摇晃晃。我开始担心这辆破车,越来越觉得我们离这个村庄,还有很长一段路要走。夜幕慢慢降临,而我们正穿过有溪流的峡谷,仍然不知所措,在这儿浪费光阴。斜坡底下有一座桥,这是一座由圆木和泥土做成的桥,很显然,大车辆频繁地来来往往,桥面被加固了。我们很快来到桥上,结果车子失控了。
我使劲地沿直线前进,车子突然来了个左转弯,车子翻过岸边,陷入了泥泞的山谷里。我们的车猛地撞到地上,跌到低洼的地方,大家一下子都陷入了冰冷的泥坑中。我都不知道我们怎么逃脱出来的,没有人受伤,按理说,如果车子翻过来,我的脊背会骨折。彼得狂笑不已,布伦基伦抖了抖头上的雪,也跟着笑起来了。我认真地检查车身,发现前轴已经断了,车子惨不忍睹。
此时厄运连连,有点穷途末路的感觉,我们被困在小亚细亚中部,进退两难,周围没有任何车辆往来,想要弄到一根新的前轴,就像到刚果滚雪球一样,简直是天方夜谭。天一片漆黑,我们不能浪费时间,我把汽油罐和一些备用轮胎,移到山上的岩石坡上,虽然车上行李不多,我们还是清理了一下。这事只能靠侯赛因,他得想办法替我们找地方过夜,等天亮了,我们还可以碰碰运气,看能不能搭个顺风车什么的,再找一辆汽车是没指望了,因为安纳托利亚的汽车少之又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