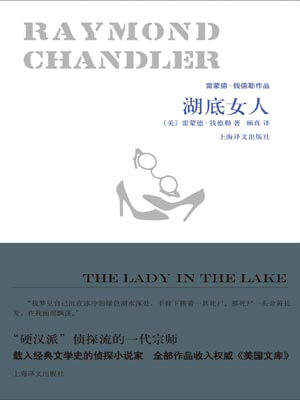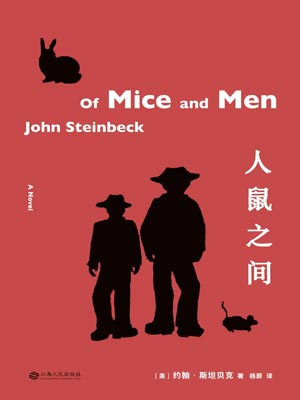吉羽提示您:看后求收藏(350中文350zw.com),接着再看更方便。
“选择最偏僻的地方走,比如……天水镇?”
“一点不错。”方骥点头道,“当夜的天水镇里,几个喜欢收藏古玉的年轻人正在一起喝茶赏月,当然,少不了端茶倒水的侍僮在一边伺候。
李修身子一颤,轻哼一声,抬眼道:“阁下是说,天水镇西的山英小馆?”
“正是。”方骥道,“李公子在那天晚上,亲手断送了一个穷苦少年的生路。”
“他是贼,还是家贼!”李修冷冷道,“山英小馆的主人祝敏收留他做侍童,就是看他可怜,给他一条生路,谁知道这个叫阿瑗的小子手脚不干净,趁我们品茶赏月时偷了祝敏新得的西周小玉马。”
“是吗?”方骥摇头冷笑,“可你们并没有在他身上搜到那只玉马。”
李修道:“从我们发现玉马失窃吵闹起来,到集合山英小馆的所有仆人、侍童搜身,其间足有一刻钟的工夫,那个小子见势不妙,完全可以先将玉马扔掉。”
“扔到哪儿?山英小馆里被你们刮地三尺搜了几遍,连灌木丛都铲掉了。”方骥道。
李修道:“山英小馆里有一口深不见底的寒井,祝敏平日煎茶只用这井里的水,还有像曲水园一样引入的活水,还有,事发时是在午夜一点左右,山英小馆周遭寂静无人,他完全可以将玉马扔到从小馆东侧流过的河道里。”
“那么,你有什么证据?脚印?”方骥哂笑道。
“当然,我们在祝敏收藏玉马的药庐间发现了踩着黑紫色泥土的脚印,山英小馆里是没有这种土的,只有小馆外种着玉冠花的小花园里才有,当夜在场的所有人都没有离开过小馆,只有那个叫阿瑗的小子被祝敏派去折一枝在夜间盛开的紫色玉冠花。”李修道,“还有,那只玉马被祝敏藏在药庐,小馆中的仆人、侍童和宾客都不知道,只是几天前祝敏藏玉时,被在药庐捣药的阿瑗撞了个正着,也怪祝敏太信任他,没有将玉马另藏他处。”
方骥连连摇头,顺手从皮包里拿出两张照片:“我想你们当时并没有注意到这些。”
“这是什……这是山英小馆的药庐,这边是药橱,这上面是……什么东西滴落的痕迹?”李修皱眉道。
“是血。”方骥指点着照片道。
李修略一思索,脸色大变。
方骥幽幽道:“天水镇是屏州下辖小镇中最偏僻的所在,山英小馆又地处天水镇西,这四周哪怕白天也寂无人迹,遑论午夜。而且小馆中仆人、侍童并不多,如果有人偷偷翻墙潜入,很难有人发现。而这个趁夜潜入小馆的人,极可能曾踏足馆外花园,沾了一脚黑紫色泥土,而且此人身上带伤,虽然处处揣着小心,但在翻找止血药时仍不慎将血滴落在药橱下,可惜,山英小馆的人没有发现。”
鲁小骅道:“如果有人从外面潜入,在山英小馆里应该留有一串黑紫色的脚印,可李公子说脚印只出现在药庐周围。”
李修叹道:“花园后就是小馆东墙,东墙内就是药庐。”
鲁小骅讷讷无语。
方骥道:“山英小馆药庐藏药既多且杂,颇负盛名,被何探长射伤逃走的盗画人应该半是顺路,半是是慕名而来。我猜祝敏藏玉马的地方,应该是放三七、紫珠草、小蓟这些止血药的抽屉吧?无论骆函还是花如映,都是精通古玩的大行家,当此人翻找止血药时,看到抽屉里竟然藏着一只玉马,岂有不顺手牵羊之理?”
“没错,是放紫珠草的抽屉,小馆里平时用不到这个。”李修脸色一暗,随即道:“对了,现场留下的脚印大小和那小子的完全一致。”
方骥道:“一个成年女子和一个少年男子脚的大小正巧相同,这有什么稀奇?
“成年女子?这么说这个盗画人是千面罗刹花如映。”何骏脸色一苦,叹道:“看来那一块被火烧过的古绢就是她的手笔。”
方骥不置可否,自顾自说道:“可怜的阿瑗,当夜便被赶出了山英小馆,孤苦无依,只好连夜赶路回家。”
“那是因为他死不认罪,还出言不逊顶撞贵客!”李修微恼道,“祝敏素来宽和,打发阿瑗离开前还顺手赏了他一个紫竹小盒,说是里面有几枚古钱,找个古玩铺子卖掉足够保他三五年吃穿不愁。”
醉蒙蒙伏在桌上的王驹猛地一惊,抬起头来。
“他是哪里人?”方骥也不多做争执,又问起了阿瑗的出身。
李修道:“好像是城西真笃村人,去年真笃村遭了水灾,人口十去七八,那小子安置好祖母之后,就孤身一人来屏州打拼,机缘巧合被祝敏收留,取名阿瑗,带去天水镇。”
“从天水镇到真笃村,要路过一个地方。”方骥冷冰冰道。
“什么地方?”李修秀眉紧蹙,随即一惊,“鬼泉河下游的那个泥潭,巡捕发现老乞丐尸体的地方!”
“不错!”方骥喝道,“那么你猜,他在那里看到了什么?”
“什么……”李修已经猜到了方骥接下来的话。
“有一辆黑色福特轿车停在泥塘边,一个衣冠楚楚的年轻公子把一具肮脏体丢进了泥潭,而那位公子他正好认得,是常与祝敏来往唱和的肖珍。”方骥把一张照片中重重甩在李修面前,正是肖冕之孙肖珍、山英小馆主人祝敏和几个年轻收藏家同桌宴饮的场面。
“李公子,想必你认得站在祝敏后面的那个孩子。”方骥用手指点点照片一角一个稍显模糊的身影。
“这是阿瑗。”李修道。
方骥冷笑一声,一把抽过照片,走到桌子对面,递给了鲁小骅:“想必鲁警官对他也不陌生。”
“这是那个抢劫韩采和李梅的小混混!”鲁小骅惊道,“他不是叫阎三儿么?”
瘫坐在桌角的王驹眼睛蓦地亮了起来,重重打了个酒嗝。
何骏思索片刻道:“方先生是不是想说,肖珍的未婚妻韩采枪杀阿瑗,是精心策划的灭口,而不是正当防卫?”不等方骥回答,又道,“那肖珍为什么不直接在抛尸现场杀了这个目击者?”
方骥道:“阿瑗在暗,肖珍在明,他并不知道树丛后的小路里藏着一个目击者。”
鲁小骅叫道:“那韩采怎么会知道?难道是阿瑗自己送上门去的?”
“没错,阿瑗被赶出山英小馆,衣食无着,只有铤而走险,将一封勒索信寄到了肖府,而鲁警官所谓‘抢劫伤人’,莫法官所谓‘正当防卫’,就发生在肖家和阿瑗约定的交付封口费的地方,屏州城北的太平巷。”
何骏道:“方先生不觉得你的话前后矛盾么?”
鲁小骅也兴冲冲拍着桌子道:“就是!你刚才还说祝敏赏了那阿瑗几枚古钱,足够他三五年吃穿不愁,怎么转口又说他衣食无着?”
方骥拿起摆在鲁小骅面前的那张照片,不急不缓地走到桌角,递到王驹眼前道:“这就要问王警官了,你凭什么夺走祝敏赏给阿瑗的‘和田马钱’,交给那个英国人?”
众人都是一惊,齐齐看向王驹。
王驹淡灰色的眼珠左右一滚,推开杵在自己面前的照片道:“一个破衣烂衫的乡下娃娃,一个西装笔挺的英国绅士,同时声称是那几枚和田马钱的主人,如果是你,你会选择相信谁?”
“和田马钱?那是什么?”鲁小骅问道。
方骥又取出一张照片道:“想必王巡长对这几枚钱币并不陌生。”
照片上是几枚呈不规则圆形的无孔铜钱,钱币正中有一圆圈,圈内有一抬腿欲行的骏马,圈外有一周奇形怪状的文字,背面则是散乱无章的汉字:重廿四铢铜钱。
“汉佉二体钱,这种文字是佉卢文。”李修惊道,“这种钱是最早是道格拉斯•福塞斯爵士曾在克里雅附近的一个废弃遗址中发现的,我看过一些报道,那是1876年,就是前清光绪二年的事。后来福塞斯在英国皇家地理学会举办的研讨会上作了一场报告,曾在欧洲引起轰动。后来斯坦因和他的团队在新疆找到不少这样的钱币,英国探险家对它非常痴迷。”
“祝敏倒真大度,竟然把这样的宝贝送给一个小贼。”鲁小骅一撇嘴道。
李修叹道:“祝敏嗜玉成痴,对古钱币倒真不大在行。也怪我当时没有讨来那个小盒多看一眼。”
王驹冷哼一声,喷着酒气道:“听你们的意思,倒像只凭这个姓方的几句话,就把这些古钱当成了那个小贼的东西。我非常确定,那些和田马钱是黑斯廷斯爵士刚刚从益古斋买到的!”
方骥眉头一挑道:“哦?凭什么?”
“凭益古斋汤老板的证词!”王驹道,“而且黑斯廷斯爵士能清楚地说出这些古钱的年代、归属、文字和辨别真伪的方法,那个阿瑗连这是什么东西都不知道!”
方骥嗤笑道:“他当然不知道,这种和田马钱冷僻得很,连祝敏这样的高段玩家都不甚了解,何况一个乡下孩子?所谓的‘证词’更不足采信,黑斯廷斯是益古斋的常客,汤老板当然会为这个大金主圆谎。”
李修见王驹脸色阵阵发黑,又问道:“听方先生话中的意思,是阿瑗和黑斯廷斯爵士在一家叫益古斋的古玩店前起了冲突,黑斯廷斯坚称是阿瑗偷了他刚刚从益古斋买的和田马钱,而益古斋的汤老板也证实爵士所言不假,那阿瑗当时怎么说?”
王驹冷笑道:“这小子说,他拿着和田马钱到益古斋,本想卖个好价钱补贴家用,结果被坐在店里的一个‘洋鬼子’一把夺了去。这不是满嘴放屁么!如果黑斯廷斯爵士真的看上了他那小玩意,花钱买了就是,黑斯廷斯又不是花不起那个钱!我问他钱的来历,他也说不清楚。”
“他当然不敢说,他是因为被李公子莫名其妙地扣上了小偷的帽子才被祝敏赶走的,这时候怎么敢说这些钱的来历?还有,‘他拿着和田马钱到益古斋’,他把钱装在什么地方?钱袋里,裤袋里,包袱里,还是拿在手里?”方骥问道。
王驹一愣,他可从来没注意过这些,那天他巡视到益古斋附近,拨开围观的人群时,那几枚马钱已经被暴怒的黑斯廷斯握在手里。
“李公子想必认得这只盒子。”方骥将一张照片递给李修,照片上是一只两寸见方的紫竹小盒,色泽凝重,古意盎然。
“这就是祝敏赏给阿瑗的那个小盒子,和田马钱就装在这里面。”李修惊道,“这照片你从哪儿拍的?这后面像是一个砚台,旁边是……笔架?”
“在益古斋汤老板的书桌上。”方骥道,“这只明代的小盒子虽然精致,却还入不得黑斯廷斯的眼,正便宜了那个汤老板。黑斯廷斯吃肉,汤老板喝汤,可怜阿瑗被逼无奈,只好铤而走险虎口夺食,生生断送了自己的性命。”
王驹狠狠盯着紫竹小盒的照片,喷着酒气道:“李公子,你确定这就是祝敏赏给那小贼的盒子?”
李修无奈点头:“独一无二,盒盖上有一道浅痕,是祝敏不小心划伤的。”
方骥望着一脸苦涩的王驹,冷笑道:“看来王巡长根本就没注意过这只盒子……”
“够了。”莫书骐有些不耐烦,“方先生,你到底想说什么?”
方骥道:“我想说的是,在座诸位自恃聪明的庸才,都是害死阿瑗的凶手。何探长放走的盗画人潜入山英小馆盗走玉马;李公子仅凭几个脚印便断定阿瑗行窃,令其含冤被逐;还有个不明就里的王巡长乱判葫芦案,断了阿瑗最后的生计,逼得他走投无路,只好投书敲诈;肖家祖孙则设下毒计,由未过门的孙媳韩采杀人灭口。肖冕、肖珍祖孙事先谋算好了这场谋杀的一切环节,包括根据鲁警官每日的回家路线和时间与阿瑗约定见面地点,为韩采设计一个合乎情理的路过太平巷的原因,寻找为了几百大洋甘愿使苦肉计刺伤自己的‘同学’李梅和其他五名证人,这一切谋算牵涉的人太多,实在算不得高明,但骗骗初出茅庐的鲁警官已经足够了,令我没想到的是,莫法官这个老江湖竟然未经深究便采信了鲁警官的证词,将韩采无罪释放,说到底,还是你老人家没把阿瑗这条贱命放在眼里吧。也许你不知道,在败诉之后,阿瑗的祖母在真笃村那间四面透风的老屋里自缢身亡,尸体直到三天后才被发现,逼死她的凶手就是你。”
莫书骐大惊,脸孔一阵抽搐,随即便镇静下来道:“她在法庭上语无伦次,口出秽语……”
“她当然语无伦次!”方骥大声道,“第一次上法庭的乡下老妇,你指望她能说出什么锦绣文章?至于口出秽语,那只是伤心过度,一时口不择言罢了。”
莫书骐沉着脸闷坐片刻,抬眼望向方骥:“方先生,你到底要做什么?要钱,还是要我们办什么事?”
方骥从公文包里取出一个小巧的正在转动的录音机,咔嗒一声关上了录音开关:“刚才和诸位的谈话我都已经录了下来,如果我把这盘录音带卖给广播电台或是报社,应该会得到不少报酬吧?”
莫书骐腮帮子一阵发酸,他升迁在即,可经不起这样的波折,舆论这东西,一旦被人引上岔路,就再难改变走向。
鲁小骅手脚冰凉,这是他入职以来办的第一件案子,错则错矣,不为人知便罢,如果这桩错案被小报广播大肆宣扬出去,他鲁小骅就算不被刘总巡捕踢去坐冷板凳,也要被那些惯会幸灾乐祸的同事戳穿脊梁骨。
何骏光头上渗出津津细汗,他就要退休了,一旦这件错案被小报电台铺天盖地地报道开来,一世英名毁于一旦不说,那些被扒光衣服搜身的名流怕是难免迁怒。
王驹将瓶中酒一饮而尽,抹了抹嘴唇道:“你想要多少钱?”
方骥抬腕看了看表,笑道:“我不要钱,不过,如果诸位能在半小时后的审判庭上高抬贵手,饶马公子一命,方某必有重谢。”说着摇了摇手中的录音机,重重掷在地上,“啪擦”一声摔得四分五裂。
“瞧,我已经表示了诚意,接下来,就看诸位在法庭上的表现了。”说着提起公文包,摇摇晃晃向门外走去,走到桌角时,顺手收回了摆在王驹面前的照片。
众人目送方骥离开,面面相觑,过了半晌,李修幽幽叹了口气,苦笑道:“原来是马家的人。”
“说起来,我只是在马公馆找到一条和第三位受害人生前照片上所戴的一样,呃……有些相似的项链,这个算不得什么证据吧?”鲁小骅瞟了何骏一眼,惴惴不安道。
王驹摸了摸酒糟鼻道:“我只是看到了马一侬出入第二位受害者的公寓,这个……说起来也不算什么铁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