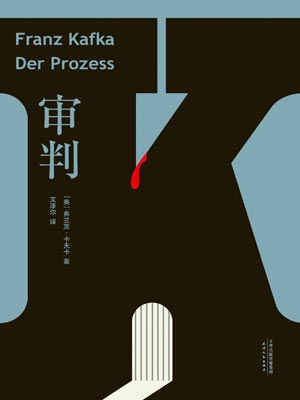赖特·米尔斯提示您:看后求收藏(350中文350zw.com),接着再看更方便。
在宏大理论中,证明就是满怀期望地演绎。目前看来,无论是要证明什么,还是如何去证明它,似乎都还不是非常明确的问题。
经验证明的问题就在于“如何认真对待事实”,而不是被事实所淹没;在于如何将想法与事实紧密关联,而不是埋没了想法。问题首先在于要证明什么,然后才是如何去证明它。
而在抽象经验主义里,要证明什么似乎不被视为值得重视的议题。如何去证明它则几乎是自动由陈述问题的方式给出了。这些方式融入了相关分析等统计步骤。事实上,对于这类证明的教条式要求似乎常常成了唯一的关注点,因此限定了甚至是决定了那些恪守这种微观风格的人使用什么“概念”,钻研哪些问题。
三
在经典风格的研究实践中,要证明什么往往被认为是重要的,甚或比如何证明它更为重要。想法的阐发与特定的一系列实质问题密切相关,而决定选择要证明什么的时候,遵循的是诸如以下的规则:努力证明所阐释的想法中据称与阐释的推论最相关的那些特征。我们把这些特征称为“关键性的”特征,倘若这一点的确如此,那么下一点、下一点、再下一点也必然都是如此。而如果这一点并非如此,那么会有另一系列的推论。这种步骤的理由之一,就是觉得需要简化研究工作:经验证明、证据、文献附注、事实的确定,这些都非常耗时,而且往往单调乏味。有鉴于此,人们会希望这类工作对自己正在采用的想法和理论是最具影响力的。
不仅如此,无论是亚历史的研究层面还是跨历史的研究层面,人们所使用的想法绝大多数其实都源于经典研究。又有哪些关于人、社会及其关系的观念,哪些真正富有裨益的想法,是来自抽象经验主义或宏大理论的呢?就想法而言,这些学派都是靠社会科学经典传统过活的寄生虫。
经典风格的治学者通常不会只针对一项大型经验研究搞出一套大型方案。他的方针是听任乃至挑起宏观观念和细节阐释之间的持续交流。为此他把自己的工作设计成一系列小型经验研究,里面每一项都似乎对他在阐发的解决方案的某个部分起到关键作用。根据这些经验研究的结果,这个解决方案也就得到了确证、修正或驳斥。
这类研究的经验成分绝不少于抽象经验主义。事实上,它往往还更加重视经验,更加贴近日常意义和经验的世界。我想说的其实很简单:弗朗兹·纽曼有关纳粹社会结构的阐述,相较于萨缪尔·斯托弗有关10079部队士气的阐述,其“经验性”和“系统性”至少不相上下;马克斯·韦伯有关中国士大夫的阐述、尤金·斯塔利有关欠发达国家的研究、巴林顿·摩尔对于苏维埃俄国的考察,相较于保罗·拉扎斯菲尔德对于伊利县或埃尔迈拉小城的舆论的研究,其“经验性”程度难分伯仲。
在经典风格的实际研究者看来,如何证明陈述、命题与推定事实,似乎并不像微观视角的研究者常常搞的那么费劲。经典风格的实际研究者通过细致阐发一切相关的经验材料来证明一项陈述。当然,我再说一遍,如果我们已经觉得需要以这种方式结合我们的问题,选择并处理我们的观念,我们就往往可能以统计调查的那种更为精确的抽象方式来展开细致阐发。而对于其他的问题和观念,我们的证明则类似于历史学家的做法,问题转向了证据。当然,我们从来也不会很确定;事实上,我们往往是在“猜测”。但我们不能说所有的猜测都有同等机会被证实。我们不妨满怀敬意地说,经典社会科学的一项宏旨就是提高我们有关重要事项的猜测的正确概率。
绝大多数经典风格的研究都介于抽象经验主义和宏大理论之间。这类研究也包含了对于日常情境中可以观察到的东西的某种抽象,但其抽象的方向是趋向社会历史结构。人们对于社会科学经典问题的梳理,正是在历史现实的层面上,也就是说,正是从特定的社会历史结构的角度出发,也正是从这样的角度来解答的。
所谓证明,就在于以理性的方式说服别人,也说服自己。但要做到这一点,我们就必须遵循公认的规则,首要的规则就是必须以特定的方式呈现研究工作,使其每一步都是开放的,以供他人核查。而要完成这一规则,并不存在“唯一正道”。不过,它总是要求我们倍加谨慎,留心细节,养成明晰的习惯,抱持怀疑态度对据称的事实进行审核,对其可能有的各种意涵,及其对于其他事实和观念所具有的影响,始终充满好奇。它要求系统有序。简言之,它要求我们坚定不懈地践行学术伦理。如果这一条不具备,无论什么技术,什么方法,都将徒劳无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