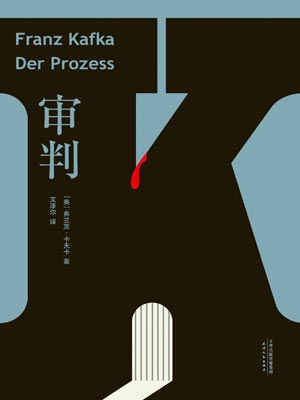赖特·米尔斯提示您:看后求收藏(350中文350zw.com),接着再看更方便。
在过去25年间,社会科学的管理用途和政治意涵发生了决定性的转变。“社会问题”在早前的那种自由主义实用取向依然还在起作用,但已经在更新近的管理型、操控型保守主义用途面前相形见绌。这种非自由主义的新型实用取向形式多样,但称得上是一种影响整个人文学科的总体趋势。要讨论它的气质,不妨首先以反映其显著合理化的例证作为导引。“对于那些计划成为一位社会学家的学生,最后需要告诫一句,”保罗·拉扎斯菲尔德如此写道:
他可能会担忧世界局势。战端重启的危险、社会体制之间的冲突,还有迅猛的社会变迁,他在自己国家观察到的这一切或许让他觉得,有关社会事务的研究可谓当务之急。危险在于,他可能指望自己就钻研社会学那么几年,然后就有能力解决所有现行问题。不幸的是,实情并非如此。他将学习更好地理解周遭事态。偶尔他也会找到展开成功的社会行动的指引。但社会学尚未发展到如许阶段,能为社会工程提供安稳的基础。……从伽利略到工业革命开始,自然科学花了大约250年,才能对世界历史产生重大影响。而经验性社会研究的历史只有三四十年。指望从后者那里求取快捷答案以解决重大世界问题,一味要求它给出直接实用的结论,只会破坏它的自然发展进程。<a id="noteBack_1" href="#note_1">[1]</a>
近些年来人们所称的“新社会科学”,不仅指抽象经验主义,也包括非自由主义的新型实用取向。这一说法兼指方法和用途,并且完全可以成立:因为抽象经验主义的技术及其科层用途如今一般都融为一体。我认为,如此融为一体,就会导致科层式社会科学的发展。
就目前人们践行的抽象经验主义而言,其存在本身及影响的方方面面特征都呈现出一种“科层式”的发展。抽象经验主义风格的学术操作努力要把社会研究的每一个阶段都变得标准化、合理化,就此越来越变得“科层式”。这些操作如此做派,使得有关人的研究往往变得集体化、系统化。只要抽象经验主义被妥当贯彻了,那些研究机构和政府机构就会发展出各种惯例,和任何企业的财务部门一样讲求合理性,不是为了别的目的,就是为了提高效率。而这两种发展趋势又在很大程度上关系到在学校教职员工中筛选和塑造新型心智品质,这些品质既有思想上的,也有政治上的。当“新社会科学”被用于工商业,尤其是广告业的沟通部门,被用于军队,以及愈益增多地被用于大学,也就开始服务于其科层主顾可能持有的任何目标。那些倡导并践行这种研究风格的人,很容易从其科层主顾和头领的政治视角看问题。而采取这样的视角,往往也就顺其自然地接受了它。诸如此类的研究努力确实能卓有成效地达成它们所宣称的实践目标,因此有助于提高现代社会中科层形式的支配的效率,增进其声名,到一定程度也会促进这类支配的流行。但无论是否有效地达成了这些公开宣示的目标,这些研究努力的确有助于将科层制气质传播到文化生活、道德生活和思想生活的其他领域。
一
恰恰是这些最急切地想要摸索出道德上冷静客观的方法的人,却最深入地参与了“应用性社会科学”和“人类工程”,这似乎颇为讽刺。既然抽象经验主义做派的研究耗资不菲,那就只有大型机构才能轻松负担,其中包括企业、军队、政府,以及它们的分支机构,尤其是广告、推销和公关部门。基金会同样也能负担,但是掌管基金会的人员做起事情来,往往倾向于遵照实用取向的新典范,也就是说,从科层角度来看是适宜的新典范。其结果是,这种风格就已经逐步体现在确定的机构核心中:20年代以后的广告和市场部门,30年代开始进入企业和综合民调机构,40年代以后蔓延到学术生活,特别是一些研究机构,而到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扩展到了联邦政府的研究部门。机构模式目前还在不断扩张,但上述这些依然是其坚强堡垒。
这些所费不赀的技术颇具形式主义,这倒使它们特别有助于为那些有能力并乐意掏钱的人提供他们所需要的那类信息。新的应用研究的焦点一般会落在具体的问题上,旨在针对实际的举措,也就是资金和管理方面的举措,搞清楚存在哪些可行方案。都说只有发现了“一般原则”,社会科学才能提供“可靠的实践指导”,但事实绝非如此。管理者往往需要了解某些细节性事实和关系,但他需要了解或想要了解的也就只限于此。践行抽象经验主义的人往往不太在意要设定自己的实质问题,所以他们非常乐意改变自己对于具体问题的选择。
从事应用性社会研究的社会学家通常不会以“公众”作为自己的受众。他有自己特定的客户,后者各自有其利益和难局。从公众转向客户,显然破坏了漠然超然的客观性这一理念,该理念或许有赖于对缺乏焦点的模糊压力做出回应,所以更取决于研究者的个人兴趣,而后者可能不经意间分散多处,因此难以操纵。
对于学院人士的职业生涯来说,任何“思想流派”都是有意义的。要界定什么是“好的研究”,就是看它如何契合于特定的流派,因此学术上的成功往往有赖于主动接受占据支配地位的流派的信条。只要还存在许多个或至少几个各持异见的“流派”,这种要求就并不需要强加给任何人,在一个不断扩张的职业市场上就更是这样。
在从事社会科学研究的个体治学者和第一流的研究之间,除了他自己的个体局限,并没有多少别的阻碍。但这样一种无所依附的人并没有能力去做规模相称的抽象经验研究,因为要想实施那类研究,必须有某个研究部门充分发展起来,提供相应的材料,或许我应当说是相应的工作流程。要践行抽象经验主义,就要求有一家研究机构,从学术角度上讲,还需要有大笔的资金支持。随着研究成本的增长,随着研究团队的形成,随着研究风格本身变得耗资庞大,对于分工的企业化控制也就随之而来。过去认为,大学就是一群职业同侪的圈子,他们各授其徒,各行其艺。这种旧观念慢慢被新的观念所取代,即认为大学是一套从事研究的科层组织,各自包含一组精详的分工,因此也就各自容纳一群知识技术专家。即便没有别的理由,就为了有效地利用这些技术专家,也越来越有必要系统地编撰程序步骤,以便人们学习掌握。
研究机构也很像是一种培训中心。它和其他机构一样,挑选某些类型的心智,并通过提供酬报,对某些心智品质的培育发展给予鼓励。在这些机构中,除了比较老派的学者和研究者外,还出现了两类对于学术舞台来说颇为新鲜的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