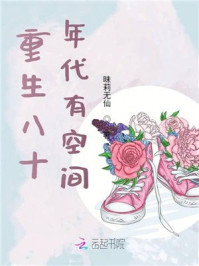劳伦斯提示您:看后求收藏(350中文350zw.com),接着再看更方便。
“但愿不会给你添麻烦。”康妮说。
然而,要是弗林特太太不麻烦,哪儿来的乐趣!康妮逗着宝宝玩,小女孩的无畏把康妮逗乐了,她从这小宝宝柔软、温暖的身上感到一种深深的快感。这年轻的小生命!这样的无畏!正是因为无助,她才无畏。所有其他人,都因畏惧而如此狭窄!
她喝了一杯相当浓的茶,吃了些精美的黄油面包和罐头李子。弗林特太太因为兴奋而满面红光,同时也很拘束,仿佛康妮是某个英勇的武士。她们谈着女人的私房话,两人都兴致盎然。
“但是这茶点太糟糕了。”弗林特太太说。
“比我家里用的还好呢。”康妮说得很真诚。
“哦——呵!”弗林特太太自然是不相信的。
最后康妮还是站了起来。
“我得走了!”她说,“我先生不知道我上哪儿了。他肯定又会东想西想了。”
“但他绝对想不到您会在这儿的。”弗林特太太高兴地笑道,“他一定会派人四处喊您的。”
“再见了,约瑟芬。”康妮亲吻了孩子,用手揉了揉她红色的软发。
弗林特太太坚持要去替康妮开门,大门上了锁,而且用门闩插上了。康妮走到了农庄门前的小花园里,小花园被绿篱环绕着,小径旁种着两行报春花,绒乎乎的,很富贵的样子。
“这报春花开得多漂亮啊!”康妮说。
“卢克管它们叫‘没心没肺’。”弗林特太太笑着说,“摘些走吧。”
于是她热心地帮康妮采了好些天鹅绒般的报春花。
“够了!够了!”康妮说道。
她们来到小花园的门边。
“您想从哪条路走?”弗林特太太问道。
“还是走畜牧场那条路吧。”
“我想想!哦,对了,母牛在挤奶场里,不过还没有挤完。但是门锁上了,你得爬过去呢。”
“那我就爬过去好了。”康妮说。
“还是我陪您到栅栏那边去吧。”
她们走下那片让兔子糟蹋得不像样的草场。鸟在林中拼命啭鸣着傍晚的欢欣。一个男人正在召回最后一批母牛,这些母牛慢条斯理地走在草场上踏出的一条小径上。
“它们晚了,今晚挤吧。”弗林特太太愤愤地说,“它们知道卢克天黑以前不会回来。”
她们来到栅栏边,栅栏另一边是浓密的小杉树林。那儿有个小门,但是锁上了。门里面的草地上立着一个空瓶。
“这是那个猎场守护人盛牛奶的空瓶子。”弗林特太太解释道,“我们装了牛奶就给他拿到这里来,然后他自己把它取回去。”
“什么时候取呢?”康妮问道。
“呵,他什么时候到这边来就什么时候取。一般都是早上。那好,再会了,查泰莱夫人!您一定要常来啊,跟您在一起真是很开心。”
康妮跨过栅栏,走到了一条窄窄的小径上,小径两旁挺立着密密麻麻的小杉树。弗林特太太穿过草场往回跑去,戴着一顶太阳帽,因为她真正是位教师。康妮不喜欢这些新植的树林;这么浓密,让人觉得恐怖又压抑。她低着头匆匆赶路,想着弗林特太太的孩子,真是个可爱的小东西,不过她两条腿会像她父亲,有点罗圈。现在已经能看得出来了,但是也许长大了就会好的。要一个孩子是多么让人兴奋、多有成就感的事啊,看弗林特太太有多得意!她有的,康妮没有,而且显然不可能有。是的,弗林特太太为人母了,是值得炫耀炫耀。但这使得康妮有点儿,稍微有点儿,嫉妒起来。她实在是有些嫉妒。
突然她从沉思中惊醒过来,轻轻惊叫了一声。一个男人出现在她面前!
是猎场守护人。他在路中间站着,就像巴兰的驴子<a id="ch1-back" href="#ch1"><sup>(1)</sup></a>似的,挡住了她的去路。
“这是怎么回事?”他惊讶地说道。
“你是怎么来的?”她喘着气问道。
“你是怎么来的?你去小屋了吗?”
“没有!哦,不!我刚去了马瑞海。”
他好奇地看着她,像在探寻着什么,她有些内疚地低下头。
“你现在是要到小屋去吗?”他有些严厉地问道。
“不,我去不了。我待在马瑞海。没有人知道我去哪儿了。我已经晚了,我得赶紧走。”
“好像是在想甩掉我吧?”他微笑着说,话里有一丝嘲讽。
“不!不。不是那个意思,只是——”
“怎么,有别的原因吗?”他说着,几步走上前去抱住了她。她觉得他的身体是这样可怕地紧贴着她,这样兴奋。
“哦,不要,现在不要。”她叫出声来,想把他推开。
“为什么不行?现在才六点钟,你还有半个小时。不!不!我现在就要你。”
他紧紧地抱着她,她感到了他的急切。她那古老的本能开始在为自由而挣扎了,但是她体内有一种奇怪的感觉,又迟钝又沉重。他的身体更急切地紧贴着她,她已无心去挣扎了。
他朝四处看了看。
“来——到这儿来!从这里过来。”他一边说,一边紧紧地盯住浓密的杉树林,这都是些小杉树,还没怎么长大。
他回头看着她。她看着他的眼睛,那么强烈、那么明亮、凶悍,充满了旺盛的精力,可不是爱意。不过她的意志已经松懈下来。她的肢体感到一阵奇异的沉重。她妥协了,放弃了。
他领着她穿过多刺的树林,那树林像墙一样很难通过,他们一直走到一块稍微空旷的地方,这里只有一堆枯死的大树干。他把一两根干枯的大树干扔到地上,再把他的外套和背心盖在上面,她得像动物似的,躺到树的树干底下,而他就站在旁边等着,只穿着衬衣和裤子,用着了魔似的双眼望着她。不过他还是考虑很周到的——他让她舒舒服服地躺着。不过,他却把她内衣的带子弄断了,因为她只是被动地躺在那儿,一点也不配合。
他只把前身裸露着,当他进入她身体的时候,她觉得他赤裸的肉体紧贴着她。好一会儿,他在她体内静静地待着,沸腾着,颤抖着。当他开始动作起来的时候,在一种突然而不可抑止的兴奋中,唤起一波又一波的新奇快感。一阵儿一阵儿,慢慢地波动起伏,好像轻柔的火焰在轻轻拍打,轻柔得就像羽毛,向着光辉的顶点奔涌,那么激烈,那么美妙,要熔化了她的整个身体似的。有如钟声,一波接一波地登峰造极。她躺在那儿,不由自主地发出狂野而细微的呻吟,直到最后叫出声来。但是这一切结束得太快了,太快了,她无法再用自己的活动来强行让自己结束。这一次是不同的,真的不同。她什么也不用做。她无法再让他坚硬而紧紧咬住,以达到她自己的满足。她只有等待,等待,心中呻吟着,感受着他在抽出,抽出,缩小,直到他从她体内滑脱、离去的那一关键时刻。她的子宫张开着,温柔地、温柔地喧闹着,好像潮水下面的海葵,喧闹着要他再次进入,成就她的满足。她沉浸在激情中,下意识地紧紧抓住他,他从来没有完全从她体内滑脱出来,她能够感到他柔软的小芽在她体内动弹,一种奇异而有节奏的慢慢加快的动作,使得这种奇异的节奏也在她体内伸展开去,慢慢地膨胀、膨胀,直到最后充满她整个分崩离析的意识。这时候,那种难以言表的运动重新开始,其实那并不是一种运动,而是感觉在纯粹的深海漩涡中翻腾着,越来越深入地穿透到她的所有组织和意识中去,直到她最终成为一种和漩涡同中心的感觉流体,而她躺在那儿无意识地发出含混不清的叫声。声音从无边的黑夜里中传出来,那意味着生命!那男人怀着敬畏听着从他身下发出的这种声音,同时将他的生命喷射在她的体内。当那声音逐渐平息时,他也停下来,静静躺在那儿,什么也不知道;而她也慢慢松开他,懒洋洋地躺在一边。他们就这样躺着,什么也不知道,甚至不知道对方的存在,二人都迷失了自己。最后,他开始醒过来,发觉自己无遮挡地裸露着,而她则觉察到他的身体正从对她的紧紧环抱中松开。他正在坍塌;但是她心里感觉无法忍受他从她身体上下来。他现在必须永远覆盖在她的上面。
但是他最终还是抽身了,他吻她,给她遮盖起来,然后开始遮盖自己。她躺在那儿,仰望着头上的树干,还无法动弹。他站着扣好他的裤子,朝四周看了看。密林中鸦雀无声,只有那条诚惶诚恐的狗躺在那里,爪子放在鼻子上。猎场守护人又在干枯树干堆上坐了下来,默默拿起康妮的手。
她转过身看着他。“这一次我们同时达到了高潮。”他说。
她没有回答。
“如果能这样真的挺不错。多数人一辈子都没体验过这个呢。”他像是在梦中说话。
她看着他的沉思的脸。
“是吗?”她说,“那你觉得快乐吗?”
他回过头来看着她的眼睛。“快乐。”他说,“是的,可还是不要谈吧。”他不想她再谈这个。于是他俯下身来,吻了她,她觉得他一定会永远这样吻她。
最后她坐了起来。
“人们不是能经常同时达到高潮的吗?”她用一种天真而好奇的语气问道。
“有很多人从来都没有过。你只要看他们一副夹生面孔就可以知道。”他不知不觉说出口,但是心里又觉得后悔开了这个头。
“你和别的女人也这样同时达到过高潮吗?”
他看着她,觉得好笑。
“我不知道。”他说,“我不知道。”
她知道,他不想告诉她的事情他是绝对不会说的。她看着他的脸,对他的激情还在她五脏六腑运行。她在尽力克制着自己,因为她已经感到迷失了自我。
他穿上背心和外套,再次艰难地穿过杉树林到小径那里去。
落日最后的几缕余晖洒在树林里。“我不跟你一块儿走了。”他说,“这样会好一些。”
她恋恋不舍地看着他,不忍转过身去,而那猎犬却焦急地站在一旁等着他出发了,他似乎也没有什么话可说了。确实没有话了。
康妮慢慢走回家,认识到身上另一种东西的深度。另一个自我活在她体内,正在燃烧、熔化,在她的子宫和五脏六腑中软软的感觉,她和这自我一起酷爱他。酷爱到走路时两膝酥软的地步。在她的子宫和五脏六腑中,她在流动,在奔腾,而一个最天真的女人,她在那种对他的酷爱中又是脆弱无助的。感觉就像是个孩子,她心想;就像有个孩子在我身体里。就是这样,就好像她一向都紧闭的子宫张开了,充满了几乎是负担然而很可爱的新生命。
“我要有个孩子就好了!”她心想,“要是他是孩子,我怀上他就好了!”——想到这个,她的肢体都融化了,她明白了,有个自己的孩子,和跟一个自己五脏六腑所渴望的男人有个孩子,这两者之间是有天壤之别的。前者似乎是平常意义上的有孩子,但是跟一个在自己五脏六腑和自己子宫中酷爱的男人有个孩子,就让她感觉和原来的自我大不相同了,感觉好像自己正在深深地,深深地沉入到整个女性的中心,沉入到孕育创造的睡眠中。
让她感到焕然一新的并不是这种激情,而是如饥似渴的酷爱。她原来对此一向很惧怕,因为那让她感到无助;她现在仍然恐惧,她害怕自己爱他爱得太深,迷失了自我,抹杀了自我,她不希望自己被抹杀,像个奴隶,像个未开化的女人。她不能成为一个奴隶。她惧怕这种酷爱,然而她不想立刻去对抗它。她知道自己可以对抗。她心中像魔鬼一般固执,足以对抗从子宫充分膨胀起来的温柔酷爱,加以摧毁。她甚至现在就可以这么做,或者她认为可以这样做,然后她可以按自己的意愿专注于激情。
哦,是啊,像一个酒神女祭司,像一个酒神信徒那样狂热激昂,在树林中飞奔,去拜谒活的阳物伊阿科斯<a id="ch2-back" href="#ch2"><sup>(2)</sup></a>,在其背后没有独立的个性,他只是纯粹为女人服务之神!个体的男人,让他不敢侵入吧。他只是一个寺庙仆役,他只是举着属于她的阳物,只是阳物的保管者而已。
于是,在不断新的觉醒中,原来那种冷酷的激情在她心中一度升腾起来,男人在她心中又蜷缩为可鄙的对象,仅仅是举着阳物的人,当他的服务完成之后,便被撕得粉碎。她感到酒神女祭司们的那种力量充斥于她的四肢和全身,女人闪现出来,迅雷不及掩耳,将男性击倒;但当她感觉这些的时候,她的心很沉重。她不想这样,这一切大家都明白,是不妊的,不生育的;酷爱才是她的珍宝。这种情感这么不可思议、这么温柔、这么深邃而神秘!不,不,她宁愿放弃那冷酷而显赫的妇人权威;她已经厌倦了这种感觉,它让她变得那么生硬;她愿意沉入新的生命之池中,沉入无声地歌唱着酷爱之歌的子宫和五脏六腑深处。开始害怕男人为时尚早。
“我去马瑞海那边走了走,还跟弗林特太太喝了杯茶。”她对克里福德说,“我是想去看看小宝宝的。那孩子真是可爱,她的头发就像柔软的红蛛丝。多可爱的宝贝啊!弗林特先生到集市上去了,所以她和我,还有那孩子一起吃了些茶点。你有没有纳闷我去了哪?”
“是啊,我正觉得奇怪呢,但是我猜你肯定是去哪家喝茶了。”克里福德嫉妒地说。凭他的洞察力,他感到她身上有了一种新的东西,这种感觉是他所无法领悟的,但是他把这归结到了那孩子身上。他认为,困扰着康妮的是她不能生孩子,也就是说,不能自动生孩子。
“我看见您穿过园林到了铁门那里,夫人。”波尔顿太太说,“所以我还以为您可能是去了神父家。”
“我差点要往那儿去,可是后来又拐到马瑞海去了。”
两个妇人的目光相遇了:波尔顿太太灰色的眼睛十分明亮,似乎在探究什么;而康妮的蓝眼睛则是那么朦胧,奇异地透出美丽。波尔顿太太几乎很肯定康妮有了情人,但是这怎么可能呢,那个情人又会是谁呢?他到底是哪里的人?
“哦,常出去走走,看看女伴儿,对您的身体是很有好处的。”波尔顿太太说,“我刚跟克里福德爵士说,如果夫人肯多出去看看,多跟人家打打交道,对夫人是绝对有好处的。”
“是啊,我觉得出去走一趟挺高兴的,克里福德,那个孩子真是奇妙可爱而又放肆。”康妮说,“她的头发就像蜘蛛网似的,是那种鲜光的橙红色,那双瓷器般的浅蓝眼睛,十分奇特、放肆。当然啦,她是个小女孩,不然不会这么大胆,简直赛过任何小弗朗西斯·德雷克爵士<a id="ch3-back" href="#ch3"><sup>(3)</sup></a>。”
“夫人说得一点不错——是个地道的小弗林特。他们始终是冒失的棕色脑袋的一家人。”波尔顿太太说。
“你不想看看她吗,克里福德?我已经约了她们来喝茶,这样你可以看看她。”
“谁啊?”克里福德问道,不安地看着康妮。
“弗林特太太和她的宝宝,下星期一过来。”
“他们可以去你楼上的房间喝茶。”他说。
“怎么啦,你不想看看那孩子吗?”她喊道。
“呵,看看倒无所谓,不过我不想把喝茶的时间都搭进去陪着她们。”
“哦!”康妮喊道,一双朦胧的大眼睛望着他。
她没有真正看见他,他是另外一个人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