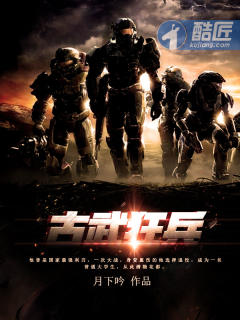米亚·科托提示您:看后求收藏(350中文350zw.com),接着再看更方便。
“给我一张小纸牌,我写一首祈祷词让你背诵。看着吧,在这之后,你就会做梦了。”
“抱歉,维塔里希奥。是写还是刻?”
我将纸牌从地下挖出来,给了他一张方片A。在红色的菱形图案四周,有空间让他写下神圣的词汇。
扎卡里亚犹犹豫豫地选好位置,摆好姿势,确保木头在他的两腿之间。他双手交替地摆弄着匕首,迟迟不肯开始记录。
“这张不行。你不如给我一张‘王后’。因为这是一首献给圣母的祈祷词。”
“把这里的居民都登记在人口清单里,把所有东西都刻在这块木头上。”我爸爸一边下令,一边递给他一柄旧匕首。
我将这张纸牌保存妥当,仿佛它是我毕生能够拥有的最珍贵的财富。当我在床前跪下,我的心总会扰乱这小小的祷告。直到有一天,我嘴里念着祷词时,军人扎卡里亚突然出现。
只有卡拉什自己笑了。也正是这位扎卡里亚,受上级指派,将会正式记录我们的新名字。
“你在唱歌吗,姆万尼托?”
“我还不知道有谁是因为喜欢才出生的。也许扎卡里亚是吧……”
“才不是呢,扎卡。是俄语,我从剩下的标签上学到的。”
我有许多个肚脐,已经出生了无数次,每次都是在耶稣撒冷,希尔维斯特勒高声宣告。同样在耶稣撒冷,我将结束自己的最后一次出生。“那边”——我们所逃离的那个世界——实在太过悲伤,令人失去了出生的欲望。
我的谎言站不住脚。扎卡里亚,没错,他奉希尔维斯特勒的命令监视我们。我们马上便被召集起来。我爸爸已经准备好了对恩东济的指责:
“他还处于正在出生的状态。”我爸爸如此解释对我名字的保留。
“是你教会了你弟弟。”
我们一个个被叫上前去。是这样的:奥兰多·玛卡拉(我们亲爱的“教母”舅舅)成为了阿普罗希玛多舅舅。我哥哥奥林多·文图拉变成了恩东济。助手厄尔内斯提尼奥·索布拉被更名为扎卡里亚·卡拉什。而玛丢斯·文图拉,我多灾多难的父亲,则变成了希尔维斯特勒·维塔里希奥。只有我保留了原先的名字:姆万尼托。
我预见到暴力,不等恩东济求助,便赶紧帮忙:
“现在,我们开始举行除名仪式。”
“恩东济根本不知道我学习的事情。”
接着,他让扎卡里亚给他拿来一桶水。他将几滴水洒在地上,但马上就后悔了。他并不想给逝者喝水。他用脚蹭掉了湿润的沙子,直到不留痕迹。修正错误之后,他用沉重的声音宣布:
“这里谁也不许祈祷!”
“这里是最后的国度,它将被称作耶稣撒冷。”
“但是,爸爸,这有什么不好?”恩东济质问。
更名改姓并非一个无足轻重的决定。希尔维斯特勒准备了一场隆重而有意义的仪式。太阳刚一落山,扎卡里亚便敲起鼓来,大声呼喊出一串费解的祷词。我、我舅舅和我哥哥聚集在小广场上。我们安静地站着,等待对我们的召唤。正在那时,希尔维斯特勒·维塔里希奥裹着床单,走进广场。他带着一块木头,以先知的风范走到耶稣受难像旁边。他将木头插在地上,于是我们明白,这是一块牌子,上面浅刻着一个名字。我爸爸张开双臂宣告:
“祈祷就是呼唤来访。”
即使在睡梦中,我哥哥依然在对抗父亲的权威。玛丢斯·文图拉这个名字同样是耶稣撒冷不可言说的秘密。事实上,希尔维斯特勒·维塔里希奥曾有过另一个名字。曾经,他叫作文图拉。在我们搬到耶稣撒冷之后,我爸爸给我们起了另外的名字。作为被再次命名的人,我们有了另一次出生,也能更加脱离过去。
“但谁会来访呢,既然世界上已经没有任何人了?”
“玛丢斯·文图拉,到地狱里下油锅去吧!”
“还有舅舅……”我适时地更正。
他瞬间就睡着了。接着便出现我们家庭的奇迹:在房间的各个角落,蜡烛自行燃烧起来。更晚一些,我躺在床上,听着恩东济沉稳的呼吸——他已经进入了猫头鹰与噩梦的国度。我有时会听到我哥哥说梦话,用不是他自己的声音呼喊:
“闭嘴,谁让你说话了?”我哥哥吼道。
“现在你们可以走了。我已经开始脱离身体。”
老希尔维斯特勒面露微笑,对大儿子的绝望表现深感满意。他已经不需要插手了,儿子已经以另一种方式受到了惩罚。恩东济注意到父亲的满足,深吸了一口气以自我克制。再度讲话时,他已经调整好了嗓音:
一般情况下,他很早就去休息了,连日落都等不到。我们陪他走到卧室,笔直地站在一旁,直到他在床上躺好。他随意地摆摆手,用模糊的声音说:
“我们能有怎样的访客呢?跟我们解释一下吧,爸爸。”
“那就上床去吧。”
“有你根本注意不到的访客。天使和魔鬼,它们无需我们同意便会到来。”
“像爸爸教导的那样拥抱的。”
“是天使还是魔鬼?”
“双臂张开匍匐在地?”
“天使还是魔鬼,区别并不在于他们,而仅仅在于我们。”
“拥抱过了,爸爸。”
希尔维斯特勒举起的胳膊不容置疑:谈话已经越了界。事情很清楚,再也不能有祈祷。这就是最终的句点,是不可争辩的唯一决断。
“你拥抱过大地了吗?”
“而你!”我爸爸指着我宣布,“我一次也不想再听到你哭。”
每天结束时,我们有另外的任务,但同样神圣。当我们来道别的时候,希尔维斯特勒会问:
“我什么时候哭过,爸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