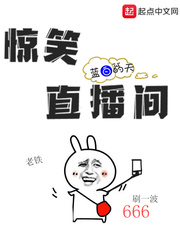章含之提示您:看后求收藏(350中文350zw.com),接着再看更方便。
从苏州回来,我在忧伤之中夹带着对新的生活的期望。经过了两年痛苦的徘徊,我终于知道我该怎样活下去了。那年我整五十,是一个重新开始的很好的里程碑。我不会忘记过去,但正因为这过去,我要再度证实我可以是生活的强者。我需要更换环境。那时我虽然有一个单位,但仍在原来的系统。那里的许多年轻人对我也不无同情,但在权势与偏见的压制下,我连工作的机会都没有。这时我得到了另一位我永不忘记的长者的帮助。那就是杜老,杜润生同志。和袁庚同志一样,我与杜老素不相识。但他们这两位老共产党员同样地珍惜人的才华,同样地对党内发生的许多事情用历史的、唯物辩证的眼光看待,同样地宽厚待人。在我一生最艰难的时期,他们两位都曾慷慨地给予我宝贵的理解和真切的帮助。当杜老的夫人马素芳大姐介绍我认识杜老,我对他说我想换个单位做点工作时,他毫不犹豫地欢迎我到他领导的国务院农研中心去协助国际交往工作。那时候,中国的经济、政治体制正在改革的初期,干部的流动还主要是组织分配和调动。因此,杜润生同志的帮助使我脱离困境,开始了并不容易的新的探索。
不思量,自难忘。
冠华的墓修成之后,每年的清明,我都去扫墓。为了能安安静静陪伴冠华,我都避开清明的正日,避开蜂拥而至的扫墓人流。每年我去时,公墓的负责人都告诉我,清明节时,来扫墓的人中很多人都要打听“乔冠华的墓在哪里”,许多人上去默哀,还有一次一位上海的文艺界人士在冠华的墓前落泪。我的朋友们逢上去苏州,也有不少专程去东山看冠华。北京医院吴蔚然院长是冠华数十年的挚友良医。1987年他在清明之后去苏州开会也抽空去了东山。回京后他给我寄来两张照片,一张是吴院长在墓前默哀,另一张是照的墓前三束已经枯萎的野花。蔚然同志贴了张条说:“哪位来探视冠华,留下野花三束?”
十年生死两茫茫,
时光又过了几年。1991年春我照例去东山。公墓已换了新的负责人,他陪我上山,就如他的上一位负责人一样,还是告诉我那些动人的故事。使我十分感动的是他还告诉我很多人为了对冠华表示怀念之情,决定也在东山为他们的亲人仿照我设计的冠华墓地修了墓。仅在那一面山坡就总共有二十八个一模一样的墓了。他领我去看了其中三个。同去的朋友开玩笑说我应当申请专利了。我却无限感慨,热泪盈眶。我说:“不,这不是我的专利。老乔的一切都是属于人民的。我感谢人民记得他。”那天我实在很激动,我请大家下去在公墓办公室等我。我一人长久长久地坐在冠华墓前的台阶上。上午刚下过雨,此时的午后阳光从云层后透出万道柔和的光束照耀在满山碧绿的橘树叶上,照耀在山脚下一望无际波光潋滟的太湖上。微风拂来,周围寂无一人,只有我陪伴着冠华。我坐在那里,一切感觉似乎都已凝固。大自然似乎也停在了永恒点上。我望着开始西斜的太阳,想着那太阳几个小时后将从西方地平线上沉没,但再过几个小时,它却又会从东方地平线上冉冉升起。就这样,周而复始,人的生命有限,而大自然是永恒的。庸庸碌碌的人生也许随着西沉的太阳从此了无踪迹,但壮丽的人生会化成阳光的光束循环不止永存于宇宙之间。我慢慢地回头看冠华的墓碑,我刚刚为之上过蜡的金字在阳光照射下熠熠生辉。我似乎有一种大彻大悟,冠华早已不在那黑色大理石的墓碑之下了。他的英魂已融化在这伟大的宇宙间,化作清风,化作细雨,化作阳光。他就这样永恒地存在,无所不在,与我在一起直至永远。
我的这篇文章从初春写到深秋,回忆的线索越拉越长,越拉越远。多少事都一件件在脑海里浮现,有生有死,有爱有恨!我的笔似乎应该停下来了,否则它可以永远地写下去,写下去……现实生活越来越淡化,而过去却越来越清晰。因为是写冠华,我的精神不自禁地在逝去的岁月中徘徊,我也常常想到在东山之巅的冠华。我曾经说过,时光不可能磨灭过去的伤痕,但会使记忆埋得更深。为了活下去,我曾努力把痛苦从心中抹去,用微笑迎接生活的挑战。但我知道那一份思念,那一份不了之情永远时隐时现地在我心中浮沉。前几日,随手翻看闲书,突然翻到冠华喜爱的苏东坡的词,见到他的一首《江城子》,那记录下的是一个相爱至深,但已是天上人间的一对情人的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