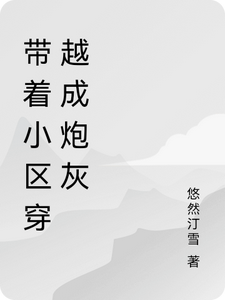迈克尔·罗伯森提示您:看后求收藏(350中文350zw.com),接着再看更方便。
屋子里堆积的书本、报纸、杂志,加上洗衣房里罐装的纤维颜料和一瓶瓶染色剂,通通助长了火势。火焰温度太高,她所有房间里的“收藏品”最后都被烧成了一堆白色灰烬。
格雷西生前常常赌咒说,要想她离开这座房子,除非把她装进松木做的骨灰盒里。未承想,到了最后,她连骨灰盒都用不上,一把簸箕就够了。
那时我早已决定不当医生。只不过我不太确定,如果不做医生,我还能做什么。我有很多疑问,却没有答案。我想知道,为什么格雷西会那么惧怕这个世界。然而,更大一部分原因在于,我想知道有谁本来可以帮到她。
在我攻读学位的四年里,父亲一逮着机会就奚落我,叫我“心理学家先生”,或者揶揄我的诊台和墨迹测验<a id="commentRef_7220" href="#comment_7240"><sup>[2]</sup></a>。我在《英国心理学杂志》上刊登了广场恐怖症理论,他既没有称赞我,也没有和其他家庭成员提及这件事。
自那时起,他便对我的事业不闻不问。我毕业后离开了伦敦,在默西塞德卫生局找了份工作。我和朱莉安娜搬去了利物浦——船首扁扁的渡轮、工厂烟囱、维多利亚时代的雕像,以及空空如也的工厂。
我们住的大楼像一座寒碜的教管所,外墙是一层小卵石灰浆,窗户上装有铁条。我们住在塞夫顿公园公交站的对面,每天早上,唤醒我们的是柴油机刺耳的声响,像极了老烟枪往水池里吐痰时的咳嗽声。
我在利物浦住了两年便决定离开,时至今日,我仍觉得离开那里就像逃离了一处绝境——于我而言,那是一座受瘟疫侵袭的现代城市,住满了愁眉苦脸的孩子,长期失业的游民,还有精神错乱的穷人。若不是有朱莉安娜陪伴,我可能早就溺死在这些人的愁云惨雾里了。
但同时,我又很感激这座城市,因为它帮我找到了归属。人生中第一次,我感觉伦敦就像我的家。我在西哈默史密斯医院干了四年,后来转去皇家马士登医院。我升任为医院的高级顾问,名字被写在马士登医院大厅里的抛光橡木板上,正对着医院前门。讽刺的是,父亲的名字也曾写在那块抛光橡木板上,后来被擦去了,照他的话说,他想“少承担些责任”。
我不知道这两件事有无关联。我也不关心。他怎么想,或者他为什么要做一些事情,早已不是我会担心的事。我有朱莉安娜和查莉陪伴。如今,我拥有了自己的家庭。别人怎么看我,我一点也不在乎——哪怕是他也一样。
<a id="comment_6961" href="#commentRef_6947">[1]</a>约瑟夫的昵称。
<a id="comment_7240" href="#commentRef_7220">[2]</a>全称为罗夏墨迹测验,人格测量工具之一,主要用于临床诊断、精神病研究、人格研究和跨文化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