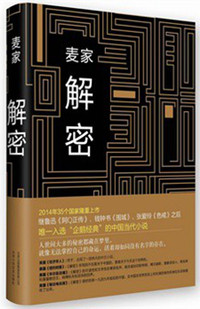常书欣提示您:看后求收藏(350中文350zw.com),接着再看更方便。
“那不走高速啊?”交警纳闷问。
“这不省俩过路费不是?”司机狡辩道。
那交警狐疑地看了他一眼,手电筒照照车身,像是在检查灯光、车轮。司机脸趴在车窗上紧张兮兮地看着,冷不丁那交警的电筒伸到车窗上往里晃,紧张的司机鬼使神差地说了句:“看啥?查车呢还是查人呢?”
这一开口熏得交警直憋气,招手道:“下车下车。”
完了,暴露了。司机期期艾艾地一下车,交警喊着拿过测试仪来,这货冷不丁撒腿就跑,几位临检的交警撵着追。追了没多远,副驾上的王雕、车厢里的几人,“嘭嘭咚咚”往下一跳,像出笼的兔子,嗖嗖乱窜,跑了,高速口登时一片混乱……
几乎在同一时间,两辆靠近贾村的车辆,亮起了灯光。灯光红蓝相间,没有鸣笛,两辆车就那么闪着灯光进村了。
这光景可把两公里外观测的娜日丽看蒙了,愕然地说:“怎么来了两辆警车啊?”
“巡逻的吧,要不抓赌的?”钱加多不当回事。
“巡逻不可能两辆并行,抓赌也不到点啊。”娜日丽凭经验判断着,总觉得哪里不对。她想不出结果来,又升高了车顶的镜头。那两辆车游弋般地驶在村中路上,靠近了他们监控的目标,泊停了。她惊得拿起了步话机喊着:“有情况,两辆警车靠近零号目标……有情况……”
晚了,两车上呼啦下了五六个穿警服的人,砸着门,冲进了78号。院子里一片鸡飞狗跳。
此时斗十方正和车手兄弟围成一圈诈金花,院子里一响,他叼着烟愣了下,紧张了。三儿飞奔向窗口一看,喊了声:“卧槽,雷子。”
他说话间翻窗就往下跳,不过脚一着地就被人摁住打上铐子了。斗十方瞬间暴起,抄着凳子往头顶一砸,直接把头顶的灯砸了。灯一灭,跟着门“嘭”一响,来人破门进来了。往门口跑的几人身上闪着噼噼啪啪的电火花,哎哟哟倒了一堆。进来的人打着电筒,挨个儿拎起来铐上。领头的揪起一个人问:“一共几个人?”
他问的是“沈凯达”。这哥们儿被电得晕头转向,还没回过神来。楼下忽然有人在喊:“这儿,这儿还有一个。”
有人奔向窗口。院子里捉到三儿的那人指着楼上,窗口一伸脑袋,“啊”地痛叫一声,捂着脑袋缩回去了。
原来,斗十方已经趁着黑暗爬到了窗外,正顺着窗户外墙,手拽着窗缝,往围墙上挪。屋里再有追出来的人时,他一脚已经踏到围墙上,跟着一蹲,在墙上搬着板砖,朝着院子里乱喊的那位就是一。那人一躲,不料何三强故意一顶他,那板砖“吧唧”,干脸上了,疼得他“哎哟”捂着脸乱喊。另一个揪着何三强就是一警棍,疼得何三强喊着:“卧槽,哪儿来的警察下手这么黑?”
“拒捕可以当场击毙你,带走。”那警察吼了声,把何三强吓得不敢吱声了。
一行人被押着上了警车。毕竟不是好货色,围观的群众指指点点:老贾家这外甥都不是头回犯事了,抓了活该。村治保主任颠儿颠儿地跑来了,扯着嗓子喊着:“他们不是我们村的啊。警察同志,啥事啊?”
“执行公务,别多问。”为首的上车,摇上了车窗,鸣响了警笛。车缓缓分开人群,驶出村,然后加速,很快消失了……
乱了,长安县高速入口刚追回两个人来,一个司机,一个体力不支没跑多远的胖子,身份还没确定,被铐着刚带进了警车。贾村这个点就出事了,而且出得莫名其妙。凌总队长气得直拍桌子骂娘,训着曾夏让他联络辖区派出所,看哪个不长眼的没报案就乱出警。
情况到了基层就复杂了。加上这拨车手吃喝嫖赌扰民,倒不排除有群众报案招来民警,可查来查去没人报案。满头大汗的曾夏联络了辖区及邻区派出所,都没出警记录,正不知该怎么查时,技侦的结果出来了,喊着曾大队来看。曾夏一看,傻眼了。
同牌号,同型号警车,此时还停在派出所院子里,压根儿就没挪过。
“天哪,假警车!”曾夏嘴里发苦,这伙人玩大了。
“假的?那警察也是……”向小园惊愕道,都不用说出来了,警察……肯定是假的。
真警察在长安县唱假戏,假警察却在市里唱真戏了,隔着两公里被抓走了几个人,零号是否也在内,暂时无法知晓了,几位指挥员霎时乱了方寸,都看向了总队长。
“内讧?!又不像内讧啊。怎么内讧也不可能针对车手,这是财源啊。难道是不同团伙的火并?追踪车和人。虽然我们不知道剧情,但肯定有戏了。”
凌总队长又是紧张,又是焦虑,还带着更大的期待,下了这样的命令。
天网的捕捉焦点,聚焦在那两辆警车上了。自贾村开始,一组追踪,一组回溯,搜索地双向扩大十公里,搜索时间段内出现的同型号车辆,一辆一辆刨出来。
搜索四十分钟后依然无果,紧张和焦虑弥漫在经侦信息中心。凌总队长在走廊里一遍一遍踱着步等,不时地看那部老式电话,期待着它下一刻能响起。
可惜事与愿违,它一直静默着,静默着……
峥嵘方显,若隐若现
“有情况了!”
角落里技侦台席有人喊,焦急等候的专案组成员目光齐齐射向角落那一台席,那是蜻蜓KTV的监控信息。专案组的几位围上来看,前方外勤传回来的信息是几帧画面,消失数日的黄飞来了,他乘了辆普通的轿车,在下车进KTV时,被外勤捕捉到了影像。看来对车手团伙的“技术性动一动”起作用了。
凌总队长的思路似乎被这个情况点了一下,他点评道:“看来这个KTV是诈骗团伙的桥头堡,人多眼杂的环境反而成了他们最好的掩护啊……这个消息惊动了谁,那谁和本案就应该有最直接的关联。但即便这个人出现,我们也未必认识啊。”
这是个自相矛盾的判断,明知道他就在人群里,但在那种环境里,你又能知道他是谁?
这个情况尚未消化,又出现了更大的惊喜。可能是事急忽略了细节,又一位重量级的人物在距离KTV三公里的交通监控上被体貌识别软件捕捉到了。“嘀嘀”的告警音响起,识别软件在模糊的画面里捕捉到了车里副驾上的人。
短发,五十岁左右,长脸,坐在副驾上正拿着手机打电话。捕捉软件信息显示,这个人和中州警方恢复的嫌疑人肖像近似度达到百分之七十,他的名字是:杜其安。
相貌迅速被过滤、放大,向小园飞快地掏出手机瞟了眼,把最早户籍档案里杜其安的照片和此人比对,这个发现让她兴奋得有点手发抖。曾夏在一旁讶异地瞄了向小园一眼,犹豫地说:“这就是你说的,那什么具备互联网+思维的老派江湖骗子?”
“对,乘坐的是蜻蜓KTV的车。您不会还坚持认为我们两地的案子关联不大吧?”向小园道。
曾夏讪然一笑,很大方地迎合了一下向小园的骄傲。他换了个角度问道:“以您提供的信息,傻雕和杜其安原本就以叔侄相称,黄飞又是跟着杜其安干活儿的,有没有可能仅仅是傻雕本人的事惊动了这两位熟人?”
刑侦上的人抬杠惯了,想方设法提出可能性的目的在于排除这种可能性。向小园理解他们的说话风格,摇摇头道:“我给不出答案。也许可能,也许不可能;也许是巧合,也许不是巧合……三个人同时跑出来,在同一地点碰面算一次巧合;这次长安县临检傻雕给惊了,捎带着这俩也惊出来了,是第二个巧合;长安在侦查的诈骗团伙案,把三人都关联起来了,算是第三个巧合吧。”
巧合多了,只有一种解释:嫌疑。
当然,也仅限于嫌疑。技侦反查车辆,车直接开到蜻蜓KTV停下了,下车的杜其安顺手扣上了夹克风帽,低着头。那种打扮和姿势,恐怕没有哪个角度的摄像头能拍到他的相貌。曾夏脱口道:“高手,这绝对是个高手。”
“这就看出来了?”邵承华好奇地问。
“我是指规避监控的高手。你看,他的动作几乎是下意识的,下车快走一步,恰好和司机错位,司机的角度就对着KTV的监控探头,虽然那个探头对他没有威胁,可他仍然下意识地躲避了……实践中已经养成这种反侦查习惯的人,基本都是高手。”曾夏解释道。初识杜其安,他就兴趣浓厚了。
向小园讪讪地补充了句:“不怕您笑话,我们在中州都没有找到他的监控记录,根本无法还原他的行动轨迹,最后技术定位的地方是一处民宿。他们谨慎到连住过的房间都用酒精喷洒过,我们提取DNA确认都花了好一番工夫,到现在都无法确认。”
“有意思。”曾夏听得面泛微笑了。警匪对决,只有同等量级的对手才能唤起双方的兴趣,那现在八成就是了。他指着屏幕上的背影道:“这个人,这么快得到消息,看来一直窝在长安。”
“嘶。那意思是,他避开了所有的天网节点?”凌总队长讶然道。这是天网首次捕捉到他的行迹,那之前没有捕捉到,只能有两种情况:一种是人根本不在长安;一种是避开了所有公共监控。如果是后者,那他此行的目的就昭然若揭了。
“肯定在长安。连傻雕和黄飞都是时隐时现,很难找到行踪,那他们的上一级,水平就应该更高了。”曾夏道。
邵承华听得瞪大了眼,愕然道:“这么诡秘啊?”
“再诡秘也得出来透气啊。看来今天有戏了……这个人。”凌宏业眼睛瞪圆了。技侦在剪切着出入KTV的人群,又一个特殊的人出现了,西装、背头、消瘦而精干。其他人愣着,面面相觑,不知道什么人会让凌总队长色变。片刻后,凌宏业呼了口气,压抑着惊讶道:“资料里有。他叫郑远东,皇城府楼盘开发商,咱们经侦总队搞过一次团购住房,和他直接打过交道。他算不上多富吧,可也算得上是有头有脸的人物了。”
“兴许,就是来玩了吧?毕竟他是这里的大股东。”邵承华不愿以最大的恶意揣度这类有头有脸的人物。
“那这就又多了一个巧合,早不来晚不来,偏偏在两处车手出事的同一时间段来玩。”向小园幽幽补充了句,更像是补了一刀。现在即便是真巧合,也看上去有嫌疑了……
一道昏黄的灯光自远而近移动,黑暗中看不清。待再近一点,影影绰绰的是辆摩托车。摩托车放缓了速度,灯光下一扇铁门洞开,那车直驶而入。随着铁门关闭,四周又陷入一片黑暗。
摩托车引擎声停了,车手叽里呱啦小声和两个人耳语几句。里面的人似乎是放心了,这才开了灯,晃着房间中央的两辆面包车。几人合力往下抬着一个车宽长短的警灯,又有人仔细把车门上的胶给擦了,顺便又换下了车牌。
“妈的,假警察。”
何三强心里暗叫苦也,虽然他被蒙着头,可在路上就听到动静了。车顶响肯定是卸警灯,在车身上剐蹭,肯定是撕“公安”的标志。那时候就知道来不及吃后悔药了,现在就更没机会了。
好不容易等到忙完了,听到脚步声朝他走来,跟着脸一凉,头套被摘了。而这些换了警服的人已经戴上了头盔。当头的一位掀起面罩镜蹲了下来,后面还站着几位,在把玩着臂粗的镐把。这地方看上去像是什么仓库或者车间,堆着满地家伙,想想接下来要发生的事,就让几位被抓的浑身起鸡皮疙瘩。
“跪直喽。问你,叫什么?”对方蹲下问何三强。
“何三强。”
“干车手活儿多久了?”
“没几天。”
“取过多少钱?”
“没多少。”
“老大是谁?”
“跑了的那个。”
那人不问了,起身一示意,后面的咣一镐把就敲在何三强背后,疼得何三强惨叫一声倒在地上,浑身痉挛着,抽搐着,吓得剩下那几位直哆嗦。
“问你,你叫什么?”
“‘沈……沈凯达’。”
“干车手这活儿多久了?”
“一……个月不到。”
“去过几个地方?”
“十几个地方,差不多全省跑遍了,还出过省,去过三门。”
“取过多少钱?”
“每次五六万,最少四万,具体我记不清。”
“老大是谁?”
“跑了的那个,斗……斗十方。”
“不过!上家伙!”
那人一喊,后面的镐把就上来了,吓得“沈凯达”一下子扑在地上恐惧地喊着:“别打!别打!他真是我们大哥,我没撒谎!”
“我问你老大是谁。老大能和你们住一起?”那人站着,顺便踩住了“沈凯达”的腿弯,踩得“沈凯达”杀鸡般尖叫着,边叫边喊着:“饶命!饶命!我也不知道是谁。好像取出来的钱都是给KTV的牛老板了,我不认识啊!只有斗十方认识!”
“哦,这不就对了?”那人饶有兴致地蹲下来,顺手拍着“沈凯达”的脸蛋谑笑道,“牛老板叫牛金。你不认识他,他可盯你们盯得很紧,还在你们身边放了个探子哦。想看看吗?”
有人亮出手机。“沈凯达”一看眼直了,居然是在贾村,是何三强上车的照片。车里那位他确实不认识,不过应该是所谓的“牛老板”。让自己看是什么意思?他茫然不解。那人又问着:“见过没有?”
“真没有。”“沈凯达”道。
“嗯,这是实话,继续,还干过什么坏事?”那人用戏谑般的口吻问着。
一迟疑,就有人踩上来了。“沈凯达”被逼得竹筒倒豆子般地开始交代干过的坏事了。还真别说,是人就有长处,“沈凯达”屡次进入传销组织被一骗再骗,落下个本事,说起话来滔滔不绝。那些人被他绘声绘色的描述吸引住,都忘记上刑罚了……
厢货车出事的消息是王雕打电话通知的。等知道这个消息,牛金联络何三强、斗十方俱告失败,派人去打听,又得到一个让他差点心梗的消息:贾村那个点被警察端了,抓走了好几个人。
这一下可是心神失守了,能联络的人他联络了一遍,此时都聚到了蜻蜓KTV四层,等着进一步的消息。人陷到警察手里一个两个可能问题不大,但两头同时出事,就让这些哪怕貌似和“车手”无关的人也坐不住了。
最坐不住的当然是牛金了。他又一次拍着桌子道:“各位,各位,赶紧想个辙啊。你们都没事,可那带头的认识我啊,他是把钱交我手里的。”
“问题不大。现金,谁能拿出证据来?”黄飞安慰道。
牛金咬牙,蹦了句:“你不至于认为,法治已经好到警察只讲证据了吧?”
“这不还没到那一步呢吗?傻雕说了,就是临检,还是交警。你找的什么人哪?好死不死酒驾,这不找死吗?”黄飞怒道。
这把牛金给憋住了。他愁苦地把眼光投向了郑老板。这位郑老板看看牛金,看看杜其安,抬眼示意着:“杜老板,从进门您还没说句话呢。”
“情况不明,我没啥可说的。”杜其安道。说话时眼珠子都没动一下,不知道是因为冷静,还是僵硬。
牛金苦着脸说:“等情况明了,就更没啥可说的了。”
“那你准备怎么办呢?”杜其安冷冷地问。
“没找上我,那没事;找上我,扛到啥时算啥时吧。关键是那个姓斗的,其他人咬不出我来。”牛金梗着脖子道。
“咬出来,你也交不出这么多钱来。你自己想好,不是扛到啥时算啥时,而是扛死喽。真出事只有两种情况:一种是人进去,钱还在;另一种是,人进去,钱没了。”杜其安冷冷地道。
两个艰难的选择让牛金颓丧地说着软话:“郑总,老杜,我在台前收的钱可是输送给大伙了,要不皇城府早倒闭了,就连KTV都够呛啊。黄赌毒查得越来越严,没这号来钱,就唱唱歌、喝喝酒,三天两头还得被检查,能赚多少钱啊?不能拿钱了大家都高兴,出事了,都这么等着我进去啊。”
“不是还没到那一步吗?胡说些什么呀。”郑总说话了,明显中气不足。
郑远东又一次看向杜其安,小心翼翼地问着:“老杜,很严重吗?”
“想听实话吗?”杜其安道。
“当然。”郑远东道。
“实话是,什么事也没有。”杜其安冷冷地道。
没有?!余众惊讶地看着他,无从明白。
“这可能是一个意外。否则犯那么大事,怎么可能只摁了个司机?其他人都跑了,你们不至于认为你们手下那几块料,比刑警的素质还好吧?在他们手底下,跑得了?”杜其安反问。
咦?好像也对,取钱这么大的事,出事不至于这么稀松平常啊。
牛金的心放下了一半,他出声道:“那贾村呢?那儿可是全端喽。”
“那就更不对了。百分之八十的车手都是在取钱时遭遇埋伏被警察逮了现行,一般都是人赃俱获,这次当不当、正不正,趁空闲时间抄了老窝。没证没据的,你准备把警察难死啊?就算对方素质再低,也应该是跟踪着,等他们犯事时动手啊?”杜其安分析道。
这让郑远东的紧张散去了一半。他反问着:“是不是以前哪次出了纰漏?”
“不会。而且这也不符合警察办案的规程啊,抓一个团伙怎么不得把周边的群众、治保走访一遍?那治保你不是认识吗?警察传讯他了吗?”杜其安问牛金。
牛金摇头:“没有啊。要是有,他早就告诉我了。”
“肯定也没有把三儿那家里搜一遍吧?”杜其安问。
“没有。抓了人就走了。那屋老贾和治保还是亲戚。”牛金道。
“这就更不对了。赃款赃物或者违禁品什么的都不查查?”杜其安问。
黄飞一摸脑袋,恍然大悟地道:“我也觉得有什么地方不对劲,就是说不上来,安叔这么一讲,我明白了。”
“什么意思?”牛金好奇问。
“是不是被人黑了?”黄飞愕然道。
“这才是正确答案。我之所以露面,就是想安抚一下大家,该干什么还干什么,自己的阵脚不能乱。”杜其安道。
“那黑咱们的,能有谁啊?这……”牛金看看黄飞,一时想不起来究竟是谁。
“该来的,总会来。”杜其安道。
这时候,牛金的电话响起来了,他没接,等铃声停了,他发现大家都在看着他,他犹豫道:“是老费的电话。”
“接吧,应该是来了。”杜其安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