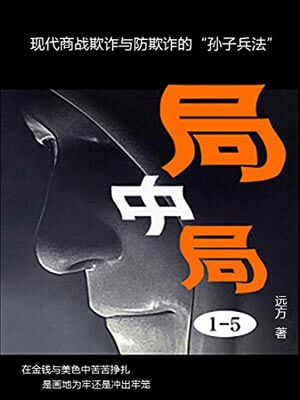19.哈里·戈贝尔事件 (第4/5页)
若埃尔·迪克提示您:看后求收藏(350中文350zw.com),接着再看更方便。
在开车从警察局总部前往监狱的路上,我从收音机里得知,几乎整个美国所有的州都把哈里写过的书从教学大纲里面剔除了出来。这简直是谷底的谷底:在不到两个星期之内,哈里失去了曾经拥有的一切。从今往后,他就只是一个被明令禁止的作者,一个被学校抛弃的教授,一个全民皆恨的对象。不管最终调查和审判的结果如何,他的名字已经被永远打上了污点。以后如果有谁再谈论起他的那本著作,就不可能不提及他跟诺拉度过的那个引起大家巨大争论的夏天;而为了避免遭到非议,各种文化活动的组织者以后肯定再也不敢把哈里·戈贝尔请去做嘉宾了。这对他来说,简直就好像是一种文化的电椅。而更糟糕的是,哈里他自己完全明白他目前的处境。在进入监狱的会客室之后,他对我说的第一句话就是:
“他们是不是要杀了我?”
“没有人会杀你,哈里。”
“可是,我不是已经死了吗?”
“不,你还没有死!你是伟大的哈里·戈贝尔!知道摔倒的重要性,你还记得吗?跌倒并不可怕,因为跌倒是不可避免的,重要的是要知道如何站起来。而我们这一次也一定能够重新站起来的。”
“你真是一个很棒的家伙,马库斯。不过,友情就好像是一个马眼罩,让你看不到事实的真相。归根结底,问题其实并不在于我是否杀了诺拉,或者德波拉·库佩,或者甚至是肯尼迪总统。问题在于我跟这个未成年少女有了不寻常的关系,而这才是不可原谅的行为。至于这本书,我是不是有什么毛病才会去写这本书啊!”
我重复着自己的上一句话:
“我们将会重新站起来的,你就看着吧。你还记得当年在洛威尔,在那个改造成地下拳击场的货仓里,我是怎么遭到痛击的吧。你看,那一次之后,我重新站起来,感觉从未这么好过。”
他在脸上勉强挤出了一丝笑容,接着问我道:
“那你呢?还有收到新的威胁信吗?”
“这么说吧,每一次我回鹅弯的时候都会想,那里到底还有什么在等着我。”
“找出是谁干的,马库斯。找到他,然后给他雷霆一击。一想到有人威胁你,我就感到难以忍受。”
“别担心。”
“你的调查怎么样了?”
“有一些进展……哈里,我开始写一本书了。”
“那太好了!”
“这是一本关于你的书。我在里面提到了你,还有巴若斯大学。我还讲了你跟诺拉的故事。这是一本关于爱情的小说。我很欣赏你们的爱情故事。”
“这个人物构思不错。”
“那么,你同意我这么写了?”
“当然,马库斯。你知道,你曾经可能是我最亲近的朋友之一。你还是一个非凡的作家。对于成为你下一本小说的主角,我感到很荣幸。”
“为什么你要说‘曾经’?为什么要说我‘曾经’是你最亲近的朋友?我们一直都是这样的,不是吗?”
他露出了悲伤的神情:
“我是实话实说。”
我抓住了他的双肩:“我们永远都是朋友,哈里!我不会抛下你不管的。这本书,就是我坚贞不渝友情的见证。”
“谢谢,马库斯。我很感动。不过,友情不应该是你写作这本书的动机。”
“怎么说?”
“你还记得,在你获得巴若斯大学文凭的那一天,我们进行的那次谈话吗?”
“是的,我们一起在校园里走了很长一段距离。我们一直走到了拳击房。那个时候你问我打算干什么,我回答说打算写一本书。于是,你问我为什么要写书。我回答说,我写书是因为我喜欢,而你则对我说……”
“是啊,我对你说什么?”
“你说,生活本没有太多的意义,而写作赋予了生活意义。”
“就是这样,马库斯。这就是你有几个月曾经犯下的错误。当巴尔纳斯基要求你交出新的小说底稿的时候,你那个时候写作只是为了写一本书,而不是要赋予你自己的生活以意义。只是为做而做,从来也不会有意义:因此你有一段时间一句话也写不出来,这也就一点不奇怪了。写作的天赋并不是体现在能否正确地写好,而是体现在能否赋予生命以意义。每一天,有人诞生,有人死亡。每一天,一群又一群不知名的劳动者在灰色的建筑物里面来来去去。幸好还有作家。我相信,作家过着比其他人都更紧凑的生活。马库斯,不要以我们友情的名义创作。写作是因为这是你把细微渺小被称作‘生命’的这个东西转变成一段有价值有意义的人生经历的唯一方式。”
我久久地注视着他,心里有一种感觉,就好像在听着老师给我上的最后一堂课。这种感受真是让人难以承受。最后,还是他开了口:
“她喜欢听歌剧,马库斯。把这个写到小说里。她最喜欢的曲目是《蝴蝶夫人》。她说过,最美的歌剧讲的都是悲伤的爱情故事。”
“谁?诺拉?”
“是的。这个15岁的小姑娘喜爱歌剧到了极致。在她自杀未遂之后,她到一个叫‘夏洛特山’的康复中心待了十几天。这种地方在今天是被称作精神疾病诊所吧。那几天,我总是偷偷地去看她。我给她带去了一些歌剧音乐碟,在那里用一个便携式电唱机放出来。她被感动得热泪盈眶,她还说,如果不能到好莱坞成为演员,她就要去百老汇做一个歌手。然后我就跟她说,她将会是美国历史上最伟大的女歌手。马库斯,你知道吗,我一直以为诺拉·凯尔甘本来有可能在这个国家留下她的印记……”
“你是否认为她的父母有可能会对她不满?”我问道。
“不,我觉得这不太可能。别忘了还有那份书稿,还有书稿上面的留言……不管怎么说,我很难想象是大卫·凯尔甘谋杀了他自己的女儿。”
“不过,她挨了那些打……”
“那些被打的痕迹嘛……那是一件很古怪的事情……”
“还有亚拉巴马呢?诺拉跟你提起过亚拉巴马吗?”
“亚拉巴马?凯尔甘一家就是来自亚拉巴马,是的。”
“不,还有其他的事情,哈里。我相信,在亚拉巴马发生了什么状况,而这件事呢,很可能跟他们离开亚拉巴马有关。不过,我也不知道是什么事……我不知道还能找谁去了解这方面的情况。”
“我可怜的马库斯。我感觉你越是深入挖掘这个事情,碰到的谜团就越多啊……”
“确实是这样的,哈里。另外,我还发现奎因夫人知道你跟诺拉之间的事情。她跟我说的。在诺拉试图自杀的那一天,她去了你的家里,非常气愤,因为她为你组织了一场花园聚会,而你放了她的‘鸽子’。可是你当时不在家,于是她就去搜了你的书房,在那里,她找到了你刚写下的一张关于诺拉的字条。”
“既然你现在提到了这个,那我想起来了,我确实丢了一张字条。我后来找了很久都没找到。我还以为是把它搞丢了呢。这在当时令我觉得非常惊讶,因为我一直都是很有条理的。她拿那张字条干了什么?”
“她说她把字条留了起来……”
“那些匿名信,是她?”
“我觉得不太可能。她甚至从来就没考虑过在诺拉和你之间真的有可能发生什么爱情。她只是以为你对她想入非非。说到这里,我想知道普拉特警长有没有问过你关于诺拉失踪的事情。”
“普拉特警长?从来没有。”
这很奇怪:为什么普拉特警长在塔玛拉告诉了他关于哈里的事情之后,从来没有在调查诺拉失踪一案中审问哈里呢?接下来,我又提到了斯腾的名字,但是并没有说他跟诺拉的事情,也没有讲到那幅画。
“斯腾?”哈里对我说,“是的,我认识他。他曾经是鹅弯那房子的主人,我是在《罪恶之源》大获成功之后从他手上买过来的。”
“你很了解他吗?”
“没有啊,我和他在1975年夏天见过一两次。第一次是在夏日舞会上,当时我们就坐在同一张桌子旁边。他为人友善,我在那次之后又和他见过几次。他很富有,并且相信我的才华。他对文化颇有研究,总之,他是一个颇有深度的好人。”
“你最后一次见他是什么时候?”
“最后一次?那应该是我在1976年买他房子的时候了,但为什么你突然和我提到这个人?”
“没什么具体的原因。哈里,快告诉我,刚才你说的夏日舞会是不是就是那个塔玛拉想让你带着她的女儿一起去参加的舞会?”
“就是那一次。最后我是一个人去的,那是多么美妙的一个夜晚……当时我得了摇彩一等奖,奖品是到马尔莎葡萄园度假一周。”
“你最后去了吗?”
“当然。”
那天晚上,在回到鹅弯之后,我收到了罗伊·巴尔纳斯基给我发来的一封邮件,里面就我新书给出的报价,任何一位作家都不可能拒绝。
发件人:r.barnaski@schmidandhanson.com
时间:2008年6月30日 19:5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