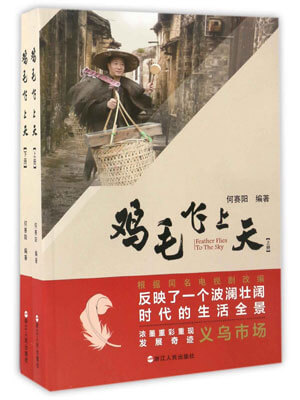宫部美雪提示您:看后求收藏(350中文350zw.com),接着再看更方便。
外立依旧垂着头,冷不防地呢喃道。话一出口就立刻失速,然后如尘埃飘落。第一次见到他时也是这样,才刚说了什么,就把自己说的话和店前步道上散落的落叶及纸屑扫成一堆,想要装进簸箕里。
“美知香和她母亲都说你没有任何错。知道你这么自责,她们俩都很心疼,也很担心你。”
外立放在膝上的手猛然握拳。那拳头也很瘦弱。
“要不要跟我一起去上炷香?如果你想去坟前祭拜也行。不要写信了,直接和美知香见一面吧。如果能和她当面谈一谈,我想你的心情应该会轻松许多。”
外立依旧低着头,不停地眨眼。他双颊凹陷,稀疏的睫毛格外醒目。我暗忖他该不会哭出来吧,这样看着实在叫人于心不忍,我不禁移开目光。
外立把长袖毛衣卷到手肘处,裸露的手臂上起满了鸡皮疙瘩。玄关处的确很冷,门不仅开关不便,门缝又夹着门铃的电线,所以拉门根本关不紧。冷风从门缝吹过,我穿着大衣还好,可是对外立的身体恐怕有影响……他虽然依然保持端正的坐姿,但在发抖。那种颤抖方式显然不只是因为寒冷。
我连大气也不敢出,缓缓又悄无声息地抬起头看着垂头的外立。我一直憋着气,因为怕如果不小心一吐气,会忍不住叫出声来。
“都是我造成的。”他说。他说那是他的责任,是他的错。
这些话,我和古屋母女及萩原社长听了之后都没有当真。
我以为这一切都是因为个性认真的外立有一颗敏感的心,因古屋的横死而受伤,变得过度自责。
我这种想法绝非轻率的自以为是,想必人人都会这么想吧。外立怎么可能有错?当他说“是我的错”时,怎么可能从中品味到不同的意味?
那样的事,谁都想不到。那样的事!不会吧。
他在“拉拉·巴西利”上过班,有机会把掺有氰化钾的饮料放进冷藏柜。他有机会,绝对有。可是,他没有理由做那种事。
这次轮到我感觉浑身僵硬。出乎意料的念头占据脑袋,害我头昏眼花。
我还在猜想是不是他发出如变调笛音般的声音在吸气,他忽然开始猛咳,激烈地扭动身体,喘个不停,一边把手伸进口袋取出吸入式喷剂。我伸手想拍抚他的背,但直到他吸药勉强稳定下来为止,我始终只是心慌意乱地看着。
“对……对不起,我没事了。”外立一边调整呼吸,一边想收起喷剂,然而却没拿好,掉到了地上。
我捡起来交给他,接触的刹那间我感到他手指冰凉。“很苦吧。”
“没什么大不了的,真的。”外立那张像是洗晒多次又褪色的旧布般的脸企图朝我微笑,“那就请你帮我介绍古屋小姐,麻烦你了。”说着深深一鞠躬。
我总算可以喘口气,嗯嗯有声地回应。导致哮喘发作的原因有很多,极度紧张应该也算其中之一吧。还有心理障碍及压力。
对于我的造访,外立有什么好紧张的?在这种情况下,到底是什么给他造成压力?
我的心脏响如铜锣。不会吧,不会吧。
幸好我现在不必与外立四目相对。如果看着他的眼,说不定会被他看穿我的心思。抑或他已知道我的想法,看穿了我的心思?他会再度发作吗?抑或他会张嘴述说究竟是什么在折磨他?
一定是我想太多了,不可能有那种事。
“那你什么时候方便?”我问。
外立软弱地歪起脖子。“随时都可以,如果奶奶忽然身体不适就不行,除此之外,我闲得很,反正也没工作。”
“你的身体吃得消吗?”
“没事。不过……”他举拳抹嘴,“年底正是最忙的时候,我怕打扰古屋小姐。等她什么时候方便就可以了。”
“明天就是平安夜。”
脱口而出后,我暗自感到尴尬。外立过的生活哪有平安夜这种节日可言。
“我先问问美知香。那我该怎么跟你联络?发电子邮件可以吗?”
他表示自己没有电脑,并且尴尬地解释他给美知香电邮都是利用附近网吧里的电脑,然后把手机号码告诉我。
“那好,我再打电话给你。你要多保重,打起精神来,知道吗?”
外立送我出去后吃力地关上晃动的拉门。
我撇下他迈步离开。不知为何就是没有那种结束采访可以打道回府的心情,总觉得自己像是遗弃了他,仿佛是我把倾颓的房子、折断的排水管、冷风从门缝灌进的昏暗和室、需要他看护的老太太、衰老多病的气息、阻碍他自由的疾病、困苦的生活和看不见前途的孤独……种种不幸通通推给他。
因为他是外人。
可是,来时尚未同行的麻烦同伴却在我踏上归途时暗藏在大衣底下。是疑惑,是某种难以言喻的直觉产生的不安。
我像被谁追赶似的加快步伐,又回到了萩原货运。社长看到我时惊讶地瞪着眼。
“社长,对不起,我想跟令郎见个面,请问该去哪里找他?”
<a id="note_1" href="#noteBack_1">[1]</a>德国作家,立志改革自然主义的传统戏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