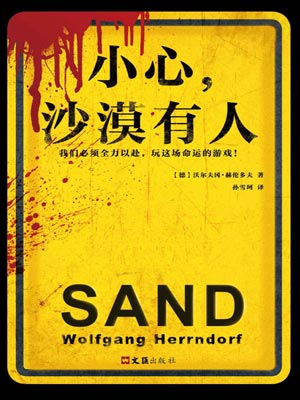斯蒂芬·金提示您:看后求收藏(350中文350zw.com),接着再看更方便。
“好吧,帕姆。”我感到极其疲倦,更别提有多挫败、多气愤了。
“什么好吧?”
“好吧,我听到你说的了,响亮又清楚。没有任何被误解的可能。打消那个该死的念头吧。我只是想救汤姆·赖利的命。”
她没有作答。也没有对我曾熟悉的汤姆作任何理智的解释。我们就这样不了了之。挂电话时我在想:好心没好报。
或许,她也是这么想的。
6
我又气又乏,不知所措。阴霾的天气也不帮忙。我想画画,但画不出来。我下楼去,拿起一本速写本,很快发现自己又开始像多年前接电话时那样乱涂乱画:大耳朵的卡通什穆。我一时恨起,想把本子扔得远远的,电话铃刚好响了。这次是怀尔曼。
“你今天下午过来吗?”他问。
“当然。”我说。
“我还以为下雨——”
“我打算窝在车里。反正我不想缩在这儿。”
“好。但不用计划诗歌朗诵会。她犯迷糊了。”
“厉害吗?”
“我认识她以来最厉害的一次。信号中断,神思飘浮,糊里糊涂。”他深呼吸一次,透过电话线听来酷似大风吹。“听着,埃德加,我真不愿意这么说,但你能不能在这儿陪她一会儿?四十五分钟,最多了。包伽廷家的桑拿室出毛病了——该死的加热器——过来修理的伙计要告诉我哪儿是总开关之类的。当然,还要签他的工作单。”
“没问题。”
“你真是白马王子。亲死你的香肠嘴。”
“干你一百回,怀尔曼。”
“耶,每个人都好爱我,这是我的诅咒。”
“帕姆给我来电话了。她和我朋友汤姆·赖利谈过了。”考虑到他们之间发展到了这一步,很奇怪我还能称汤姆为朋友,但,管他呢。“我认为,她相信他准备自杀了。”
“那挺好啊。为什么我觉得听来还有下文呢?”
“她想了解我怎么知道的。”
“不是怎么知道她和这小子乱搞,而是——”
“我怎么能在一千五百公里之外未卜先知猜到他抑郁得要自杀。”
“哈!那你怎么说的?”
“当时没有好律师在场,我只能照实说。”
“然后她觉得你是个小疯子。”
“不,怀尔曼,她认为我是个超级大疯子。”
“有区别吗?”
“没有。但她会好好想想的——照我说,帕姆是美国奥林匹克思考团队的主力选手,你最好信我——而我担心,我干的好事会在小女儿面前曝光。”
“我猜想,你太太是想找个替罪羊。”
“这个猜想挺靠谱的。我了解她。”
“那可就糟了。”
“那会搅得伊瑟的世界天翻地覆,可她不该被打扰。在她和梅琳达的生活里,汤姆一直都是个好叔叔。”
“那你就必须说服你老婆,你真的是亲眼看见,而你的女儿和此事毫无牵连。”
“可我怎么能说服她呢?”
“要不,你跟她说些你绝对没法知道的事情?关于她的小秘密?”
“怀尔曼,你疯了!我没法操控那种事发生!”
“你怎么知道你不行?朋友,我不得不挂电话了——听起来,伊斯特雷克小姐的午餐刚刚砸到地板上。我们待会儿再见?”
“好的。”我说。我打算说再见的,但他已经挂了。我也放好电话,回想我把帕姆的园艺手套放在哪儿了,印着手拿开的手套。如果我找得到,怀尔曼的主意倒也不算太疯狂。
我满屋子找,却一无所获。大概我画完《福利之友》之后就扔掉了吧,但我不记得这么做过。我现在什么都想不起来了。只知道画完后我再也没见过它们。
7
那天下午,怀尔曼和伊丽莎白称为“瓷亭”的房间里荡漾着令人忧伤的亚热带冬季天光。现在,雨下得更大了,重如鼓点般一阵阵打在窗上和墙上,大风也刮起来,把围绕杀手宫的棕榈树丛吹得哗啦啦直响,也搅得墙上的光影翻腾不定。自从我第一次来这儿后,还是头一回看到长桌上的瓷人们凌乱无章;没有了舞台造型,只是一群人、动物和建筑的混合。一头独角兽和一个黑脸人并肩站在倾覆的学校大楼旁。如果今天的桌景也有剧情可讲,那准是部灾难片。塔拉庄园式的宅邸立在“甜蜜欧文”曲奇饼干桶上。怀尔曼已经解释过了,如果伊丽莎白吩咐我做什么,我该如何应对。
老太太坐在轮椅里,身体朝一边歪,眼神空洞地俯瞰玩具桌上的一团糟,平日里,那个小世界总是很整洁的。她穿着一条蓝裙子,和脚上大号的蓝色查克·泰勒款的匡威鞋几乎是一个颜色。她萎靡瘫软地坐靠一边,船形的领口也歪向一边,露出象牙色的内衣肩带。我不禁思忖,早上是谁把她打扮成这样的,她自己还是怀尔曼?
一开始,她的言语还算有条理,用正确的名字称呼我,询问我身体可好。怀尔曼去包伽廷家时,她跟他说再见,还让他记得戴帽打伞。都挺好。但十五分钟后,当我把茶点从厨房端出来后,情况就变了。她正瞅着一个角落,我听到她在悄悄说话:“回去,回去,苔丝,你不属于这儿。让那大男孩走开。”
苔丝。我听过这个名字。我发挥自己的发散性思维,寻找记忆里的关联点,果然摸到了切入点:报纸的头条标题是<b>她们走了</b>。苔丝是伊丽莎白的姐姐,双胞胎之一。怀尔曼跟我说过的。我想起他说:估计她们都淹死了,便觉不寒而栗。
“拿给我。”她说着,手指曲奇饼干桶,我照做了。她从口袋里掏出一个包在手帕里的小瓷人。她把饼干桶的盖子打开,用狡猾又迷乱的眼神瞧了我一眼,再把小瓷人扔了进去,落进空罐里时,发出“嘣”一声响。她摸索着,想要把盖子盖上,我想帮忙,她却把我的手拨开。然后,她把它递给我。
“你知道该怎么办吗?”她问,“那个……那个……”我听得出她脑海里的挣扎。词语和你捉迷藏,话到嘴边就溜走。嘲笑她吧。我可记得别人嘲笑我时,我是如何怒火中烧的,所以我宁愿等待。“他,有没有告诉你该怎么做?”
“是的。”
“那你还等什么?把这婊子拿走。”
我抱着饼干桶,走到网球场边的小水池旁。鱼儿欢快地跃出水面,它们比我更喜欢下雨天。长椅旁有些小石块,恰如怀尔曼所说。我小心翼翼地扔了一块石头进去,不想砸伤哪条鲤鱼(“你大概不会相信她听得到扑通一声,可她的耳朵尖着呢”,怀尔曼这样对我说的)。然后,我抱着饼干桶,以及依然在其中的小瓷人,回到大屋里。但我没有走入瓷亭,而是直接去了厨房,揭开盖子,取出包在手帕里的小人。这个举动不在怀尔曼交待的紧急情况处理守则之列,但我很好奇。
那是个女人的瓷像,但脸部被削掉了,只剩一片碎屑,空白的脸。
“谁在那儿?”伊丽莎白尖叫起来,吓得我原地跳起来,差点儿把脆弱的瓷像跌落在地。一旦失手,它必定会在瓷砖地上分身碎裂。
“是我,伊丽莎白,”我朝瓷亭的方向喊了一声,把瓷像搁在流理台上。
“埃德蒙?还是埃德加,唉,你到底叫什么?”
“是埃德加,没错。”我走回了瓷亭。
“你把我吩咐的事儿处理妥当了吗?”
“是的,夫人,我办妥了。”
“我吃过点心了吗?”
“吃过了。”
“那好吧。”她叹了一口气。
“你还想要点别的吗?我想我可以——”
“不用了,多谢你,亲爱的。我肯定火车马上就要到了,你知道的呀,我不喜欢吃得饱饱的上火车。我总是会坐反座,吃饱了肯定会晕车。你看到我的饼干桶了吗,甜蜜欧文的曲奇罐?”
“我想是在厨房里吧。要我拿来吗?”
“这么潮湿的日子里就不用啦,”她说,“我以为我让你把她扔进池子里了,池水管用,但我改主意了。这么潮湿的日子,看起来没必要了。慈悲不是出于勉强,你明白的,恰如甘霖从天降落。”
“自天堂。”我把这经典老话说完。
“对呀,对呀。”她挥挥手,好像这个补充无关紧要。
“你怎么不摆你的小瓷人了,伊丽莎白?今天他们全都混成一团了。”
她瞥一眼长桌,一阵强风突然猛烈刮来时,又抬头看了看窗,“妈的,”她说,“我真他妈想不通。”转而又用深深的怨恨说,“他们都死了,只留下我来干这事。”我真没想到她能有这么恶狠狠的语气。
她记忆失调、语词疏漏乃至爆出粗口,这可能会让别人厌恶透顶,但我决不会;我太理解了。或许,仁慈是强求不来的,芸芸众生如你如我靠着这种信条生生死死,但是……仍会有这种事等着我们去忍受。是的。
“他根本就不该碰那东西,但他不知道呀。”她说。
“什么东西?”
“什么东西,”她重复我的话,点点头,“我要等火车。我要在大男孩来之前离开这地方。”
之后,我俩都陷入沉默。伊丽莎白闭上眼睛,坐在轮椅里打起盹来。
为了给自己找点事情做,我起身离座——那把椅子要放在绅士俱乐部里才相衬,探身凑近长桌。我捏起一个小男孩和一个小女孩,看了看他俩,再放到一边。我抓了抓不存在的那条手臂,研究眼前毫无头绪的一团乱景。抛光橡木桌上,至少共有一百个小瓷人。或许两百。其中,有一尊女子瓷像,头戴一顶过时的小帽——牛奶女工小帽,我心想——但我也不想要她。帽子不对头,况且,她也太年轻了。我接着找,找到一个长发女子,头发上刷了漆色,她就好多了。头发长了点,也太黑了,但——
不算黑,因为帕姆总去美容院,又称,中年危机时的青春之源。
我攥着这尊小瓷像,真希望我能有栋房子安置她,再有本书给她读。
我想把小瓷人挪到右手——相当自然而然,因为我的右手就在那儿,我能感觉得到——她当的一声落在桌上,没有跌碎,但伊丽莎白的眼睛睁开了,“妈的!火车来了吗?是不是火车叫?拉汽笛了?”
“还没,”我说,“你为什么不再睡一会儿呢?”
“哦,你会在二层楼梯平台上找到它。”她说,好像我刚刚问了她什么,然后又合上眼睛,“火车进站了就叫醒我。我真讨厌火车站。留神大男孩,那个婊子操的可能在任何地方出现。”
“好的。”我说。右臂奇痒难受。我探手去掏口袋,希望记事本就在袋里。不在。我把它落在浓粉屋的流理台上了。但这让我想到杀手宫的厨房。我搁曲奇罐的流理台上也有一摞记事贴。我匆匆回到厨房,一把抓过便贴,咬在齿间,几乎是一路小跑回到瓷亭,并已经把我的圆珠笔从前胸口袋里拔出来了。我坐进扶手靠背椅里,飞快地把小瓷人画下来,此时狂风卷雨鞭打在窗玻璃上,伊丽莎白靠在桌子对面的轮椅里,嘴巴微张地打着盹。风雨中的棕榈树影投在四面墙上,犹如蝙蝠翻飞。
我画着画着,没用多久,突然意识到:我正在把痛痒倾泻于笔尖,把它从我的体内倾倒到画纸上。我正在描画的女子是瓷偶,但她也是帕姆。那个女人就是帕姆,同时她也是这尊瓷人。她的头发比我上次见她时长了些,披散在肩头。她正坐在椅子里。什么椅子?摇椅。我离开前,从没在那个家里见过这种椅子,但现在有了。她身边的桌子上放着什么东西。一开始我都不知道那是什么,但它从笔尖下慢慢显形,变成了一只盒子,上面印有文字。甜蜜欧文?你是说甜蜜欧文?不,是老奶奶牌的。我的圆珠笔又在桌上画了什么,在盒子旁边。燕麦曲奇。帕姆的最爱。当我看着它时,笔尖又勾勒出帕姆手中的书。看不到书名,因为角度不对。现在,我手中的笔正在窗户和她的脚之间添画线条。她说是下雪天,但现在雪已经停了。线条代表着阳光。
(焦黑,朋友)
我以为这幅画已经画完,但显然还有两样物事没画。圆珠笔移到画纸的左边,添上了电视机,笔触快似闪电。新电视,和伊丽莎白的超薄平面一样。那下面——
笔尖骤停,落出我手。奇痒消失了。我的手指根根僵硬。长桌对面的伊丽莎白已从打盹变成了沉睡。很久以前,她或许年轻又美丽。很久以前,她或许是某个年轻人的梦中佳人。现在她在打鼾,没剩几颗牙的嘴朝着天花板。如果真有上帝,我认为他需要再加把劲。
8
我知道图书室和厨房里都有电话分机,而图书室离瓷亭更近。我相信,不管是伊丽莎白还是怀尔曼都不会小气到不让我打一通长途电话到明尼苏达。我摘下电话,又握在胸前冷静了片刻。骑士盔甲旁的墙上挂着一组古董兵器,被天花板上几盏漂亮的射灯照亮:长枪筒的前膛枪,看似出自于革命战争时期,还有燧发手枪,温切斯特卡宾枪,还有一把大口径短口手枪,若搁在内河赌船上会更显相得益彰。而悬在卡宾枪上方的,便是我和伊瑟初见伊丽莎白那日她攥着的小玩意儿。两边各有四支,摆放成颠倒的V字。你不能称之为弩箭;它们太短了。好像只有“箭枪”是正确的称呼。箭头锃亮,看来非常锋利。
我心想,你要用这玩意儿,准能把人伤得极惨。然后又想到:我父亲是潜游人。
我把这些想法赶出脑子,拨通了从前家里的电话。
9
“嗨,帕姆,还是我。”
“我不想再和你说话了,埃德加。该说的都说完了。”
“不见得。但这次会很简短。我有位老妇人要照看。她正在睡觉,但我不想离开她身边太久。”
帕姆到底还是好奇的,“老太太是谁?”
“她叫伊丽莎白·伊斯特雷克。八十多岁了,她已有了阿尔茨海默症的前期表现。她的首席陪护正在帮某些人解决桑拿室的故障,我就过来帮忙了。”
“你想在工作日志的好人好事栏里挣颗小金星吗?”
“不,我打电话来是想向你证明,我没有疯。”我带来了我的画,现在正把话筒夹在肩膀和耳朵中间,这样才能拿起画看。
“你干吗这么介意?”
“因为你认定这一切都是伊瑟泄露的,但不是那样。”
“我的上帝啊,你真是不可理喻!如果她从圣达菲打电话来,说她鞋带断了,你一定会飞过去帮她系上一条新的!”
“我也不喜欢你认为我在这边完全丧失了理智,而我没有。所以……你在听吗?”
那头只有沉默,但沉默已经够好了。她在听。
“你刚刚冲完澡出来,十分钟,顶多十五分钟的样子。你穿着家常服,头发披在肩膀上,所以我这么推断。我猜想你依然不太喜欢吹风机。”
“你怎么——”
“我不知道怎么知道的。我打来电话的时候,你坐在一把摇椅里。那肯定是离婚后你新买的。边看书边吃曲奇。老奶奶牌的燕麦曲奇。现在太阳已经出来了,照进了窗户。你有了一台新电视机,平面的那种。”我停了停,“还有一只猫。你养了一只猫。正趴在电视机下睡觉。”
电话那头只有死寂。在我这头,大风呼啸,雨打玻璃。我正想问她是不是还在电话旁,她就开口了,阴沉的声音听来一点儿也不像是帕姆。我本以为她已经伤够我的心了,可我显然是错了。“别再偷窥我的生活了。如果你曾经爱过我——就别再窥探我了!”
“那就别再责怪我。”说这话时,我的声音嘶哑,几乎破不成声。突然,我想起伊瑟准备回布朗大学时,站在三角洲航机楼外的热带烈日下仰头看着我说,你真该过得好些,有时候我都怀疑你是不是真的相信这一点。“这种事发生在我身上,又不是我的错。车祸不是我的错,这也不是。并不是我要这样的。”
她尖叫起来:“难道你认为是我的错吗?”
我闭起眼睛,暗自祈求,随便怎样都好,但求不要以暴制暴。“不,当然不是。”
“那就离我远点!别再给我打电话了!别再<b>吓我</b>了!”
她挂断了。我依然站在那里,话筒搁在耳旁。一段沉默过后,响起响亮的咔嗒一声。随后便是杜马岛所特有的鸟鸣声,今天听来特别沉闷,或许因为小鸟都在雨水下。我把电话放好,站在那里盯着盔甲看。“兰斯洛特爵士,我认为一切进展得非常顺利。”我说。
没有回答,正是我应得的。
10
穿过盆栽摆列两边的廊厅,我回到瓷亭,看到伊丽莎白还在睡,脑袋倾斜的角度还是原样。刚才我还被她尽显老态的鼾声所震惊,现在倒觉得有抚慰人心的奇效;否则,你甚至会以为她断颈坐死在这里了。我想了想要不要叫醒她,决定让她继续睡。无意间,我朝右边瞥了一眼,看向宽宽的主楼梯,突然想到她说过,哦,你会在二层楼梯平台找到它。
找到什么?
或许又是一句胡言乱语,但我也没别的事可做,便迈入廊厅,雨点啪啪地落在玻璃天顶上。要是在简朴人家里,这条带顶棚的小径大概决不会有廊亭的美名。我走上了宽宽的楼梯。离二楼还有五个台阶时,我停下脚步,凝视片刻,再缓慢地往上走。果然有东西可看:一幅巨大的黑白照片镶在窄边金框里。后来,我问怀尔曼,一九二几年的黑白照片怎么可能放到这么大?起码有五英尺高、四英尺宽,并且一点都不模糊。他说,大概是用哈苏拍的,那可是人类历史上最精良的非数码相机。
照片里共有八个人,站在白色沙滩上,墨西哥海湾便是辽阔的背景。男子高大英俊,大约四十多岁,身穿一套黑色泳装:吊带汗衫,游泳裤,看似当今篮球运动员们的贴身内衣。在他的左右两边站着五个女孩,最大的女孩已到青春年华,最小的那对儿同是一头黄发,面容近乎一个模子里刻出来的,让我不禁想到早年读过的鲍勃西双胞胎的故事。这对孪生姐妹手拉着手,穿着一模一样的游泳服,下摆是镶花边的小裙子。空出来的那两只手里都抓着腿脚摇晃、系着围裙的碎布娃娃,也让我不禁想起瑞芭……空洞笑脸之上黑漆漆的纱线头发一定是<b>红色的</b>。那男子准是约翰·伊斯特雷克,毋庸置疑,而勾住他臂弯的第六个小女孩尚在学步,最终将变成楼下打鼾沉睡的干瘪老妇。白人一家之后,还站着一个黑人妇女,大约二十二岁,头发扎在方巾里。她提着个野餐篮,手臂肌肉鼓起,从这个不容忽视的细节来看,篮子一定很重。她的前臂上套着三个银手镯。
伊丽莎白在微笑,伸出胖乎乎的小手,指着拍摄这张全家福的人,且不管是谁。别的人都没有笑,尽管男子的嘴边似有若无隐着一丝笑意,因为他有胡子,很难说他是不是在笑。年轻的黑人保姆绝对是一脸严峻。
约翰·伊斯特雷克一手拉着学步女童,另一只手里抓着两样东西:一是潜泳面罩,二是我在图书室墙上见过的箭枪。在我看来,问题该是这个:到底是不是伊丽莎白穿越了迷雾,以足够清醒的意识将我引上二楼,来到这里?
我没来得及想得更深,楼下前门便被打开。“我回来了!”怀尔曼高声说道,“任务完成了!现在谁来一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