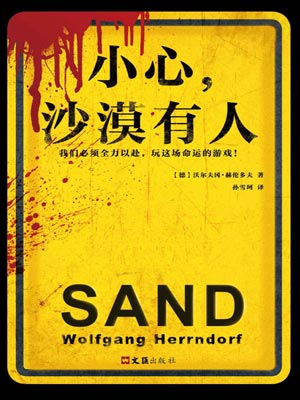斯蒂芬·金提示您:看后求收藏(350中文350zw.com),接着再看更方便。
“你为什么要打玛乔丽·瑟洛打针的地方?”布莱泽问。
“我愿意。”
“那好,”布莱泽说着向前走去。
布莱泽还没有靠近,格伦就在他的脸上揍了两拳,鲜血立刻从布莱泽的鼻子流了出来。格伦后退了几步,想保持自己的优势。有人喊了起来。
布莱泽使劲摇摇头,鲜血四处飞舞,滴落在他周围的雪地上。
格伦狞笑着。“孤儿院的孩子,”他说,“没爹没妈的东西,愚蠢透顶的东西。”他对着布莱泽凹进去一块的额头揍去,胳膊突然痛彻肺腑,脸上的笑容僵在了那里。不管那里有没有凹进去一块,布莱泽的额头都非常硬。
格伦一时忘记了后退,布莱泽挥出了自己的第一拳。他没有全身用力,只是将胳膊像活塞一样挥了出去。他的指关节与格伦的嘴碰到了一起,格伦发出一声惨叫,他的嘴唇在牙齿上磕破了,开始流血。周围的喊叫声更加疯狂。
格伦尝到了自己的鲜血,忘记了后退,忘记了嘲弄这个额头上凹进去一块的丑鬼。他向前迈了一步,左右开弓,向布莱泽挥拳。
布莱泽牢牢地站在那里,任凭格伦的拳头袭来。他隐隐约约听到远方传来了同学们的喊叫声和劝告声,让他想起了自己那天意识到兰迪会真的扑向他时狗圈里那些吠叫不已的牧羊犬。
格伦至少狠狠揍了布莱泽三拳,每一拳挥来时,布莱泽的头都会被打得左右晃动。他喘着粗气,将流淌着的鲜血吸进了肚子里。他听到自己的耳朵在嗡嗡作响。他再次出拳,感到拳头的冲击波一直传到他的肩膀上。格伦嘴巴上的鲜血几乎立刻布满了他的下巴和脸颊。格伦吐出了一颗牙齿。布莱泽再次出拳,击中了格伦的同一个地方。格伦发生一声惨叫,就像小孩手指夹在门缝里时发出的惨叫声。他不再左右躲闪,他的嘴已经稀巴烂。福斯特太太正向他们跑来。她的裙子在飞舞,她的双膝在快速交替向前,她在吹着小银哨。
布莱泽胳膊上打针的地方很痛,他的拳头在痛,他的头在痛,但他还是再次挥拳,用尽了全身力气,用他那只已经完全失去知觉的手。那天用在兰迪身上的正是这只手,而他今天挥出这只手时与那天在狗圈里一样使足了全身的力气。这一拳正好击中格伦的下巴,一声清晰的“咔嚓”声吓得所有的孩子不敢再吭声。格伦双腿一软,眼睛一翻,倒在了地上。
我杀了他,布莱泽想,哦,上帝,我杀了他,就像杀了兰迪一样。
但格伦动了一下,喉咙深处嘟哝了一声,像人们睡着后说梦话一样。福斯特太太尖叫着,让布莱泽回教室去。布莱泽向教室走去时,听到她在吩咐彼德·拉沃尔去办公室拿急救箱,而且要“赶紧跑着去”。
他离开了学校。他被勒令停学了。老师们用冰袋给他的鼻子止住了血,在他的耳朵上贴上创可贴,然后打发他步行六公里多回养狗场。他沿着公路走了一会儿后,突然想起了自己的午餐袋。鲍伊太太总是给他准备一块抹了花生酱后对折起来的面包,外加一个苹果。东西虽然不多,但回家的路很长,而正如约翰·切尔兹曼所说,有一点东西总比一无所有要强。
他回来时学校方面不让他进去,但玛乔丽·瑟洛替他把午餐拿了出来。她大概一直在哭,眼睛还是红红的,那副神情仿佛想说点什么却又不知道如何开口。布莱泽明白那是一种什么样的感觉,于是冲她笑了笑,让她知道他没事。她也冲他笑了笑。他的一只眼睛已经肿得只剩下了一条缝,因此他只能用另一只眼睛望着她。
他走到操场边时转过身去,想再看她一眼,可她已经走了。
“给我到棚子里待着!”鲍伊吼道。
“不。”
鲍伊吃惊得瞪大了眼睛。他微微摇了摇头,仿佛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你说什么?”
“你不应该打我。”
“那得由我来决定。你给我到棚子里待着。”
“不。”
鲍伊向他步步逼近。布莱泽后退了两步,肿着的双手握成了拳头。他停下脚步,鲍伊也突然止步了。他察看过兰迪的情形,兰迪的脖子断了,就像严寒中折断的雪松树枝一样。
“回屋去,你这狗娘养的蠢东西。”他说。
布莱泽进了屋。他坐在床沿上,可以听到鲍伊在冲着电话咆哮。布莱泽知道鲍伊在对谁吼叫。
他不在乎,真的不在乎。可是一想到玛乔丽·瑟洛,他却突然在乎起来。一想到玛乔丽,他就想哭,那种感觉与他偶尔看到一只鸟独自停在电话线上时想哭的感觉一样。但是他没有哭,反而看起了《雾都孤儿》。这本书的内容他早已牢记在心,就连书中那些他不认识的字也会念。外面传来了狗的吠叫声,它们饿了,该给它们喂食了。可是没有人来叫他给狗喂食,尽管如果叫他的话他会去的。
他继续看他的《雾都孤儿》,一直看到赫顿之家的客货两用车来接他。开车的是“牢头”,两只眼睛气得通红,嘴巴抿成了下巴和鼻子之间的一条缝。一月的落日投下长长的阴影,鲍伊夫妇站在那里,望着他们驱车远去。
回到赫顿之家后,布莱泽有一种非常糟糕的熟悉感,就像身上穿了一件湿衬衣一样。他得使劲咬着舌头才没有哭出来。三个月过去了,这里的一切都没有变。赫顿之家还是原来那堆永远不朽的红砖,同样的窗户投下同样的黄色灯光,落到外面的操场上,只是操场上现在覆盖着白雪。到了春天,这些积雪就会融化,但窗户上投下的黄色灯光会照旧。
“牢头”在他的办公室里又拿出了板子。布莱泽本可以将板子从他手中夺走,但他已经厌倦了打斗,而且他估计总会有人身材更加高大,也总会有更大的板子。
“牢头”的手臂锻炼结束后,布莱泽被打发去了福勒楼的公共寝室。门口站着约翰·切尔兹曼,一只眼睛青肿得只剩下一条缝。
“你好,布莱泽,”他说。
“你好,约翰。你的青春痘呢?”
“都破了。”他说,接着便哭诉道,“布莱泽,他们打烂了我的眼镜,我现在什么也看不了!”
布莱泽想了想。他很不愿意回来,可看到约翰在等他后又深受感动。“我们可以把眼镜修好。”他突然有了一个主意,“要不,下次下雪后,我们去城里帮人除雪,攒钱买副新眼镜。”
“你觉得我们可以做到吗?”
“当然可以,可你得帮我做家庭作业,好不好?”
“那当然,布莱泽。”
他们一起进了屋。
更多好书分享关注.公众号:sanqiuju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