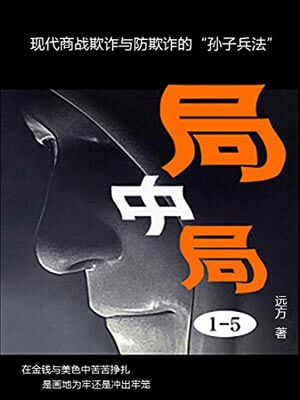斯蒂芬·金提示您:看后求收藏(350中文350zw.com),接着再看更方便。
“因为——”
头戴牛仔帽的两个男人领着两个身穿西部衬衫仔裤、头梳马尾、笑容满面的姑娘朝他们的包厢走了过来。靠近后,相同的困惑表情——严格说来,并不是恐惧——出现在了他们脸上,一行人继而转身朝吧台走去。他们能感觉到我们,大卫想。像把他们推走的冷风——这就是现在的我们。
“因为这是该做的。”
薇拉笑了,笑声有些疲倦:“你让我想起了过去在电视上卖燕麦粥的老头。”
“宝贝儿,他们一直认为自己在等一趟能把他们接走的火车!”
“说不定真有呢!”他几乎被她语气中突如其来的残酷吓了一跳,“说不定就是他们一直歌唱的那辆福音火车,开往荣耀之地,不搭载赌徒和午夜游魂……”
“我可不认为美国铁路公司有开往天堂的专列,”他本想逗她发笑,可她只是低头看着双手,脸上的表情几乎可以算是阴沉,他突然有某种不祥的预感。“你是不是还知道什么?我们应该告诉他们的事情?有,对不对?”
“我不明白为什么我们要去找麻烦,待在这儿不好吗?”那是气急败坏的语气吗?他认为是的。他不曾见过她这一面,想也没想过。“或许你有点缺乏远见,大卫,但至少你来了。为此,我爱你。”说完她又吻了他一下。
“我还遇上了一匹狼,”他说,“我拍拍手,把它吓跑了。我还考虑把名字改成驱狼者大卫呢。”
她瞠目结舌地看了他一会儿,大卫想:看来直到我们都死了,我才有本事让我爱的女人吃惊。片刻,她仰倒在包厢厚厚的椅座上,放声大笑。恰巧路过的女招待砰的把整托盘的啤酒都掉到了地上,生气地咒骂了起来。
“驱狼者大卫!”薇拉叫道,“我想在床上这么叫你!哦,哦,驱狼者,大块头!体毛男!”
女招待瞪着地上冒泡的一片狼藉,仍然像个登岸的水手般骂骂咧咧。与此同时,她一直同那个空空的包厢保持相当的距离。
大卫问:“你认为我们还能吗?我是说,还能做爱吗?”
薇拉擦擦笑出眼泪的眼角,说:“感知和期望,记得吗?合在一起,它们能移动大山。”她又拉起了他的手,“我仍然爱你,你仍然爱我。你爱我吗?”
“我是驱狼者吗?”他也问。他还能开玩笑,因为他的神经并不真的相信自己已经死了。他越过她,看向镜子,在里面看到了他们俩。然后,只剩下他一个人了,他的手中空无一物。接着,镜中的两个人都消失了。可仍然……他在呼吸,他能闻到啤酒、威士忌和香水的味道。
一个杂工不知从何处过来,帮助女招待清理地上的乱摊子。“我刚才就像猛地踏下台阶一样。”大卫听到她说。人在死后的世界听到的就是这样的东西吗?
“我想我会跟你一起回去,”她说,“但有这么个好地方,我是不会在那个无聊的车站和那一帮无聊的人待在一起的。”
“好。”他答应。
“谁是巴克·欧文斯?”
“我会告诉你的,”大卫说,“还有罗伊·克拉克。但首先,告诉我你还知道什么。”
“他们中的大多数我一点都不在乎,”她说,“可是亨利·兰德是个好人。还有他的妻子。”
“菲尔·帕尔默也不坏。”
她皱了皱鼻子说:“药罐菲尔。”
“你知道什么,薇拉?”
“你自己会看到的,如果你真的看的话。”
“如果你直接告诉我,不是更简单吗?”
显然,她并不这样想。她直起身体,直到大腿贴到桌子边缘,手向前指着:“看,乐队回来了!”
和薇拉手拉手走在公路上时,月亮已经高挂在天空中了。大卫不明白怎么会是这样——他们不过是听了乐队下半场的头两首歌而已——但月亮千真万确就在那里。这令他困扰,但还有更困扰的问题。
“薇拉,”他说,“现在是哪一年?”
她想了想。风吹动她的衣裙,像吹动任何一个活着的女子的衣裙一样。“我也记不清楚,”她终于回答,“是不是很怪?”
“想想我连上次吃饭或喝水都记不得了,也不是很奇怪。如果非要你猜的话,你会说什么?快,别思考。”
“一九……八八年?”
他点点头。他自己的话,会说一九八七年。“酒吧里有个女孩,穿着一件写有克罗哈特高中〇三届的T恤,而如果她的年龄都够进酒吧了——”
“那么〇三年最起码也是三年之前。”
“我就是这么想的。”他停了停,“可是,不可能是二〇〇六年,对不对,薇拉?我是说,二十一世纪?”
没等到她回答,他们就听到了脚掌踩在沥青地上发出的哒—哒—哒的声音,这次,不止一匹,公路上有四匹狼在跟着他们。站在其余几匹身前的最大的一匹,就是大卫去克罗哈特时看见的。不论在哪里,他都能认出那身杂乱蓬松的黑色皮毛。它的眼睛比上次更加明亮。半月映射在它的眼中,像没入水中的灯。
“它们能看见我们!”薇拉欣喜地叫道,“大卫,它们能看到我们!”她在斑驳的过路线上单膝跪下,伸出右手。她舌头一弹,发出咯的声音,说,“这边来,小伙子!到这边来!”
“薇拉!我可不认为这是个好主意。”
她不予理会,典型的薇拉做派。薇拉总是对事情有她的一套想法。是她想搭乘火车从芝加哥去旧金山的——因为,她说,她想知道在火车上做爱是什么感觉,特别在是一趟快速且略有摇晃的火车上。
“来呀,小伙子,到妈妈这里来!”
为首的大狼过来了,身后跟着它的配偶和它们的两个……该称它们为幼仔吗?它向着那只伸向它的纤细的手撅起尖嘴(还有一口森森白牙),月光充满了它的双眼,把它们变成了银色。就在它的尖嘴即将碰到她的皮肤时,狼突然发出一阵尖利的叫声,惊慌失措地往后退去,退得那么猛,一时间只用两条后腿站立着,一双前爪抓挠着空气,腹部的白毛也露了出来。其他狼四散开来。头狼一拧身,夹着尾巴跑进路右边的灌木里去了。另三匹也尾随而去。
薇拉直起身,看着大卫,眼中的忧伤让大卫无法承受。他垂下目光,看着自己的脚。“我本来好好地听着音乐,你把我拖到黑黢黢的外面,就是为了这个?”她问,“为了让我知道我现在是什么?就好像我本来不知道一样!”
“薇拉,对不起。”
“还不到你道歉的时候,但你会的。”她又拉起了他的手,“走吧,大卫。”
他冒险偷看她一眼。“你不生我的气啦?”
“有一点——但我现在只有你了,我不会放你走的。”
遇上狼没过多久,大卫看到前方的路边有一只百威啤酒罐。他几乎可以肯定就是他来时一直踢的那只,直到他一脚踢歪把它踢进了鼠尾草中。现在,它又出现了,在最初的位置……因为他根本不曾踢动过它。感知不是一切,薇拉曾说过,但感知和期望加在一起呢?加在一起,你的脑子会变得像好时的花生巧克力杯一样美妙。
他抬脚把啤酒罐踢到灌木丛中,走过去之后,他回过头,看见它仍然在原处待着,就在某个牛仔——或许是在去26酒吧的路上——把它从小卡车的车窗扔出去后的着地点。他记得在《嘿—嚯》中——一档由巴克·欧文斯和罗伊·克拉克共同主持的电视节目——他们曾把敞篷小货车称为牛仔的凯迪拉克。
“你在笑什么?”薇拉问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