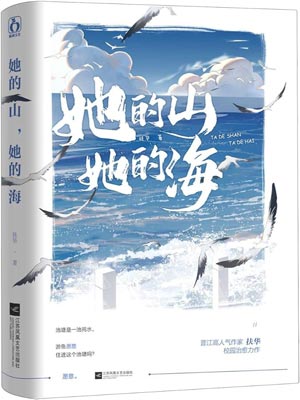埃勒里·奎因提示您:看后求收藏(350中文350zw.com),接着再看更方便。
亚德利摇摇头。“不是一个圆,我的孩子,而是一个水滴或者说梨形的小人像。安克本质上类似于一把钥匙,叫作克鲁克斯安萨它<a id="zhu19" href="#zs19"><sup>[19]</sup></a>,在埃及铭刻中屡见不鲜。它意指神,或是王权,能赋予拥有者以生命生产者的身份。”
“生命生产者?”什么东西在埃勒里眼中酝酿。“好家伙!”他叫道,“正是这样!终究是埃及十字架!某种东西告诉我,现在我们想法对路了!”
“请解释明白,年轻人。”
“你看不出吗?怎么啦,这明明白白!”埃勒里大声说,“安克——生命的象征。T字一横——双臂;一竖——身体;顶上的梨形玩意儿——头。而头被砍了!那意味着什么,我告诉你——克罗萨克有意把生命的象征改变成死亡的象征!”
教授凝视了他一会儿,接着爆发出一阵长长的嘲弄的笑声。“高明,我的孩子,无比高明,但离事实十万八千里。”
埃勒里的激动消退了。“哪儿错了?”
“如果说安克,或者说克鲁克斯安萨它,是人像的象征的话,你对克罗萨克先生砍去受害者头的富有灵感的解释可能言之有理。但它不是,奎因。它有着平凡得多的来源。”教授叹了口气,“你记得斯特赖克穿的拖鞋吗?那是仿造的典型的古埃及鞋……哦,我不想被人援引这个——毕竟我只是一个人类学家,而不是埃及学家——但安克通常被专家们认为代表一种鞋带,像斯特赖克用的那种,顶上那个活结是那个绕踝的带子的一部分。活结的垂直下方是带子的那一部分,它越过鞋面向下跟大脚趾和其他趾头之间的鞋底相连。短些的,平行的那些,从脚两侧向下通到鞋底。”
埃勒里显得垂头丧气。“但我仍然不明白,那个象征,如果它的来源是一只拖鞋的话,怎么可能代表生命的创造呢,即使是在比喻意义上。”
教授耸耸肩。“词或观念的来源,对现代人的心理来说,有时是不可理解的。整个演变过程从科学角度来看不是很清楚。但因为安克符号作为表示‘生活’的词干,被频繁使用在书写各种各样的词上,它最终成为生活或生命的象征。尽管它来源的材料是柔软的——自然,拖鞋通常由处理过的纸草制成——但最终埃及人以坚硬的形式使用这种符号——木制的护身符,等等。但肯定这象征本身从来没有指代人像。”
埃勒里擦拭了他的夹鼻眼镜,同时眯着眼若有所思地看着那阳光照耀的水面。“很好,”他绝望地说,“我们放弃安克理论……告诉我,教授,古代埃及人会将人钉死在十字架吗?”
教授笑了。“你拒绝投降,是吧?没有,据我所知。”
埃勒里果断地把眼镜戴到鼻梁上。“那么我们把埃及理论整个儿抛弃!至少我是这样。最近一个令人担心的征兆就是我会半路抛弃原先的思路;我的脑子必定在生锈。”
“我的孩子,如蒲柏<a id="zhu20" href="#zs20"><sup>[20]</sup></a>所言,”教授说,“一知半解害死人。”
“还有,”埃勒里反驳说,“faciunt nae intelligendo,ut nihil intelligant……<a id="zhu21" href="#zs21"><sup>[21]</sup></a>知识太多带来的是全然无知。自然,这不是故意针对某个人——”
“当然不是,”亚德利严肃地说,“泰伦斯<a id="zhu22" href="#zs22"><sup>[22]</sup></a>也不是这个意思,对吧?无论如何,我觉得你在拼命努力用埃及学解释这些犯罪行为。你总是倾向于浪漫化,我记得甚至上学时也是这样。一次,我们在讨论阿特拉斯<a id="zhu23" href="#zs23"><sup>[23]</sup></a>传说的来源,因为那是转述自柏拉图、希罗多德<a id="zhu24" href="#zs24"><sup>[24]</sup></a>和——”
“请允许我打断您,”埃勒里有点不耐烦地说,“我在努力从一大片污泥中找寻出路,而你则在用无关的古典知识搅浑它。对不起……如果克罗萨克砍去受害者的头,在犯罪现场附近散布T字符号,那肯定代表的不是安克十字架,而只能是T十字架。因为在法老时代的埃及,T十字架存在的意义微乎其微,大概克罗萨克心里没有这种想法,尽管他和一个着迷于埃及宗教事物的疯子有联系……确定?是的。托马斯·布雷德被吊在一个图腾杆,对不起,图腾柱上。这是另一种宗教象征。我们再来进一步确认——如果克罗萨克想意指安克十字架,他会留下头,而不是砍掉头……所以我们对建构在埃及学上的推测产生了怀疑。我们没有证明有关美洲图腾推测的证据,除了那单一的偶然事实,即布雷德被钉成十字架的地方——它被选择显然是因为它的T字形意义,而非任何宗教意义——我们根本无法坚持关于十字架的推测……T十字架在基督教信仰中……据我所知,斩首从未用在处死殉教者上……Ergo,我们放弃所有宗教方向的揣度——”
“你的信条,”教授笑嘻嘻地说,“看起来像拉伯雷<a id="zhu25" href="#zs25"><sup>[25]</sup></a>的宗教——一个大大的‘也许’。”
“——并重新回到一开始就在我眼皮子底下的东西。”埃勒里带着懊恼的苦笑,结束了他的发言。
“是什么呀?”
“就是T很可能就只是T,而不是别的什么该死的东西这一事实。T在它字母上的意义。T,T——”突然他住了口,教授好奇地打量他。埃勒里盯着水池,他的眼睛像是从未见过像蓝色的水和金色阳光那么单纯的东西。
“怎么啦?”亚德利问。
“那可能吗?”埃勒里咕哝着,“不……太巧合了。而且无法证实。以前我曾一度想到——”他拖长了声音,甚至没有听到亚德利的问题。教授叹了口气,重新拿起他的烟斗。好长时间两个男人什么也没说。
两个几乎全裸的人就那么呆坐在安静的露台上,突然一个年老的女黑人啪嗒啪嗒跑进来,发光的黑脸上带着愤慨的表情。
“亚德利先生,”她用轻柔的抱怨声说,“有人想要闯进来。”
“是吗?”教授吃了一惊,丢开了遐想,“是谁?”
“那个警官。他像是喝醉了。”
“好吧,让他进来。”
沃恩不一会儿便闯了进来,挥着一张不纸片,激动得满脸通红。“奎因!”他大声说,“重大消息!”
埃勒里两眼茫然地挪挪身子。“是吗?哦,你好,警官。你这是得到什么消息了?”
“读读这个。”警官把那张纸扔到大理石地面上,在池子边坐下,喘着粗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