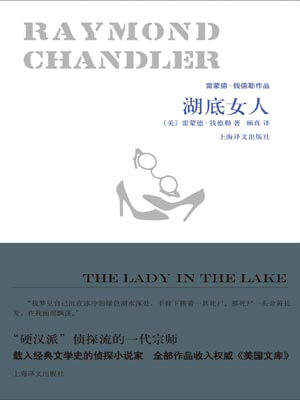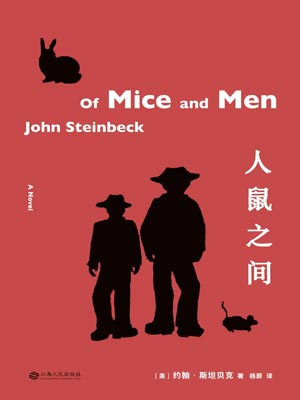第三章 (第3/5页)
P.D.詹姆斯提示您:看后求收藏(350中文350zw.com),接着再看更方便。
说话的是索菲。她的弟弟接过话说:“我们都喜欢她。问题是,我们怎么摆脱她?”
随后的几分钟是一阵低声交谈,她听不清他们在说什么,只听见伊莎贝尔的插话。
“这不是,我觉得,一份适合女人的工作。”
一阵椅子刮擦地板的声音,接着是脚步声。科迪莉亚赶紧悄悄回到洗手间关上水龙头。她曾经问伯尼要不要接一桩离婚案,到现在她还记得他洋洋得意的告诫。
“你干不了我们的工作,伙伴,你也成不了男人。”
她站在那里看着那扇半开着的门。雨果和伊莎贝尔离开了。等到前门关上,汽车开走之后,她才走到楼下的客厅。索菲和戴维正从一只大旅行包里往外拿蔬菜和水果。索菲笑着说:“伊莎贝尔今天晚上要办一个聚会。她在离这里很近的潘顿大街有一处房子。马克的导师爱德华·霍斯福尔可能会去,我们觉得你或许需要向他了解马克的情况。聚会晚上八点开始,但是你可以到这里来找我们。现在我们要先收拾野餐用的东西,我们打算花一个钟头在河上划船。你愿意的话就一起来吧。这可是游览剑桥的最好方式。”
事后,那次河上野餐在科迪莉亚的记忆中成为了一系列短暂而清晰的画面,是视觉和感官的融合,时间仿佛被暂时冻结了,阳光下的美景牢牢印在了她的头脑中。阳光照在河面上泛起耀眼的金光,也给戴维胸前和手臂上的毛发镀上了金色,他那双强有力的上臂像蛋壳般撒上了斑点;索菲在用篙撑船,还不时抬起手臂擦去从眉毛上淌下的汗水;篙从神秘的河底带出的绿色水草,它们在水面下方扭转翻腾;一只活泼的鸭子把白色的尾巴翘起,一头扎进碧绿的水里,激起一片涟漪。当他们的船荡漾着从希福尔大街的桥下经过时,索菲的一位朋友游到他们的船边,就像一只身上滑溜溜的大鼻子水獭,黑色的头发如同两块刀片贴在脸颊上。他把双手搭在船沿上,向正在抗议的索菲张开嘴,要求投喂几片三明治。平底船和独木舟在桥下的激流中挤撞碰擦着,空气中充满欢声笑语。许多人半身赤裸地躺在绿色的河岸上,仰面晒太阳。
戴维一直把船划到河的上游,科迪莉亚和索菲分别躺在船两头的垫子上。两人相距甚远,不可能进行私下交谈,科迪莉亚猜测这是索菲精心安排的。时不时的,索菲还会跟她大声介绍几句,好像是为了强调,这次出来玩仅限于参观游览。
“那块像婚礼蛋糕一样突出的建筑是圣约翰学院的新庭院,我们刚刚从下面经过的那座桥是克莱尔桥,我觉得它是最美的景点之一。这座桥是托马斯·格伦巴尔德在一六三九年建造的,据说他的这项设计只得到三个先令的报酬。你肯定知道这个景点,从这里看王后学院再好不过了。”
“是不是你和你弟弟一起杀了你的情人?”科迪莉亚很想打断这场东拉西扯的观光讨论,粗暴地问出这句话。但她还是没有这个勇气。
此刻他们正泛舟在洒满阳光的剑河上,提出这样的问题似乎不甚得体,近乎荒唐。她快要一点点地接受自己的失败:也许是她太过神经质,自己所有的怀疑只归因于对刺激和名声的过分追求;或许她只是想证明罗纳德勋爵的雇佣费没有白花,她认为马克·卡伦德是被人杀害的,因为她愿意相信。他一个人生活,自立,不依赖父亲,有一个孤独的童年,这使她产生了惺惺相惜的感情。她甚至开始觉得自己是在为他报仇——这是一种非常危险的假设。从花园别墅饭店前经过时,索菲接过撑篙,戴维在微微摇晃的平底船上小心翼翼走过来,然后在她身边躺下。她知道自己不可能再提到马克的名字。只是出于一种模糊的、不冒犯他人的好奇心,她不由自主地问道:“罗纳德·卡伦德勋爵是个出色的科学家吗?”
戴维拿起一把短桨,在波光粼粼的水面上漫不经心地划动。“我那些亲爱的同事们会说,他研究的科学很值得尊重。实际上岂止是值得尊重,目前这个实验室正在研究扩大生物监视器的应用范围,对海洋及内河入海口污染状况进行评估。也就是说,对可以作为监测污染指标的植物和动物进行定期观测。去年,他们还对塑料的降解做了一些非常有用的初步研究,罗纳德·卡伦德本人并不非常热衷,但你指望一个五十多岁的人还能有多少创新理论呢?不过他确实很善于发现人才,也知道如何管理团队。你能想象有什么方法,能让团队中的所有人都全身心投入,感情如兄弟一般吗?我可想象不出来。甚至在发表论文的时候,他们都不以个人的名义,而是以卡伦德研究实验室的名义。换我绝做不到。我发表论文完全是为了戴维·福布斯·史蒂文斯的光荣,附带的,也为了感谢索菲。蒂林姐弟都喜欢成功。”
“这就是他当时给了你一个工作机会,而你却不愿意留下来的原因吗?”
“还有其他原因。他支付报酬很大方,但要求也太多。我不想被钱买下来,而且我尤其反感每天晚上穿正装用餐,感觉就像动物园里表演的猴子。我是分子生物学家,不是在寻找圣杯。爹妈把我养大,让我成了循道宗教徒,这在过去的十二年中都毫无问题,我觉得没有理由为了罗纳德·卡伦德的伟大科学原则,就把好好的信仰抛弃了。我不信任那些将科学奉若神明的科学家。加福斯庄园里那一小撮人如果没有一天三次朝卡文迪什实验室<a id="jz6" href="#jz6"><sup>[6]</sup></a>方向跪拜,那才叫奇怪。”
“伦恩这个人怎么样?他在那里能适应吗?”
“哦,那个该死的家伙是个怪物!他十五岁那年,罗纳德·卡伦德在一家孤儿院里发现了他——别问我是怎么找到的——后来把他培养成一个实验室助理。你不可能找到比他更称职的了。那里的所有仪器和器皿,没有克里斯·伦恩弄不懂或者管不好的。他还自己研究出了一两样,卡伦德为它们申请了专利。如果说这个实验室里缺了谁不行的话,那大概就是伦恩了。所以罗纳德·卡伦德更喜欢的是他而不是自己的儿子。你也许能猜到,伦恩把罗纳德·卡伦德看成了万能的神,这使他们俩都很满意。这简直不可思议,伦恩那种原本要街头斗殴和欺负老太太时体现的暴力,现在被用来为科学服务。你不得不佩服卡伦德,他知道如何挑选自己的奴才。”
“利明小姐也是他的奴才吗?”
“这个嘛,我也不知道伊丽莎白·利明是什么角色。她负责安排处理各种事务,和伦恩一样,大概也是个不可或缺的人物。伦恩和她之间似乎有一种又爱又恨的关系,也可能只是彼此仇恨。我对这种心理上的微妙区别可不在行。”
“但是罗纳德勋爵如何支付他所有的研究?”
“这的确不是小数目,是吧?有谣传说大部分钱是他妻子的,还说他和伊丽莎白·利明用这些钱做了一笔相当明智的投资。他们当然有必要这样。后来他从承包合约中得到一笔钱。即便如此,他的开销也不小。我在那里的时候,听说沃尔温顿信托基金对他的研究有兴趣。如果卡伦德能有什么大的研究成果——我想一般的研究也有辱他们的名声——他的大部分问题就能迎刃而解。马克的死肯定对他打击很大。再过四年时间,马克就会得到一笔相当可观的财富,他对索菲说过,他打算把其中大部分都交给他老爸。”
“他为什么要这样做呢?”
“天知道。也许是良心作怪。不管怎么说,他显然认为这件事应当让索菲知道。”
他有什么良心钱要付呢?科迪莉亚疲惫地想。因为他不太爱他的父亲?因为他拒绝了父亲的热情?因为他是一个没有达到父亲期望的儿子?现在马克的钱会怎么样呢?马克一死,这笔钱将会归谁?她心想应当去看一看他祖父的遗嘱,或许会有什么发现。但是这就意味着要到伦敦跑一趟。这样做真的值吗?
她把脖子向后仰,面对着太阳,一只手伸进河里。船篙溅起的水洒落在她的眼睛上。她睁开眼,看见船在贴近河岸的地方漂流,头顶上方的树木遮住了阳光。她的前方垂挂着一截枝干,齐根断裂,有人的躯干那么粗,只有树皮还连着。平底船从它下面经过的时候,它还轻轻地转了一下。她意识到戴维在说话,他肯定已经说了很长时间。她感到奇怪的是,她竟然记不得他说了些什么。
“如果你想自杀,那是不需要理由的,不想自杀倒是需要理由。他就是自杀,科迪莉亚。我不会再纠缠于这个问题了。”
科迪莉亚心想自己刚才肯定睡着了一会儿,因为他似乎正在回答一个问题,可她记不清自己提过问。然而这时,她的耳边响起了一些更响亮、更急切的声音。其中有罗纳德·卡伦德勋爵:“我的儿子死了。我的儿子。如果这其中有我的责任,那么我要知道。如果是别人的责任,我也想知道。”还有马斯克尔警长的声音:“你如何用这个东西来上吊呢,格雷小姐?”那根皮带她用手摸过,光滑、弯曲,像一个有生命的东西在她的指间滑过。
她突然坐起来,双手紧紧抓着膝盖,由于动作太猛,平底船剧烈摇晃起来,索菲不得不抓住头顶上方的一根树枝来保持平衡。有意思的是,她那张黝黑的脸似乎变得很短,而且被烙上了树叶的阴影。她似乎正从一个很高的地方俯视着科迪莉亚。就在她们目光相遇的时候,科迪莉亚意识到,自己离放弃这个案子的想法已近在咫尺。这里的美景、阳光、悠闲、伙伴的承诺,甚至友谊,已经使她忘记了今日此行的目的。意识到这一点之后,她颇为吃惊。戴维说罗纳德勋爵善于用人,而他又选中了她。这是她接手的第一桩案件,任何事或者任何人都无法阻止她解决这个案子。
她郑重其事地说:“谢谢你们今天的陪伴,但我不想错过晚上的聚会。我应当找马克的老师谈一谈,而且到时候其他人也许还能告诉我一些情况。现在我们是不是可以考虑返回了?”
索菲把目光投向戴维。他耸了耸肩,动作之小几乎难以觉察。索菲没说话,用篙使劲往岸上一撑。平底船开始缓慢地返回。
伊莎贝尔的派对定在八点开始,可是索菲、戴维和科迪莉亚快九点时才到达。从诺维奇大街步行到这里只要五分钟,科迪莉亚一直也没有弄清它的确切地址。她很喜欢这所房子,伊莎贝尔的父亲花了不知多少钱在房租上。这是一幢两层楼的白色长形别墅,弧形的窗户很高,配有绿色百叶窗。房子远离附近的街道,半地下室里有一段台阶通向前门,另一段相仿的楼梯从客厅通向长形的花园。
客厅里已经聚集了许多人。科迪莉亚看了看来宾,庆幸自己买了件土耳其长袍。看来大多数人都穿上了引人注目的衣服,尽管她认为没这个必要。人们这样做,无非是为了展示自己的与众不同——最好能够艳惊四座,甚至哪怕看上去怪诞不经,也好过毫无特色。
客厅里的陈设十分讲究,不乏浮华,带有伊莎贝尔那凌乱、不切实际并一反传统的女性特征。一盏装饰华丽的水晶吊灯如旭日般挂在天花板中央,却在这个房间里显得太过巨大笨重,豪华铺张的丝绸坐垫和窗帘使这里更像是妓女和情妇的闺房。科迪莉亚不相信这些东西是房东的风格。那些画肯定也是伊莎贝尔自己的东西,因为没有哪个房东会把这么贵重的画作留在墙上。壁炉上方挂着一幅画,上面是一个搂着小狗的年轻女子。科迪莉亚目不转睛地看着它,内心感到一阵激动和喜悦。毫无疑问,她不可能看错那女孩裙子的独特蓝色,还有那年轻丰腴的面颊和手臂上令人赞叹的色彩,它们在吸收光线的同时也反射出光线——可爱、富有弹性的肌肤。她情不自禁地发出感叹:“这是雷诺阿的画!”人们纷纷回过头来看她。
在她身边不远处的雨果笑着说:“不错,不过别这么大惊小怪嘛,科迪莉亚。不过是幅雷诺阿的小作品。伊莎贝尔向她爸爸要一幅油画来装饰客厅,他总不能用《干草车》的印刷品,或者梵高那张破椅子的廉价复制品打发她吧。”
“伊莎贝尔会知道其中的区别吗?”
“哦,那当然。伊莎贝尔很识货。”
科迪莉亚想知道,他语气中的尖酸是在针对伊莎贝尔,还是针对他自己?在房间另一头,他们看见伊莎贝尔正冲他们微笑,雨果如同坠入梦幻般径直朝她走去,抓住了她的手。科迪莉亚冷眼旁观,只见伊莎贝尔的头发盘成希腊式的高发髻,身穿一条长及脚踝的奶油色丝绒连衣裙。裙子的方领开得很低,袖口缝着繁复的褶边。科迪莉亚思忖:这俨然是一件模特儿的服装,在这种非正式聚会中,本应显得很不协调,可相反,它使得其他女人的衣服看上去都像是临时凑合,就连科迪莉亚自己这身衣服也成了一块俗气的破布,不似买来时那么淡雅精致。
科迪莉亚决定晚上找个时间和伊莎贝尔单独谈谈,但发现这恐怕不容易。雨果在她身边寸步不离,一只手始终占据着她的腰际,把持着她在朋友之间应酬。他似乎在一杯接着一杯地喝酒,而伊莎贝尔的酒杯也始终没有空着。也许随着夜晚过去,他们会放松警惕,到时就有可能找机会把他俩分开。眼下,科迪莉亚决定在房子里四处看看,尤其要看看洗手间在哪里,以备不时之需。在这样的聚会上,这种事需要客人自己留心。
科迪莉亚走上二楼,来到楼道尽头的一扇门前。她轻轻把门推开,顿时一股浓烈的威士忌酒气扑面而来。她本能地悄然进入,并顺手把门带上,以免酒气弥漫到整个房子里。这不是个空房间,里面一片混乱。床上还躺着一个女人,身上搭着一条床罩;这个女子身着粉红丝绸睡袍,金色头发披散在枕头上。科迪莉亚走到床边俯视着她,她已经喝得酩酊大醉了。她的嘴巴半张着,一阵阵威士忌的酒气像无形的烟圈般不断散发出来。她的下唇和下巴肌肉绷得很紧,起了一道道皱纹,使她的脸看起来冷峻而严厉,好像对自己的状况感到强烈的不满。她薄薄的嘴唇上抹着厚厚的唇膏,浓浓的紫色渗进嘴唇四周的皱纹中,使她的身体看起来就像遭遇着酷寒。她的两只手一动不动地放在床单上,布满皱纹的手指被尼古丁熏得焦黄,还有一圈一圈的痕迹。两根鹰爪般的指甲上有裂痕,其他指甲上的砖红色甲油有的开了裂,有的已经脱落。
一张笨重的梳妆台挡在窗前。她把视线从这双皱巴巴的手上移开,一一扫过桌上几瓶开了盖的面霜、洒落的粉底,还有一杯喝剩下的看似咖啡的东西。科迪莉亚挤到桌子后面,把窗户推开,深深地吸了一口清新的空气。在下面花园的草地上、树荫之下,有几个苍白的影子在静静地移动,就像死去多年的酒鬼的幽灵。她把窗户开着,走回床边。现在她什么也做不了,不过还是把那双发凉的手塞到被罩下面,从门背后的钩子上取下一件比较暖和的睡袍,把它盖在那个女人身上,然后把四周掖好。至少这样就不怕吹风着凉。
做完这些之后,科迪莉亚悄悄返回楼道,正好看见伊莎贝尔从隔壁的房间里出来。她迅速伸手连拖带拽地把她拉进卧室。伊莎贝尔轻轻地喊了一声,科迪莉亚把她紧紧地按在门上,压低嗓门急切地说:“把你知道的有关马克·卡伦德的事情告诉我。”
那双紫罗兰色的眼睛从门转向了窗户,仿佛急欲夺路逃跑。“他做那件事的时候我不在那儿。”
“什么时候?谁做了什么事?”
伊莎贝尔朝着床的方向退去,似乎那个一动不动、发出呻吟般鼾声的人会向她提供支持。那个女人突然翻了个身趴在床上,像一头痛苦不堪的野兽发出长长的哼唧声。两个女人都惊讶地看了她一眼。科迪莉亚又问了一遍:“什么时候?谁做了什么事?”
“马克自杀的时候,我并不在场。”
躺在床上的那个女人轻轻地叹了一口气。科迪莉亚压低了嗓门:“可是在那不久之前你还去过,是不是?你到那个大宅去打听他的消息。马克兰德小姐看见你了。事后你坐在花园里,一直等到他把活干完。”
也许是科迪莉亚的想象?伊莎贝尔感到这个问题无关要害之后,似乎突然放松了许多,长长地舒了一口气。
“我是去找马克的。他们在学院宿舍把他的地址告诉了我,我就去看他。”
“为什么?”
这一苛刻的问题似乎令她茫然不解。她简单地回答说:“我想和他在一起。他是我的朋友。”
“也是你的情人吗?”科迪莉亚问道。这种单刀直入的方式总好过问他们是不是睡在一起或者同床共枕——而且伊莎贝尔也许根本就听不懂那些愚蠢的委婉用语。此刻,从她那双漂亮、受惊的眼睛中,很难看出她真正理解了多少。
“不,马克从来不是我的情人。他在花园里干活,我只好在农舍那儿等他。他在太阳底下给我放了一把椅子和一本书,我一直等到他把活干完。”
“什么书?”
“我记不得了,很没意思的书。在马克回来之前,我一直觉得很无聊。接着我们就用很好玩的杯子一起喝茶,就是带蓝杠的大杯子。喝完茶之后我们一起散步,然后一起吃晚饭。马克还做了色拉。”
“后来呢?”
“我就开车回家了。”
此刻她已经完全平静下来。科迪莉亚听见楼梯上传来上上下下的脚步声和一阵阵说话声,但她还是进一步追问:“在那之前呢?那次喝茶之前,你什么时候见过他?”
“是在马克离开学校前的几天。我们一起开我的车去海边野餐。不过我们先在城里停了一下——圣埃德蒙兹镇,对吧?马克去找了一个医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