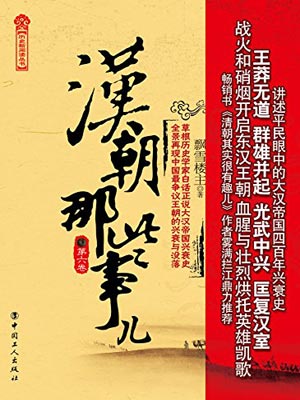雷蒙德·钱德勒提示您:看后求收藏(350中文350zw.com),接着再看更方便。
我在那个叫弗洛里安的女人面前抬起照片,举到她够不着的地方。她扑过来抢,但没摸到。
“干吗把它藏起来?”我问。
她喘着粗气,一声不吭。我把照片塞回信封,装到衣服口袋里。
“干吗藏起来?”我又问了一遍,“这张照片和另外那些有什么不同?她现在人在哪里?”
“她死了。”那女人说,“她是个好孩子,但已经死了。你这个条子,快滚吧。”
女人黄褐色的眉毛绞在一起,上下耸动。她的手一松,酒瓶滑落到地毯上,酒水汩汩流出。我弯腰去捡酒瓶,她伸出脚想踢我的脸,于是我撤开几步。
“你还是没说为什么要把她的照片藏起来。”我对她说,“她什么时候死的?怎么死的?”
“我只是个又病又老的可怜女人。”她咕哝道,“别来招惹我,你这个狗娘养的!”
我站在原地看着她,什么话都没说,什么要说的话都没想。过了一会儿,我走到她旁边,捡起地上几乎已经流空的酒瓶,放到她身边的桌子上。
她一直低头盯着地毯。收音机在角落里欢快低吟。屋外一辆汽车经过。一只苍蝇在窗户后面嗡嗡作响。过了好长一段时间,她开始嚅动半片嘴皮,对着地板说话,吐出一堆毫无意义的零碎语句。她大笑起来,仰面朝天,呆呆流出一摊口水。她又伸出右手,拿起酒瓶,咯咯磕着牙齿喝光了剩下的酒。她举起空瓶子摇摇,然后朝我扔了过来。酒瓶飞落到房间一角,顺地毯滚动,最后砰一声撞到踢脚板上。
她再次阴险地看了我一眼,之后就闭上眼睛,打起了鼾。
她可能在演戏,但我不在乎。突然间,我感觉受够了这一幕,简直受够了,实在受够了。
我在长沙发上捡起帽子,走向门口,打开纱门,来到屋外。收音机还在角落里嗡嗡低吟,那女人还躺在椅子里,呼呼打着轻鼾。关上门之前,我回头看了她一眼,之后我关上门又悄悄打开,再次看了她一眼。
她的眼睛仍然闭着,只是眼皮下有什么东西在闪动。我走下台阶,沿开裂的走道回到主路。
隔壁家的窗帘掀起了一角。一张狭窄、专注的脸贴在窗户上,凝视着这边——是个白发尖鼻的老女人。
爱管闲事的老太太又在打探邻居了。每条街上都至少有一个像她这样的人。我朝她挥挥手。窗帘落了下来。
我回到停车的地方,钻进车,开回七十七街分局,爬上楼梯,来到纳尔蒂那间位于二楼的臭烘烘的狭小办公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