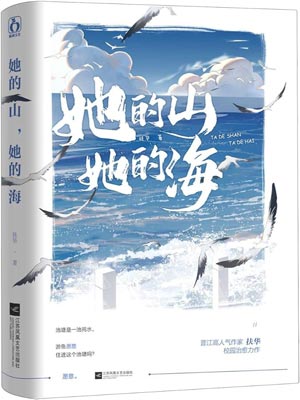P. D. 詹姆斯提示您:看后求收藏(350中文350zw.com),接着再看更方便。
“我想,我得见见博勒姆小姐的律师,”达格利什说,“把你所知道的有关她的事都跟我说说,那是非常有用的。我恐怕要问到一些个人方面的问题。通常,这些问题和犯罪案件无关,不过我必须尽可能对相关人员有所了解。你的堂姐除工资外还有其他收入吗?”
“哦,有。堂姐她比较有钱。希德尼伯父给她母亲留下大约25,000英镑的遗产,这笔钱后来全部转到了伊妮德名下。我不知道具体剩下多少,但我认为不算工资,她每年大约会有1000英镑的进账。她继承了伯母在巴兰坦大厦里的一套公寓。而且她……她对我们一直都很好。”
“怎么个好法,博勒姆小姐?她会给你些钱吗?”
“哦,没有!堂姐她不愿意这样做。她给我们的都是礼品。圣诞节的时候给30英镑,7月给我们50英镑过暑假。妈妈得了扩散性动脉硬化症,我们不可能去住普通旅馆。”
“现在博勒姆小姐的钱怎么处理?”
她抬起灰色的大眼睛看着他,丝毫没有觉得尴尬。她的回答很简单:“转到妈妈和我的名下。没有其他人可以给,对吧?伊妮德一直说,如果她死在前头,那些钱就转给我们。当然,她先我们而去曾经看来是不大可能的,至少妈妈在世的时候是不可能的。”
达格利什思忖,按常规,博勒姆太太确实不可能从那25,000英镑或者剩下的钱当中获得什么好处。任何检察机关都很看重这个,因为这显然是作案动机,可以理解,也符合常规。每个陪审团成员都理解金钱的诱惑。玛丽安护士如此坦然地向他提供这个信息,难道真的没有意识到它的重要性吗?清白的人会这么天真?内疚的人会这么自信吗?达格利什突然发问:“你堂姐人缘好吗,博勒姆小姐?”
“她朋友不多。我想她不会认为自己人缘好,也不愿意这样。她参加自己的教堂活动和女童子军活动。其实她是一个非常文静的人。”
“你听说过她有什么仇家吗?”
“哦,没有!一个也没有。堂姐很受人尊敬的。”
她这些正规、古板的词语几乎难以入耳。
达格利什说:“那这起谋杀看起来好像既没有动机,也没有预谋。一般,这表明是病人干的。但这看来几乎不可能,而且你们都认定这是不太可能的。”
“哦,不!不可能是病人干的!我敢肯定我们的病人没有人会这么干。他们都不是暴力型的。”
“就连蒂皮特先生也不会?”
“不可能是蒂皮特,他住院了。”
“他们跟我说了。这儿有多少人知道蒂皮特先生这周五不来诊所?”
“我不知道。内格尔知道,因为接电话的是他,然后由他告诉伊妮德堂姐和安布罗斯护士长,后来安布罗斯又告诉了我。你看,星期五晚上我要看护麦角酸病人,我一直很关照蒂皮特。当然,我几乎一刻也不能离开自己的病人,但我偶尔也会出去看看蒂皮特的情况。今天晚上却没有必要。可怜的蒂皮特的确很喜欢艺术疗法!鲍姆加滕太太病倒后有六个月没来了,不过我们没办法劝蒂皮特好好养病,不要来。他连一只苍蝇也不会伤害,暗示蒂皮特可能跟这个案子有关简直是没安好心,没安好心!”
她说着说着激动起来。达格利什语气温和地说:“可是没有人说过这样的话。如果蒂皮特住医院了——我对此毫不怀疑——他当然就不可能在这里了。”
“可是有人把他的雕像放在尸体上了,不是吗?如果蒂皮特在这儿,你们会立马怀疑他,他则会显得心烦意乱。做这种事的人很邪恶,真的很邪恶!”
玛丽安护士的声音哽咽起来,眼泪都快掉下来了。达格利什注意到,她把手夹在大腿之间,细长的手指在不安地扭动。他和颜悦色地说:“我想,我们没有必要为蒂皮特担心。现在,我要你仔细想想,然后把你所知道的诊所里发生的情况都告诉我,从你今天晚上来值班说起。不要说其他人,我只想知道你做了些什么。”
玛丽安护士对自己所做的事情记得很清楚,稍事犹豫之后,她进行了合乎逻辑的详细叙述。她星期五晚上值班的时候要“特别”给接受治疗的病人使用麦角酸。她解释说,这种治疗方法可以舒缓病人的深层压抑,使他们回忆起被压抑在潜意识中的事,并把它们说出来,因为这是他们的病根。她在谈到这种治疗的时候,丝毫没有紧张不安,忘记了她是在向一个外行进行解释。但是达格利什没有打断她。
“这种药很神奇,巴古雷医生用得很多。它的全名叫麦角酸二乙酰胺。我想它是德国人在1942年发现的。我们把它用于口服,一般的用量是0.25毫克。每支药含1毫克药物和15到30毫升的蒸馏水。我们要求病人不吃早饭服用。服药后经过大约半小时,就会开始出现药物反应,在用药一到一个半小时后,就会出现更加令人不安的个人体验。这时候巴古雷医生就会过来,和病人待在一起。药物作用可以长达四小时,病人会出现心情亢奋、烦躁不安、脱离现实的状况。当然,我们从来不让病人独处,我们使用地下室的房间,因为那里比较隐蔽和安静,他们发出的噪声不会影响到其他病人。我们通常都是在星期五下午和晚上给病人使用麦角酸二乙酰胺,而且我总是‘专门’照看这些病人。”
“我想,如果星期五地下室里传出声音,比如说喊叫声,大多数工作人员都会认为那是接受麦角酸二乙酰胺治疗的病人,对不对?”
玛丽安护士表现出怀疑的神情。
“我想有可能吧。毫无疑问,这些病人有时候会大吵大闹。今天我的病人就比平常更加烦躁不安,这也是我密切关注她的原因。一般情况下,病人的反应高峰期一过,我就会到治疗室里面存放衣物的小屋里待会儿,把洗干净的衣物叠好。当然,我会把两个房间之间的门开着,这样我就可以时不时地看病人一眼。”
达格利什问她当晚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
“呃。下午3点30分治疗开始。4点刚过不久,巴古雷医生来查房,看有没有什么问题。我和病人一起待到了4点30分,这时候肖特豪斯太太来告诉我,说下午茶好了。安布罗斯护士长下来后,我就到上面的护士值班室去喝了茶。我4点45分下来,5点给巴古雷医生打了个电话。他来和病人待了大约四十五分钟,然后就回夜间门诊治疗室去了,剩下我和病人在一起。今晚,她焦躁不安,我决定从小房间里出来。大约5点50分,彼得·内格尔来敲门,说要收待洗的衣物。我告诉他还没有整理出来。他觉得有点奇怪,但没说什么。此后不久,我觉得听见了一声尖叫。开始我没有在意,因为那声音好像不在近处,我还以为是在广场上玩耍的孩子们的声音。接着,我觉得应该看一看,于是就走到门口。我看见巴古雷医生和斯坦纳医生领着安布罗斯护士长和英格拉姆医生一起去了地下室。安布罗斯护士长告诉我没什么事,让我回到病人身边去,我照办了。”
“巴古雷5点45分离开之后,你有没有离开过治疗室?”
“哦,没有!没有必要啊。如果我要去厕所或者什么的,”说到这里,玛丽安护士的脸有点发红,“我会打电话让安布罗斯护士长过来临时替我一下。”
“晚上你有没有从治疗室给外面打过什么电话?”
“只有5点的时候给夜间门诊室打过一个电话,是找巴古雷医生的。”
“你肯定没有给博勒姆小姐打过电话?”
“给伊妮德堂姐?哦,没有!我没有任何理由要给她打电话。她……也就是说,我们在诊所不经常见面。安布罗斯护士长负责管我,你知道,伊妮德堂姐是不管护理人员的。”
“但是,在诊所外面你经常看见她?”
“哦,也不是!我不是这个意思。我到她的公寓去过一两次,去拿圣诞节和暑期的支票,不过对我来说,离开妈妈不容易。此外,伊妮德堂姐有她自己的生活。再说,她的岁数比我大很多。其实我对她不是很了解。”
她的声音有点哽咽,达格利什看见她在哭。她抽泣着把手伸到围裙下面去摸护士服上的口袋。
“太糟糕了!可怜的伊妮德!那个雕像被放在她的遗体上,好像是在取笑她,好像她是在照顾一个婴儿!”
达格利什不记得博勒姆小姐见过那具尸体,于是就问了她。
“哦,我没有!埃瑟里奇医生和安布罗斯护士长不让我去见她,但是他们把所发生的事情都跟我们说了。”
博勒姆小姐看上去的确像在护理一个婴儿,但让达格利什感到奇怪的是,一个没有看见过尸体的人竟然会这么说。医务主任肯定对现场进行了形象的描述。
突然,玛丽安护士摸到了手绢,随即把它从口袋里拽了出来。一副薄薄的手术手套掉了出来。达格利什把掉在他脚前的手套拾起来问道:“我没有想到你在这里还要用手术手套。”
玛丽安护士好像并没有因为他的兴趣而感到吃惊。她以惊人的毅力控制住抽泣,而后回答说:“我们用得不多,但是要保留几副。整个集团现在都使用一次性手套,可是这种老式的还有几副。这就是一副老式的。我们用来做一些特殊的清洁工作。”
“谢谢你,”达格利什说,“如果可以的话,这副手套由我来保存。目前我想我没有什么问题需要再麻烦你了。”
玛丽安护士嘟囔着,可能是在说“谢谢您”,而且几乎是倒退着走出去的。
对诊所员工而言,待在前面那个诊室等候谈话时,每一分钟都过得很慢。弗里德里卡·萨克森到她四楼的房间拿来几张报纸,开始做智力游戏。此前有人议论,该不该让她独自一人去楼上,但萨克森小姐态度坚决地说,她不想坐在那里浪费时间,无所事事,等着警方找她去谈话。她还说自己没有把凶手窝藏在楼上,没有提出销毁相关证据,也没有反对其他员工陪着她一起上去,以满足他们的好奇心。这种得罪人的坦率引起了一阵低声的不满,不过也有人说尽管放心。博斯托克太太突然说,她想去医用图书馆拿本书,于是这两个女人就离开了房间,过了一会儿又一起回来了。人们一开始还看见过卡利,他说自己算个病号,后来因为肚子疼就提前回家去了。唯一剩下的病人金太太被找去谈话之后,就让她丈夫把她带走了。伯奇先生先一步走了。此前他曾大声抗议说,他的治疗受到了干扰,整个过程中精神受到了创伤。
“跟你们说吧,他有点儿自鸣得意,很明显吧?”肖特豪斯太太对集中在那里的工作人员悄悄地说,“警司早就想叫他走了,我跟你们说吧。”
肖特豪斯太太好像有很多事情要跟他们说。她得到允许,可以到一楼后面的小厨房去煮咖啡,做三明治,这就给了她借口在大厅里来回不停地走动。她几乎是一个一个地端来三明治,连杯子也是一只一只拿去洗的。这样的来来往往使她有机会向其他工作人员报告最新情况。每个人都焦急地期待着新的消息,而且抑制不住内心的渴望。肖特豪斯太太不是他们期待的密使,但不管消息是如何得到的,或者由谁转述的,都有助于他们减轻由悬念造成的压力,而她对警方程序的了解的确出人意料。
“现在有好几名警察在大楼里搜索,而且门口也有他们的人。当然,他们还没有发现任何人。这个嘛,也是有理由的。我们知道,凶手不可能已经走出这幢大楼,或者说,根本没进来。我跟那个警官说:‘这幢诊所我今天已经全部清理过了,所以跟你们的人说吧,别到处乱踩……’
“警方的医生已经查看过尸体。指纹采集师还在楼下采集每个人的指纹。我还看见了摄像师。他带着三脚架和一只上白下黑的大包在大厅里拍照……
“还有件搞笑的事。他们在地下室的升降梯上寻找指纹,测来量去的。”
弗里德里卡·萨克森抬起头,似乎想说点什么,接着又继续干她自己的事。地下室的升降梯面积大约四平方英尺,是靠绳子和滑轮工作的。当年诊所还是一座私宅的时候,它一直被用来从地下室的厨房向一楼餐厅运送食物。直到今天,它还没有被拆掉,偶尔还有人用它把病历档案室的医疗记录送到二楼和三楼的诊疗室中,除此以外,这部升降梯没有多少用处。谁也无法提出任何理由来解释警方为什么在升降梯上寻找指纹。
肖特豪斯太太端着两只杯子去洗,不到五分钟她就回来了。
“劳德先生正在总务处给主席打电话,我想是在汇报谋杀案的事。这将使医管会主席多一些谈资,不会有错的。安布罗斯护士长正和一个警察核对亚麻布物品的清单。好像艺术疗法室缺了一件橡皮围裙。哦,还有一件事。他们正在让锅炉熄火。我想他们想从里面把那件东西找出来。我必须说,这对我们有好处。到星期一,这个地方会冷得要死……”
“运尸车来了。他们就是这么叫的——‘运尸车’。你看,只要受害者已死,他们就不用救护车了。你们可能听到它来了。我敢说,要是你们把窗帘拉开一些,就会看到她被弄进车里。”
可是谁也不想拉窗帘。担架员那缓慢、笨重、小心的脚步跨出大门的时候,诊室里鸦雀无声。弗里德里卡·萨克森放下手中的铅笔,好像祈祷似的低下了头。前面大门关上之后,从轻微的呼吸声中,可以听出他们都大大地松了口气。一阵短暂的沉寂后,那辆车开走了。肖特豪斯太太是唯一说话的人。
“可怜的小讨债鬼!跟你们说吧,由于这样那样的原因,我知道她在这里最多只能再干六个月。可是我绝对没想到她是死后被人抬出去的。”
珍妮·普里迪坐在治疗用长沙发的边沿,离其他工作人员有一段距离。警司与她的约谈意想不到地简单。她不知道自己当时会面对什么,当然也没想到会面对一个平静、温和、声音深沉的男人。她还处于发现尸体后的震惊中,但他并没有对她表示同情,没有冲她微笑,更没有表现出父亲般的关心和理解。他给她的印象是:他的兴趣在于尽快让真相大白,而且希望每个人对他都有同样的感觉。珍妮小姐心想,在他面前说谎很难,而且她也没想说谎。整个过程都是直来直去,也很容易被记住。警司的问题围绕她和彼得在地下室的十分钟左右的时间。这原本也是意料之中的。很自然,他想知道彼得从邮局回来之后到和她相遇之前的这段时间里,她有没有可能杀害博勒姆小姐。但这不可能。她跟在彼得后面,两人几乎是同时走下楼梯的,而肖特豪斯太太可以作证。也许杀博勒姆不用很长时间,可是不管彼得动作有多快,他都没有作案时间。她尽量让自己不要去考虑这件突然发生的、残暴而有预谋的暴力行为。
她想到了彼得。在这几小时的孤独中,她大部分时间都在想他。然而今晚,这熟悉而温馨的想象却被焦虑所刺痛。他会不会对她的表现感到生气?发现尸体时,她投入他的怀抱,然后惊恐地尖叫了起来。想到这里,她感到有点难为情。当然,他一直那么宽容和体贴,不工作的时候也总是很体贴人,总是记得她。珍妮知道他不喜欢大惊小怪,也讨厌任何感情的流露。她逐渐学会接受他们的爱,再也不敢怀疑它的真实性,而且对他的条件全盘照收。自从发现博勒姆死亡之后,他们在护士值班室有过短暂的接触,她基本上没有再和他说话。她无法想象他有什么感受。但是有一点可以肯定:她今天晚上不能再给他当模特,摆各种造型了。这与羞耻感和负罪感毫不相干;他早就使她逐步摆脱了这两个羁绊。他会期待她如期来到工作室。毕竟,她的不在场证据是确定无疑的,而她的父母亲会相信她在上夜校。彼得会觉得没有合理的理由来改变他们的安排,而他希望什么事都要有理由。可是她做不成了!至少今天晚上不行。接下来可不是摆造型的时候。她不可能拒绝他,也不想拒绝。可是今晚博勒姆死了,她觉得自己无法再听人摆布了。
与警司谈话出来之后,斯坦纳医生坐到她身边,表现得很和蔼。斯坦纳医生确实非常和蔼,尽管他有些懒散,也喜欢取笑自己的病人,但是他的确非常关心人。巴古雷医生恰恰相反,他工作非常努力,经常在办公室里累得要死,可是他根本不喜欢别人,只是希望自己能表现得像是关心他人。珍妮也不知道自己怎么对此一清二楚。她以前还真的从来没有这么想过。可是今天晚上,发现尸体的冲击过去之后,她的思维出奇地清晰。不仅如此,她的整个认知能力都变得十分敏锐。她周围的有形物体——罩着长沙发的印花棉布、沙发脚下叠放着的红毯、放在办公桌上的各种绿色植物和金色菊花都比以前更加清晰、明亮、真实。她看见萨克森小姐手臂弯曲着放在办公桌上,护着她正在看的那本书,她前臂上的汗毛在台灯灯光映衬下也清晰可见。她想知道彼得是不是总能以惊奇和清晰的方式看见他四周的生活。这感觉就像一个出生在陌生世界的人,看见了造物的第一抹明亮色彩般。也许这就是一个画家所感觉到的。
“我觉得是白兰地。”想到这里,她哧哧地笑了笑。她记得半小时前曾听见安布罗斯护士长嘟囔着抱怨什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