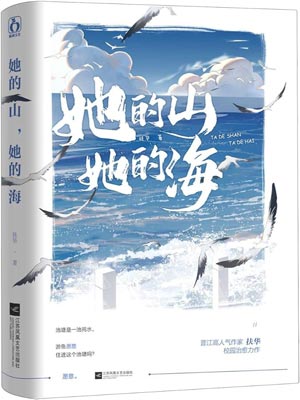P. D. 詹姆斯提示您:看后求收藏(350中文350zw.com),接着再看更方便。
“是她的相册,先生。大部分是女童子军营地的照片。看来她每年都和姑娘们出去。”
达格利什心想,也许那就是她一年一度的休假。他尊重那些自动放弃假日与别人的孩子在一起的人,这就像是个奇迹。他并不喜欢孩子,与大多数男孩子在一起,不消片刻,他就发现自己无法忍受。他从马丁手里接过相册。这些照片很小,摄影技巧一般,是小型厢式相机拍的。它们都很仔细地贴在相册上,每张照片上都有清晰的白色印记。照片上,女童子军徒步行进,在汽化煤油炉上做饭,支帐篷,用毯子围着篝火,进行装具检查。许多照片上都有她们的队长(一个体态丰满、像母亲的女人)在微笑。很难把这个丰满、愉快而又外向的女人和档案室地板上的那具可怜的尸体联系在一起——也很难把她和斯蒂恩诊所工作人员所描述的那个有强迫症的、大权在握的行政主管联系在一起。这些可怜的照片下面有一些愉快的记忆:
“‘燕子’队在分菜。雪利在注意那个有雀斑的小家伙。”
“从幼年童子军‘飞来’的瓦莱利。”
“‘翠鸟’队在洗碗。苏珊抓拍。”
“队长帮助洗刷!简拍摄。”
最后一张照片上,博勒姆小姐滚圆的肩膀钻出海浪,有五六个女童围绕着她。她披下的头发像海草般湿漉漉的,垂在她笑盈盈的面颊两旁。两个侦探看着这张照片,一阵沉默。然后达格利什说:“我们还没有见到什么人为她流泪,是吧?只有她堂妹,与其说感到悲痛,不如说是感到震惊。不知道‘燕子’和‘翠鸟’们会不会为她流泪?”
他们合上相册,继续搜索。最后只有一样东西令他们感兴趣,而且的确非常耐人寻味。那是博勒姆小姐死的前一天写给她律师的信件复印件。她要约见她的律师,事关“我遗嘱的修改,我们昨天晚上曾经在电话上简短地交谈过”。
调查了巴兰坦公寓之后,调查出现了空当期。这是不可避免的耽搁,可是达格利什发现它难以接受。他的办事效率历来比较高。他的名气不仅靠办案的成功率,也依靠办案的速度。他从未仔细想过处理这种工作的复杂。知道一点就够了:这样的耽搁对他的刺激比对其他大多数人都大。
也许这样的耽搁本在意料之中。指望伦敦的律师于星期六下午来自己办公室几乎是不可能的。巴布考克与霍尼维尔律师事务所的巴布考克先生,星期五下午和妻子飞往日内瓦去参加朋友的葬礼了,要下周二才能回伦敦。从电话上得知这个消息,他觉得十分扫兴。霍尼维尔此刻不在事务所,不过如果巴布考克手下的主管能帮得上忙,他将于星期一上午去他的办公室。说这些话的人是值班员。达格利什不知道这位主管能帮上多少忙。他还是特别想见巴布考克先生。这位律师有可能提供博勒姆小姐的财务状况及家庭状况的信息,不过他在提供这些信息的时候,至少会表现出某种程度的不乐意,达格利什需要施展一些智谋。先去见巴布考克先生的雇员是极不明智的行为,对达格利什的成功不利。
在获得遗嘱的细节之前,达格利什没有必要再去见玛丽安护士。他为没能立即执行自己的计划而焦虑。在没有马丁陪伴的情况下,他独自驱车去了内格尔家。他没有明确的计划,不过也不担心。他会很好地利用这段时间。他可以在嫌犯家中边谈,边听,边看,边研究。他的一些最有用的工作都是在这种没有计划、几乎随意的过程中完成的。他能从不经意流露的信息中了解一个人(即受害者)的人格信息。对于任何谋杀案而言,这都非常重要。
内格尔住在埃克莱斯顿广场附近的平里科,住在一幢高大的白色维多利亚式大楼的五楼。达格利什大约三年前来过这条大街。这幢房子已经年久失修。可是现在潮流变了。在伦敦无端风行的时髦和流行的浪潮有时候会忽视一个地区,而横扫另一个地区,在洗刷了一条宽阔的大街之后,又恢复了它的秩序和繁华。从房产代理商牌子的数量上就可以看出,房地产投机者像往常一样嗅出了潮流在回归,并且收获了预期的利益。拐角的那幢房子看来是新近油漆的。沉重的前门敞开着,门里面有一块牌子,上面写着承租人的姓名,不过没有门铃。达格利什推断,这些单元房都是自成一家,管理房子的人肯定住在附近,而且整幢大楼在夜间上锁之后,如果有人按门铃,他就会来开门。他没有看见升降梯,所以径直走上五楼去找内格尔的住房。
那是一栋明亮、通风的公寓,非常安静。到了四楼也没有发现生活的痕迹,只听见有人在弹钢琴,而且弹得很好。也许是个职业音乐人在练习。高音像瀑布一样落在达格利什头上。在接近五楼的时候,他耳中的声音渐渐低了下去。在五楼有一扇带铜制大叩门器的普通木门,上面的牌子上写着“内格尔”。他才叩了一下,就听见内格尔高声回应“来了”。
这套公寓令人称奇。达格利什几乎不知道自己要期待什么,但肯定不是这间极为宽大、通风良好、令人难忘的工作室。它占据了这套房子的整边,北面的大窗户没有拉上窗帘,可以看见被扭曲的烟囱盖和不规则的倾斜屋面。屋子里不止内格尔一个人。他双膝分开坐在一张狭窄的床上。那床搁在屋子右侧一座凸起的平台上。在他的对面蜷缩着穿睡衣的珍妮·普里迪。他们正在用两只蓝色大杯子喝饮料。他们身边的小桌子上有一个托盘,上面有茶壶和牛奶。屋子中间的画架上放着内格尔最近还在画的一幅画。
看见达格利什,这个姑娘并不觉得害羞,不过她把腿从床上放下去,冲他笑了笑。这笑容显然是高兴的,几乎可以说是在欢迎他,当然,也是没有礼貌的。
“喝点茶吗?”她问道。
内格尔说:“警察在执行任务的时候什么都不喝,包括茶。最好把衣服穿上,孩子。我们不想让警司感到惊讶。”
这个姑娘笑了笑,一只手臂夹着衣服,另一只手上端着茶盘,消失在工作室另一端的一扇门里。从这个自信、性感的人身上,达格利什很难看到在斯蒂恩诊所第一次见到的那个泪流满面、完全不同的小孩子。他看着她走过去。除了内格尔的睡袍,她几乎是光着的;她的胸部从薄薄的羊毛内衣中凸起。在达格利什看来,他们曾经做过爱。她从视线中消失之后,他转向内格尔,从他的眼睛中看出了短暂、愉快的期待目光。不过他们都没有说话。
达格利什在工作室内到处走动,床上的内格尔用眼睛看着他。这间房子并不杂乱无章,它显得很整洁。这使他想起了伊妮德·博勒姆的公寓,当然,除此以外,它们在其他方面没有共同之处。平台上是张简易木床、椅子和小桌子,显然是用作卧室的。工作室的其他地方都是画家的半成品,没有不守规矩的胡乱涂画,但也没有与艺术家生活有关联的。南边的墙上有十几张大油画,达格利什很惊讶地发现它们蕴含着冲击力。这里不是业余画家放纵自己才华的小天地。珍妮小姐显然是内格尔唯一的模特。她具有胸部丰满的少女身材,摆出各种造型看着他,这儿故意短一点,那儿有趣地长一点,好像画家的才华都融化在他的技巧之中。最近的一张画仍然在画架上,画上的这个姑娘两腿分开,坐在一张小圆凳上,两只孩子般的手自然地放在大腿两侧,两只乳房向前凸出。在这样的技巧中有几点非常突出,那就是绿色和淡紫色的大胆运用,以及细腻的色调关系,这勾起了达格利什的回忆。
“是谁教的你?”他问道,“萨格?”
“是的。”内格尔并不感到意外,“你知道他的作品?”
“我有一张他早期的作品。裸体画。”
“你投资投对了,暂且不要出手。”
“我正是这么想的,”达格利什小声说,“我很喜欢那张画。你和他在一起的时间长吗?”
“两年。当然是在业余时间。再过三年,我就能教他了,当然,如果他还能学的话。他老了,沉湎于自己的套路。”
“你似乎是在模仿它们。”达格利什说。
“你这么看?有意思,”内格尔似乎没有受到冒犯,“这就是我最好还是离开的原因。最晚到这个月底,我就要到巴黎去了。我申请到了贝林格奖学金。老人家替我美言了几句。上个星期,我接到一封回信,说这机会是我的了。”
他尽管试图克制自己,可仍未能掩饰声音中胜利的情绪。在他那冷漠的语气中,可以听出一丝喜悦。他有理由为自己感到骄傲。贝林格奖学金不是普通的奖学金。达格利什知道,这意味着这个学生可以在欧洲的任何城市居住两年,既有一笔丰厚的津贴,又可以选择自己的生活和工作。贝林格信托基金是由一个专利药品制造商建立的。他死的时候非常富有,而且非常成功,但是并不满足。他的钱来自粉状胃药,但是他的内心很痛苦。他的才能很一般,从他捐赠给当地绘画博物馆的绘画收藏品就能看出,他的品位和他的表现一样。但是贝林格奖学金能确保艺术家对他感恩戴德。贝林格认为,在贫困中是不可能有艺术繁荣的,冷阁楼和空肚皮不能激发艺术家格外努力。他在贫困中度过年轻时代,没有欣赏到艺术和生活。他上年纪之后,游历很广,并幸福地生活在国外。贝林格奖学金使有前途的年轻艺术家享受后者而不经受前者,是值得拥有的奖学金。如果内格尔得到这笔奖学金,他就不会再经历像斯特恩诊所的这些麻烦事情了。
“你打算什么时候去?”达格利什问道。
“我想去的时候。不管怎么说,这个月末吧。不过我也可能早点去,而且不打招呼。没有必要惊动什么人。”
他歪着头朝远处那扇门看了一眼说:“这就是这项谋杀令人厌恶的原因。恐怕它会是个阻碍。毕竟,那是我的凿子。这还不是把我拖下水的唯一动作。我在办公室等邮件的时候,有人打电话要我到下面去收待洗衣物。电话好像是个女人打的。当时我把外套穿上,正要出门,所以我说我回来之后再去取。”
“所以你送完邮件后要去见玛丽安护士,问待洗衣物准备好没有?”
“对的。”
“当时你为什么没有把电话的事也告诉她?”
“我不知道。好像没有必要。我不想在麦角酸诊室前面徘徊。这些病人的呻吟和低声耳语让我浑身起鸡皮疙瘩。玛丽安护士说还没准备好,我还以为是博勒姆小姐打的电话,现在这么说已经没有用了。她对护士责任方面的事管得有点多,或者说他们是这么看的。反正关于这通电话的事,我是什么也没说。我本可以说,但是没有。”
“第一次找你谈话的时候,这两点你都没有告诉我。”
“又对了。实际情况是,我觉得整件事情有点蹊跷,我需要时间来考虑考虑。呃,我考虑好了,有必要让你知道这件事情。你可以相信,也可以不相信,随你的便。这对于我来说都一样。”
“如果你真认为有人想把你拖进这场谋杀,你怎么这么处之泰然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