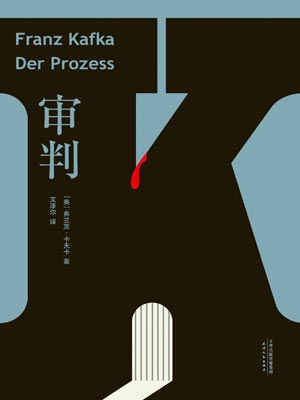赖特·米尔斯提示您:看后求收藏(350中文350zw.com),接着再看更方便。
四
现在,社会科学家在政治上和学术上——两个维度在此互相重合——的首要任务,就是厘清当代的不安与漠然都包括哪些成分。这是其他文化工作者——从自然科学家到艺术家,乃至于整个学术共同体,对他们提出的核心要求。我相信,正是由于这项任务和这些要求,社会科学将日渐成为我们这个文化时代的共同尺度,而社会学的想象力也将愈益成为我们最需要的心智品质。
在思想上的每一个时代,都会有某种思考风格趋于成为文化生活的共同尺度。不过,放眼当下,有许多思想时尚蔚为流行,却也只是各领风骚一两年,然后就被新的时尚所取代。这样的狂热或许会使文化这场戏更加有滋有味,但在思想上却只是轻浅无痕。而像“牛顿物理学”或“达尔文生物学”之类的思维方式则不是这样。这些思想世界个个影响深远,大大超出观念和意象的某一专门领域。无论是引领时尚的论家,还是籍籍无名的学者,都能基于这些思维方式的用语或从中衍生的用语,重新定位自己的观察,重新梳理自己的关切。
精神分析学者反复指出,人们的确常常“愈益感到被自己内心无法确定的模糊力量所推动”,事实确实如此。欧内斯特·琼斯曾有言曰:“人的主要敌人和危险就是他自己的桀骜本性,就是他心中被禁锢的黑暗力量。”然而,此言谬矣。正相反,现如今,“人的主要危险”乃在于当代社会本身桀骜难驯的力量,以及其令人异化的生产方式、严丝合缝的政治支配技术、国际范围内的无政府状态,简言之,即当代社会对人的所谓“本性”、对人的生活的境况与目标所进行的普遍渗透的改造。
在现代西方社会,物理科学和生物科学已成为严肃思考与大众玄学的主要共同尺度。“实验室技术”成为普遍接受的程序模式和学术保障的源泉。这就是学术上的共同尺度这一观念的意义之一:人们可以基于它的用语陈述自己最牢固的信念;而其他用语、其他思考风格,似乎沦为回避问题和故弄玄虚的手段。
比如,如果不考察工作,我们甚至无法表述休闲问题。要想把漫画书引发的家庭困扰这个问题梳理清楚,就不能不结合当代家庭与社会结构的新近制度之间的新关系,考察当代家庭所面临的困境。要是没有认识到不适与漠然如今已经在多么大的程度上构成了当代美国社会的社会风气和个人倾向,那么,无论是休闲,还是它那些令人萎靡不振的实际应用,都不会被视为问题。在这样的风气和倾向下,如果没有认识到进取心作为在合作经济中工作的那些人的职业生涯的重要成分,也已遭遇危机,那就无法阐述更无法解决任何有关“私人生活”的问题。
一种共同尺度大行其道,并不必然意味着不存在任何其他的思维风格或感受模式。不过它的确意味着,往往会有更加普遍的学术兴趣转向这一领域,在那里得到最明晰的梳理,一旦其得到如此梳理,就会在一定程度上被视为已经成功,即便不是成功找到解决之道,至少也是成功找到一种有益的推进方式。
这一切是如此令人瞩目,以至于观察家们往往解释道,如今需要梳理的问题的类型本身已经有了变化。我们常常被告知,我们这十年的问题,甚至我们时代的危机,已经不再局限于经济这个外部领域,现在成了与个人生活质量有关的问题,这其中其实牵涉到这么一个问题:是否不久之后就不再有什么可以被恰当地称为个人生活了。人们关注的焦点不再是童工,而是漫画;不再是贫困,而是大众休闲。不仅有许多私人困扰,而且有许多重大公共议题,都被从“精神病学”的角度来描述。这样的努力往往显得可悲,因为这是在回避现代社会的大议题、大问题。这样的表述似乎往往只依赖于一种狭隘的地方意识,只对西方社会感兴趣,甚至只对美国感兴趣,从而忽略了全人类其他三分之二的人口。它还常常武断地将个人生活与更大范围的制度相脱离;而人们的生活就是在那些制度中展开的,后者对于个人生活的影响,有时会比孩童时节的亲密环境更为严重。
我相信,社会学的想象力正成为我们文化生活主要的共同尺度,成为其标志性特征。这种心智品质体现于社会科学和心理科学中,但远远不限于我们目前所知的这些研究的范围。个体乃至整个文化共同体要获得社会学的想象力,乃需要点滴积累,往往也需要蹒跚摸索,然而许多社会科学家对这种品质缺乏自觉意识。他们似乎不知道,要做出他们可能做出的最佳研究,关键就在于运用这种想象力。他们也不明白,由于未能培养出这种想象力并加以应用,也就未能满足日渐赋予他们的文化期待,那原本是他们这几个学科的经典传统留下来的可用遗产。
然而,对于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遭受威胁的这些价值,人们往往既没能广泛承认其为价值,也没能普遍感受到它们面临威胁。大量私人的不安就这么得不到梳理,大量公众的不适,以及众多极具结构相关性的决策,都从未成为公共议题。而对于接受理性和自由之类的传统价值的人来说,不安本身就是困扰,漠然本身就是议题。这种不安和漠然的境况,就是我们时代的标志性特征。
不过,出于对事实与道德的关注,文学作品和政治分析通常要求具备这种想象力的品质。它们的具体表现形式虽然五花八门,但已经成为判定思想努力和文化感受的核心特征。一流的评论家和严肃的新闻记者都很好地展示出了这些品质。事实上,两者的工作往往都是从这些角度来评判的。流行的批评范畴,如高雅趣味、中级趣味和低俗趣味,在现在的社会学意味与美学意味至少可以说不相上下。小说家的严肃作品体现着对于人类现实流传最广泛的界定,其中往往就蕴含着这种想象力,并努力满足相关的要求。借此,人们便可以寻求从历史的角度为当下定向。由于有关“人性”的意象变得更成问题,人们感到越来越需要更加密切地、更具想象力地关注那些社会惯例和社会巨变,因为它们在这个充满民间躁动和意识形态冲突的时代揭示着人的性质。虽说时尚往往正是被应用时尚的尝试所揭示出来的,但社会学的想象力并不仅仅是一种时尚。它是一种特别的心智品质,似乎以极其令人瞩目的方式,承诺要结合更广泛的社会现实,来理解我们自身私密的现实。它并不只是一种与当代诸多文化感受力并立的普通的心智品质。唯有这种品质,它的应用更为宽广,更为灵便,并会就此做出承诺:所有这类感受力,其实就是人的理性本身,将会在世间人事中扮演更重要的角色。
在20世纪30年代,人们基本没有什么怀疑,只有某些自欺欺人的工商界人士觉得经济议题也就是一堆个人困扰。在这些有关“资本主义的危机”的争论中,对马克思的梳理,以及许多未曾明言的对其著述的重新梳理,或许确立了这个议题的主导论调,有些人开始从这些角度来理解自己的个人困扰。大家都很容易看到是哪些价值受到威胁并予以珍视,而威胁它们的结构性矛盾也似乎一目了然。人们对这两点都有广泛而深切的体验。那是一个讲政治的年代。
自然科学作为更传统的主要共同尺度,其文化意义越来越让人怀疑了。许多人开始觉得,作为一种思想风格的自然科学有些不够充分。科学风格的思维和情绪、想象与感受,其充分性当然从一开始就面临宗教上的质疑和神学上的争论。但我们的历代科学前辈们成功地平息了这类宗教质疑。目前的质疑是世俗的,是人本主义的,往往很让人困惑。自然科学晚近的发展固然在氢弹的发明及其环球运载手段方面达到了技术上的巅峰,却并未让人感到,对于更大的思想共同体和文化公众群体所广泛知悉并深切思虑的那些问题,它能就其中任何一个提出解决之道。人们认为这些发展是高度专业化的探究的结果,这没有问题,但要觉得它们是令人惊叹的奇迹,就有些不合适了。它们在思想上和道德上所引发的问题其实多于它们已经解决的问题,而它们所引发的问题则基本全部属于社会事务,而非自然问题。在高度发达的社会中的人看来,征服自然,克服稀缺,明显几近大功告成。如今在这些社会里,科学作为这种征服的首要工具,让人觉得肆无忌惮,漫无目标,有待重估。
我们的时代弥漫着不安和漠然,但这种不安和漠然又还不能得到清楚阐明,并接受理性的分析和感性的体察。它们往往只限于模糊的不安造成的苦恼,而不是从价值和威胁的角度得到明确界定的困扰。它们往往只是沮丧的情绪,让人觉得一切都有些不对劲,却不能上升为明确的论题。人们既说不清面临威胁的价值是什么,也道不明究竟是什么在威胁着他们。一句话,它们还没到能让人做出决策的程度,更不用说被明确梳理成社会科学的问题了。
现代社会对科学的敬重早已徒具其表,而时至今日,与科学维系一体的那种技术精神和工程想象与其说是充满希望与进步的情怀,不如说更可能是令人惊惧、形象模糊的事物。诚然,所谓“科学”,意涵并非尽在于此,但人们恐惧的是,这样的意涵会慢慢成为科学的全部。人们觉得需要对自然科学进行重估,就反映出需要找寻一种新的共同尺度。从科学的人文意义和社会角色,到其牵涉的军事议题和商业议题,乃至其政治意涵,都在经受着令人困惑的重估。军备方面的科学进展有可能导致世界政治重组的“必要性”,但人们并不觉得这种“必要性”仅凭自然科学本身就能解决。
但是,假如人们对自己珍视什么价值浑浑噩噩,又或者没有体验到任何威胁呢?这就是所谓漠然的体验。而如果这种态度似乎波及所有价值,那就成了麻木。最后,假如他们浑然不知自己珍视什么价值,但依然非常清楚威胁本身的存在呢?那就会体验到不安,体验到焦虑,如果牵涉面足够广泛,就成了完全无法指明的不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