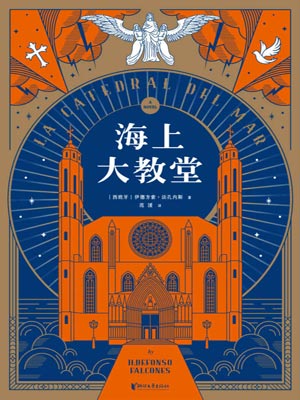高满堂提示您:看后求收藏(350中文350zw.com),接着再看更方便。
那嫌犯说:“他打的!”
一听这个嫌犯瞎告状,汪新气不打一处来,对马魁说:“他自己摔的,这小子偷了东西不承认,还骂骂咧咧的!”
马魁皱着眉头问:“那你就动手?”
汪新叫屈:“我没有!”
那嫌犯扯着嗓子喊:“就是你推的我,好多人都看见了。”
汪新被诬陷,气得青筋直蹦,马魁示意他离开,等一会儿再过来。汪新走出餐车,站在外面说不出有多憋屈。过了好一阵子,马魁走了出来,汪新忙迎上去问:“马叔,都审完了?”
马魁板着脸,没有说话。
汪新没意识到问题的严重性,自顾自地说:“您是没看见那小子当时有多赖,死不承认!”马魁沉默片刻后,说道:“你说钱包是他偷的,可根本没人能证明,他愣说自己捡的;你说是他自己摔一跟头,也没有证据,现在这小子嚷嚷着要找领导,还要索赔。”
“怎么没证据啊?车上那么多人都看见了。”
“这都多少站了,目击者早就下车了,上哪儿给你找证人去?”
“那我就活该被冤枉?”
听到汪新说“冤枉”,这个词对马魁来说既敏感又扎心,没人比他更能体会被冤枉的滋味,失去自由的那十年,有多少血泪都得往肚子里咽。汪新此时的心情,马魁比谁都懂。
一下火车,马魁就被叫到胡队长办公室。胡队长神色凝重,问汪新打人是否属实。马魁说,是那小子自己摔了一个跟头,磕破了鼻子和下巴,跟汪新没关系。胡队长苦着脸说,可没人能证明啊。在餐车审问的时候,有个乘客跟汪新辩了几句,他还把人家挤对一通。马魁认为警察办案,旁人七嘴八舌那是在添乱。见马魁向着徒弟,胡队长拿出一张报纸,指着上面的一则豆腐块文章让他瞅,这事儿都上报纸了。
一听上报了,马魁意识到事情闹大了,后果很严重,忙拿过报纸看。胡队长说:“那个乘客是大学老师,教法律的,把那天的情况写了篇文章,还添油加醋地描述了一番,现在小汪浑身是嘴都说不清了。”马魁问:“组织上打算怎么处理?”“正在研究呢!本来也不是什么大事儿,可是一上了报纸,那情况可就不一样了。局里头刚刚来电话问呢,我都不知道咋说。”
马魁沉默良久,他知道,汪新遇到人生的大坎儿了。
走出胡队长的办公室,马魁顺道去了一趟菜市场,买了一兜子菜往家走。他瞧见汪新站在不远处,看样子有话要说,马魁走到汪新近前,不咸不淡地说:“天太热了,眼睛里都冒火了。”
汪新压抑着情绪说:“心里也冒火了。”
“那就喝点凉白开,降降火。”
“一句好话都没给我说,是吧?”
“那又怎样?”
“马叔,我是冤枉的。”
“冤没冤枉,你自己说了不算,头上有警徽,身上穿警服,做事得擎住这个‘警’字!”
“马叔,告诉您个好消息,我这身警服穿不成了,您可以好好喝顿大酒了!”
马魁看着汪新,一时无语。汪新挺直了腰板,大步流星地离开。望着汪新远去的背影,他心里五味杂陈。
儿子遇到这么大的事儿,汪永革还不得出面说道说道。他来到乘警队邀请胡队长到家里唠唠嗑儿,喝点酒。不等胡队长说话,汪永革就像点炮仗一样噼里啪啦说起来:“那小崽子,可把我气死了,他怎么能脑子一热,就不管不顾地做出违反规定的事儿呢?把我气得狠狠地给了他两撇子,他也知道自己错了,还大哭了一场。老胡,汪新这错犯得不应该,得狠狠教训!可这孩子还年轻,火气盛,工作经验不足,难免会惹祸,会犯错误,要是一棒子打死,那他这辈子就完了。”
“老汪,你说的我都明白。”
“老胡,咱们多少年的交情了,你得想办法救救这孩子啊,我求求你了!”
胡队长叹了一口气:“老汪,你听我说,这事儿已经捅到上面去了,屁大点的事儿上了报纸,那就是天大的事儿。领导很生气,还把我臭骂了一顿,说我管理不严,影响了铁警形象!咱关门说句屋里话,我也想把这盆火压灭了呀,可火烧得太猛了,压不住了!”
汪永革心里拔凉拔凉的,呆在那儿说不出话来。胡队长出主意说:“要不你去找找上面,看还有没有回旋余地。”汪永革撕下脸皮,正想开口求胡队长,人家立马堵住了他的嘴:“你就别为难我了。”
这条路走不通,汪永革只得厚着脸皮来找马魁。他走进马魁家时,马魁正在看报纸。马魁扫了汪永革一眼,接着看起报纸来,既不打招呼,也不让座。
汪永革自顾自地坐下来,沉默了好一会儿,说:“老马,汪新的事,你都知道了吧?”
马魁淡淡地说:“那么大的事儿,想不听见都难。”
“老马,汪新犯了错,应该承担责任,这没的说。可这孩子是个什么秉性,你做师傅的,最清楚。”
“等等,你这是想把我给扯进去呗?”
“你想哪儿去了,我是说你了解汪新,这孩子心眼儿不坏,就是一时冲动,他做事方式不对,可心还是奔着尽职尽责去的。”
马魁不咸不淡地说:“唱得再好听也没用,人家就说他打人了,还说他刑讯逼供。”
汪永革赔着笑脸说:“我知道,可他还年轻,要是为了这事儿栽了大跟头,那就一辈子都站不起来了!再说,这事儿,他确实冤。”
“我知道被人冤枉是啥滋味。当年,要是有人能给我作证,我也用不着蹲十年大牢!你儿子这回能不能把这事儿抖搂利索了,就看有没有人愿意给他作证吧!”
马魁旧事重提,汪永革无言以对,那过去的记忆,是抹不去的,马魁见他沉默不语,冷哼一声说:“还有事吗?”
“老马,汪新这辈子,能活成什么样儿,全靠你了。”
“靠我?那得看你这个当爹的实诚不实诚!”说起往事,汪永革实在无话可说。
“你是不是以为我全蒙在鼓里呢?当年,你明明看见我没推人下去,为啥不能给我作个证?”
汪永革沉默着,打死也不说。
马魁对此既不能理解,也无法原谅,在那么一瞬间,他脑海里闪过两个字“报应”。汪新这孩子不错,这不好的词儿不能套用在他身上,这样不厚道。
马魁还抱着一丝希望,再次问道:“不说话是吧?”
汪永革苦涩地说:“你真的看错人了,那不是我。”
马魁冷笑道:“行,就当我瞎了眼。”
汪永革感觉路都走绝了,心情沮丧地回了家,看到汪新坐在桌前画画,他气急败坏地说:“你还有闲心画画呢?”
汪新没吱声,什么也不想说。汪永革走到桌前,看着画问:“这是什么东西?”
汪新恶狠狠地说:“狼。”
纸上画的是一只恶狼,汪新气呼呼地说:“老马头不讲情面,没人味儿,狼心狗肺!”
汪永革责备说:“你怎么总说人家的不是!你要没惹祸在先,人家能说道上你吗?”
“就算我没惹祸,他也是看我一百个不顺眼!”
“你再犟嘴!”
“本来就是这么回事,还不让说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