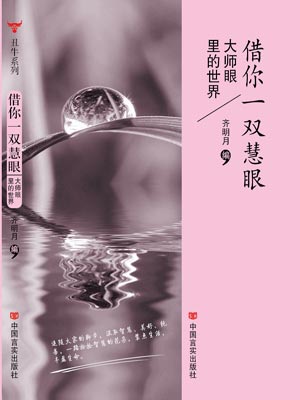塞巴斯蒂安·巴里提示您:看后求收藏(350中文350zw.com),接着再看更方便。
第一天晚上,我是蜷缩在一片废弃的荒地上对付过去的,荒地紧挨着一家整夜喷吐烟尘的大钢铁厂,正好可以作为拍摄电影的外景场地。空气、河流、花园,到处都弥漫着钢铁的尘屑。最初几天,我简直不知道自己是混迹在魔鬼还是天使的行列。我的身体变得沉重不堪,就像是太空人困在一个地心引力超强的星球上。仿佛濒临死亡,又仿佛进入了奇异的来世。要说起来,克利夫兰每天都有人死去。一个雾气蒙蒙的早晨,我看见两个年轻的警察从公园里抬出一具尸体,那是一个穷困潦倒的老人到了生命的最后一息。他们小心地把老人裹在一张旧油布里,扔上一辆垃圾车。
我是个年轻的流浪者,此话一点儿不假。我甚至没有勇气去乞讨,虽然乞丐随处可见。在那段日子里,我很有可能被人杀死,谁也不会注意到。
如我所说,我确实还年轻。年轻可以标上价码。我可以用自己的身体换取几美元,但我还没到那个份儿上。有几个男人,看样子很有钱,不像是流浪汉,他们走到我跟前纠缠不休。每一条人行道上都有心甘情愿奉献自己的女孩和女人,操着上帝创造的每一种语言招揽生意。我还没到那个份儿上,但毫无疑问,那是我再往后必须要走的一步。
这段记忆结尾处是一片完全的空白。
醒来的时候,我发现自己待在一个陌生的房间里,还听到有人在说话,过了一会儿,我才看见方形的窗框里站着两个人影,明亮的阳光倾泻在他们头上,一片耀眼的光辉。短短的一瞬间,我还以为自己回到了都柏林城堡,父亲和两个姐姐正在照看着我。
原来,我昏倒在了卡蒂斯·布莱克先生,也就是卡西的父亲居住的那座公寓楼外面,是他出于善良的本性,把我抱了进来。“我本来不想把你带回家。”他后来这样对我说,用他自己特有的古怪、淡然而又充满友善的语调。当时,他把我放到自己的床上。“你让整间屋子臭气熏天,”他嘴里嘟嘟囔囔地说,决定把我一个人扔下一会儿也没什么大不了的,“我才不管你会不会死掉。”他说着,便一路走去谢克海茨找贝洛太太,把自己的女儿找来帮忙,贝洛太太是她的雇主。“告诉你,”布莱克先生说,“她不想让卡西出来。她付给卡西每星期四美元,可不是让她在外面跟老爸一起到处溜达的。”
不管怎么说,卡西还是马上跟他一起乘坐电车回到家里,发现我几乎都要饿死了,就喂我吃了些东西。平底锅在布莱克先生那个简陋的小煤气炉上好一阵乒乒乓乓。
接下来我一阵呕吐,迷迷糊糊不知道自己身处何地,就像葛丽泰·嘉宝在《瑞典女王》中扮演的克里斯蒂娜,死死抓住卡西不放。
她又给我吃了些东西,这次喂得很有节制。
再往后,我觉得自己睡了很久很久。
我听见卡蒂斯·布莱克在用排箫吹奏曲调。
“都是弗吉尼亚的老歌。”他说。
“我拿不准自己究竟信任不信任爱尔兰人,”贝洛太太说,我们三个——卡西,贝洛太太和我,站在她的厨房里,“信任在雇人方面非常重要。上个在我这儿干的姑娘,一直偷偷摸摸把我的亚麻布拿出去卖钱。我的亚麻布都是上好的爱尔兰亚麻布。她可能卖了个好价钱。”
贝洛太太的衣服像盔甲一样穿在她身上,昂贵的布料看上去很厚实,给人一种奇特的古板感觉,就像是一道绝缘墙。她自然是卡西的女主人,卡西正努力给我找个挣钱的营生。
“克利夫兰有那么多流浪的姑娘,我不能给她们每个人都安排工作。至少你有一点不同,你是卡西带来的。我不能不说,我很信服卡西对一个人的看法。的确是这样。有钱的好人到处都是,但是,没有钱的好人,那种你想留在家里的人,真是很难找。”
卡西从始至终都在微笑,只是微笑,宽宽的脸庞看上去那么满足,那么快乐。但她一句话也没有说。我想她心里非常清楚这条河是深是浅,里面有没有鱼。
“好啦,”贝洛太太说,“你可以在我这儿开始干。试用一段时间。我敢说,你会发现这份工作不那么容易。你个子很小,看上去也不怎么壮实。”
下了这句评语之后,她便回到房子前面去了。卡西用双手紧紧抓住我的肩膀,强壮有力的手指把我的骨头都快捏疼了。她把头来回左右摇摆。
“感谢仁慈的上帝。”她说。
她带我去看马车房上面归我们俩住的小房间。一张大铁床,墙壁四周到处挂着属于卡西的东西,一件宽松长袍,几顶样式很有趣的帽子,一个洗脸盆连同一个大罐子和一块粗糙的东西,可能是石炭酸皂,她零碎物件和小玩意儿放在一张快要散架的小桌子上,此外,还有她那口很深很深的大箱子。总的看来,整个房间非常洁净,但我要说,这房子自从刚一开始用淡黄色的油漆全部粉刷过之后——那应该是一百年前的事儿了,此后再也没有动过一下刷子。我看见墙洞里塞进了碎布,那肯定是冬天为了抵御渗漏进来的寒气才想出的法子。她有一面带镀金镶框的小镜子,金色的涂料一点点剥落下来,就像是营造出了一个小小的秋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