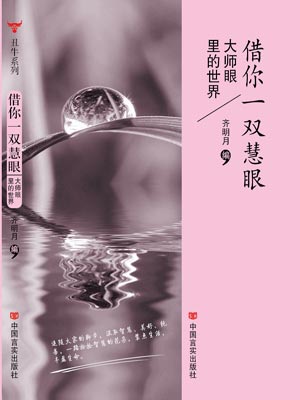塞巴斯蒂安·巴里提示您:看后求收藏(350中文350zw.com),接着再看更方便。
新婚一个月不到,我们收到了玛丽亚·谢里丹那封有名的电报,蜉蝣季到了,我们兴致昂扬地驱车向东前往奥玛德,炫耀我们新婚夫妇的身份。
谢里丹一家就是热情的典范,曼之前就常常说起。谢里丹夫妇没有子嗣,他们常常暗示曼作为他们最爱的侄女,可能会继承奥玛德的房子——想到就令人激动。当蜉蝣黄色的翅膀在谢灵湖<a id="jz_2_1" href="#jzyy_1_2"><sup>[2]</sup></a>上空熙熙攘攘,这就是玛丽亚的朋友和家人期盼已久的信号,他们会抛下一切,来到卡文。尼古拉斯的兄弟菲利克斯,虽然呆头呆脑的,但是温和无害,他会仔细地扫去网球场上的落叶和冬日留下来的垃圾,山上的泉水汇成小溪流下来,他会修理溪流里的旧坝,让鲑鱼栖身的河床深度足以游泳。教区神父、医生、律师、银行经理,周边各色强健的天主教农户们,以及所有的姑母和表亲们,都汇集到这所老房子,好像他们也是一种蜉蝣,遵循着远古的召唤。
我们到之前,曼的兄弟,杰克,已经到了,他气质沉静内敛,身高非比寻常,从罗斯康芒带着他的钓鱼竿和鱼线急匆匆赶来,因为除了飞钓,或许还有打猎,当然了,还有曼之外,他对任何事情都概不关心。当我走进陈旧的走廊,他朝我走来并同我握手,我如释重负。
“好了。”他说。我想在整段做客过程中他总共就说了这么多话。
身为曼的丈夫,我受到了盛情接待,对此我不胜荣幸。长长的餐桌上堆满了农场的水果,我们不仅是客人,更是带来快乐的客人——玛丽亚显然很喜欢她挑选的这些人出现在她家里。
晚上曼大胆地演奏钢琴。白天,她在网球场上大杀四方,不论老少。她穿着深蓝色连体式泳装,自信地在鲑鱼池中转圈,她的亲戚菲利克斯看着她,呆呆地笑着。我对着玛丽亚既安心,又开心,我和她说起我的旅行,她似乎很喜欢,我和她丈夫尼古拉斯谈起桥梁、道路和沟渠,这是我们的三个共同点。尼古拉斯是旧政府时期前太平绅士<a id="jz_3_1" href="#jzyy_1_3"><sup>[3]</sup></a>,也是很少见的天主教地主。
1920年,谢里丹一家曾收留过迈克尔·柯林斯的未婚妻凯蒂·基尔南住在奥玛德。当然了,我们初次造访时柯林斯已经过世。但是独立战争期间,他曾因选举事宜来到卡文,结识了基尔南一家,他们在格拉纳德<a id="jz_4_1" href="#jzyy_1_4"><sup>[4]</sup></a>经营一家小旅馆和一家杂货店。一天,一位来自都柏林的警官被射杀,当时他正在旅馆酒吧喝酒。基尔南一家与那位年轻的警官相识,也和柯林斯相识——冲突中两个对立的阵营,我们在联合国会这样说。那位警官很有可能死于柯林斯同伴之手。但是不论爱尔兰错综复杂的时局如何,九辆载满人的卡车从卡文的军营驶来,车上的皇家爱尔兰警队警察和士兵报复性地将基尔南家的房子,连带着格拉纳德的大部分地方付之一炬。基尔南一家,包括凯蒂在内,逃到了奥玛德,谢里丹一家收留了他们,我相信,在那段动荡的岁月里,这让柯林斯感激不尽。
白嘴鸦在山毛榉上大发牢骚,夕阳落下枝头,失去光彩,网球选手们在暮色中依旧奋战,求胜心切。杰克·柯万从河边归来,钓鱼竿上挂着鲑鱼,老菲利克斯在路上胡言乱语,玛丽亚在屋内生火,煮起一大锅土豆,又烘又烤,显然一切都在井然有序地向前推进,令人鼓舞。
我很自豪,自豪能在这样一群人之间,能被他们接纳。我在基尔纳莱克<a id="jz_5_1" href="#jzyy_1_5"><sup>[5]</sup></a>被大家称为“杰克·麦克纳尔蒂,曼·柯万的丈夫,年轻的土木工程师”——仿佛这是一串高贵的头衔。
我们在非洲的日子,我们的青春岁月,一去不返,千金难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