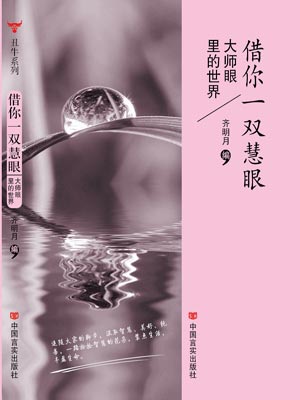塞巴斯蒂安·巴里提示您:看后求收藏(350中文350zw.com),接着再看更方便。
很快我们便抵达了第一个河流站口,我们抛下印第安摩托车,交给那里的摆渡人保管。汤姆用埃维语和他交流,显然是在告诉他我们会及时回来取摩托车。每个人都怡然自得,汤姆惬意地和摆渡人还有他可爱的女儿们说笑。然后我们登上光秃秃的、没有上漆的船,这艘船有些年头了,不是当地人的手艺,是几十年前抢救下来的帝国的遗产,煞费苦心地保持完好,可以在河上使用。我们坐在木凳上休息,两岸繁茂的绿意缓缓流过。两个五十多岁的男子,我敢说是朋友,还是这只是我可笑的错误猜测?两个人不知对着什么大笑,看着疾驰而过的一个个村庄,漫不经心地朝女人们挥手,男孩和女孩们在岸边不知道在忙些什么。这些河岸只开放几秒钟,展示着非洲田园景色,然后随着船猛烈的引擎轰鸣声向前,船舵下的油孔喷出黑烟,这一切就归于终结、遗忘。
因为我们要前往这条河的某条支流,我们换了船。现在我们坐在一艘小得多的木船上,做工粗糙得多,但依旧是欧洲产的。在我的脑海中,我想象着我们坐上越来越小的船,行驶在越来越窄的河流上,最后坐的是一艘空心的独木舟。森林中夜幕降临,我开始担心蚊子,白天猴子的叫声和天知道什么鸟的叫声变成了另一种更加难以捉摸的叫声,有时更加刺耳、热烈,那是夜行的捕食者,鸟类和野兽。缓和的水流给我一夜好眠,醒来时那种奇怪的心情依旧充盈于我内心,这近乎狂喜的心情,标志着纯粹的幸福,再次,再次,就像孩子的心和身体,就像我自己小时候在斯莱戈,在爸爸的房子里。仿佛那一天,那向往的一天,就在我面前,没有恐惧,没有危险。我们在流淌的溪水中洗了脸,一整夜都守着引擎的船夫给了我们一些水果当早餐,大概是在路上摘的,我也不清楚。然后我们到达了河上一个中转点,据汤姆说这里有条小路出去,再走几个小时,就能到提提克普。
汤姆和船夫说了他的安排,我也分不清是不是埃维语,虽然这听起来好像是我不知道的第三种语言,也许是新版本或者带口音的埃维语,就像爱尔兰语在阿尔斯特省、伦斯特省、芒斯特省和康诺特省之间听起来也会有不同。他把摩托车上的挂包甩到肩上,里面有一些换洗衣服和其他东西,尤其是一个小盒子,里面装着他给他妻子米瑞安买的东西,他没有说是什么。然后我们沿着那条小路出发,宽度仅够两个人并肩行走,仿佛在盘根错节的树根和灌木丛之间划出了一条清晰的分界线。
“没多远了,少校。”沿着小路走了两个小时之后,我们在一块空地上休息,他这样说道。
然后,它发生了。那时他正在四处搜寻着什么,在树枝下张望,脚在地面踢踏着,我不知道他在找什么,突然间他停了下来,两只手放在脖子两侧,维持着那样一个奇怪的姿势,眯起眼睛,发出痛苦的剧烈呻吟,我确定那声音里包含了他整个存在的疼痛,整整三十秒,他一动不动,屈膝踉跄着向前,有一会儿左膝跪地,好像一个等待册封的爵士,他灰扑扑的帽子掉落在地,然后他又向下坠落了几分,我以为他就要停在那里,脸离地面还有十五厘米,双手依旧捧着脖子,但是现在他大口喘着气,仿佛无法呼吸,吸不进气,他惊恐地盯着我,那种疑问的、可怕的眼神,就像一个被谋杀的人,他一头栽倒在地上,脸撞上了大地,撞在那两厘米厚的积满落叶的尘土中,他躺在那里,此时双手落在身侧,手掌向上,怪异地扭曲着,仿佛他用某种方式将自己折叠了起来,仿佛他即将完成某项复杂的任务,这项任务要求他屈身伏地,需要他这么做,一项肢体任务,如同他此生高效完成的无数项任务般,爱他的妻子,在军队挖掘运河,杀死日本人,为工作无数次调动,艰辛度日,年复一年,他的优雅和他那该死的善良,全部静止。
“汤姆·奎伊,汤姆·奎伊,”我大喊,“朋友!你怎么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