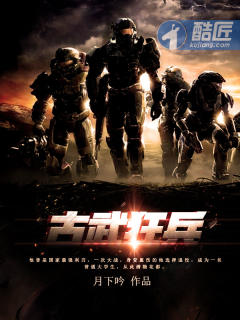奥斯特洛夫斯基提示您:看后求收藏(350中文350zw.com),接着再看更方便。
一月二十一日晚六时五十分……
“我请求大家不要打断我的话,也不要中间插话。我想完整地阐明我们的观点,虽然我早就料到,这是白费口舌,因为你们是多数。”
报务员急忙记录下来,然后放下纸条,用手托着头,继续往下听:
他走上主席台,会场上一片寂静,精神专注。在演说之前常有的这种沉寂却使杜巴瓦感觉到大家对他的疏远和冷淡。现在,他已经失去了在各个支部会上发言时慷慨激昂的劲头,情绪一天比一天低落,现在他仿佛是一堆被水浇过的篝火,冒着呛人的黑烟——这黑烟就是他那被明显的失败和老朋友们坚决反击刺伤的、病态的自尊心,也是死不认错的顽固态度在作怪。他决心硬着头皮一干到底!虽然他也知道,这种做法只会使他同大多数同志离得更远。他发言时压低了声音,但很清楚:
在高尔克村逝世……
杜巴瓦要求发言,立刻得到许可。
他慢慢地记下来。一生中他不知收发过多少喜讯和噩耗,他总是最先获悉别人的悲哀和幸福。他对那些简略而不完整的句子早已不去多加思索,只是仔细地听着,机械地记录下来,根本不去考虑它的内容。
“德米特里,你马上去发言。当然,这已挽回不了局面,显然我们的败局已定。但是必须把图夫塔的话纠正过来。他简直是个蠢货,信口开河,乱说一通。”
现在又有人死了,必须通知某人,如此而已。报务员忘记了这封电文的开头是:“同文发往各站,同文发往各站,同文发往各站!”收报机继续哒哒地响着,老报务员把它逐个译成字母:弗……拉……基……米……尔——伊……里……奇。他平静地坐着,有点儿疲劳了。某个地方有个叫弗拉基米尔·伊里奇的人死了,今天他要给某个人记下这个悲痛的消息,他会因绝望和悲伤而放声痛哭。但是,这与报务员毫不相干,报务员只是局外的旁观者。收报机继续响着:几个点之后是一划,又是几个点,又是一划。他从那些熟悉的哒哒声中已经知道这个词的第一个字母是“Л”,于是把它记在电报纸上。在这之后又写了第二个字母“E”,然后,他工整地写了个“H”,又把H这个字母中间的一小横描了两次。H后面又添上了字母“И”,最后一个字母很容易就写出来了,是“H”。
杜巴瓦接到茨韦塔耶夫的一个纸条:
收报机接着打出一个停顿符号。报务员只用十分之一秒的时间瞥了一眼他刚抄录的那个词——“ЛЕНИН(列宁)”。
“当然,你们可以开除我们,把我们往哪个角落里一塞。现在已经这么做了嘛。我就是从省团委里被排挤出来的。这没关系,究竟谁是谁非很快就会见分晓的。”说完,他就从台上跳下来,走下主席台。
收报机继续哒哒地响着,但是,老报务员又想起了他刚才瞥到的那个熟悉的姓名。他又看了一遍最后这个词:“列宁”。怎么?是列宁?他把电报纸拿远一点,看了一遍电报的全文。老报务员盯着那张纸,看了一会儿,在三十二年的报务员生涯中,他第一次不相信自己记录的东西。
大家静了下来。图夫塔也意识到他的话说过头了。也许这些话现在还不该说。他的脑子陡然一转,前言不对后语地说了下面几句话,想赶紧收场。
他反复看了三次,但仍然还是那句话:
“让他把话说完,听听大有好处!图夫塔说出了别人想说而不敢说的话。”
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列宁逝世。
会场上的吵嚷声越来越厉害了。潘克拉托夫站起来喊道:
老报务员跳了起来,手里拿着那螺线形的纸条儿,全神贯注地又看了一遍。两厘米长的小纸条证实了这个他无论如何也不能相信的消息。他脸色煞白,转过头来,对着两个女同事惊恐地叫道:
“是的,应当有组织党派的自由。否则我们这些持反对意见的人,怎么能捍卫自己的观点呢?怎么能同这样一个有组织、有纪律、团结一致的多数派进行斗争呢?”
“列宁去世了!”
图夫塔仿佛在泅水似的挥动双手,激动而急促地说:
伟人逝世的噩耗从敞开的房门悄悄地溜出了电报房,飓风般迅速闯进车站,冲到暴风雪中,在铁道线、道岔口盘旋,然后随着一阵刺骨的冷风,钻进了机车库那扇半开的大铁门。
“他们是为那帮人在卖力气——从米亚斯尼科夫到马尔托夫!”
机车库里一号修理地沟上面停着一辆机车,抢修队正在修理。波利托夫斯基老头亲自下到地沟里,钻到他那辆机车下面,把有毛病的地方指给钳工看。扎哈尔·布鲁兹扎克同阿尔青正把弯曲的炉条锤直。布鲁兹扎克钳住炉条,放在砧子上,阿尔青一锤一锤地打着。
“俄国共产党可不是议会!”
近年来,布鲁兹扎克老了不少,他所经历过的一切在他额上留下了一条深深的皱纹,两鬓斑白,背也驼了,那双深深陷下去的眼睛里总是显出忧伤的神情。
“你讲什么?又来一次布尔什维克和孟什维克!”
突然,有个人影从半开的门里闪了进来。但是,天色已晚,光线较暗,看不清是谁。铁锤敲打的声音盖住了来人的第一声呼喊。他奔到在机车周围干活的人们跟前时,阿尔青举着抡起的铁锤,没有敲下去。
图夫塔的话被一片愤怒的叫喊声所淹没。
“同志们,列宁去世了!”
大厅里又掀起了一股巨大的浪潮。
铁锤慢慢地从阿尔青肩上滑下,他轻轻把铁锤放在水泥地上。
“既然你们组织了多数派,那我们就有权组织少数派!”
“你说什么?”阿尔青的手像钳子似的一把抓住报信者的皮外套。这个消息太可怕了。
图夫塔那又尖又细的嗓音非常刺耳,他继续说道:
报信人满身是雪,喘着粗气,用低沉而悲痛的声音又说了一遍:
“是呵,这个笨蛋会把事情全给弄糟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