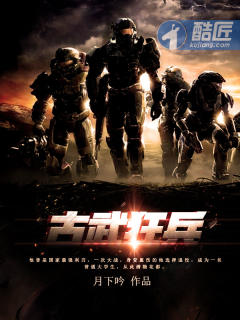米亚·科托提示您:看后求收藏(350中文350zw.com),接着再看更方便。
战败的人消失在各家各户的阴影里。所有人都回来了,除了杜布拉。
“恰恰相反,我是出于对他的尊重。”
两天过去了,我的大哥没有任何消息。我们知道他去了马齐穆伊尼战场,和侵略者的军队会合。其他就不知道了。接下来的几天,没有人提起他的不在,可是一片阴云始终笼罩着我的家。
“你想挑衅他吗?”
第三天,希卡齐决定去见她的兄弟。我不待她请求,便陪她一起去。
“我来这儿正是为了让舅舅看见。”
在穆西西的院子里,我们甚至没有坐下。母亲痛苦的双手在胸前交叉又放下,突然指向前方,仿佛射出指责的利箭:
“在你舅舅回来之前走吧。我弟弟要是见你打扮成这样,会用长矛刺穿你。”
“杜布拉今天还没有回家。你,穆西西,杀死了我的儿子。”
母亲跪在儿子面前,把手覆上他的头,温柔地恳求:
“谁告诉你的?”
父亲双头抱头,来回踱步:热尔马诺·德·梅洛要是知道我们家有人出演了这样不幸的场景,他会说什么?
“梦和我说的。我们是姐弟,我们被同样的祖先拜访。”
“我从未如此清醒。”
“我没见到杜布拉,战斗前后都没有。”
“你疯了吗?”
“你没看见他,是因为我的儿子在战场上变成了另一个人。你杀了他,穆西西。听清楚:你再也不会有属于你自己的夜晚了。”
“我又没有打扮成战士的样子,我就是恩古尼战士。”
这天上午,我独自去了被诅咒的马齐穆伊尼平原,现在改名为“死亡平原”。我去找我的哥哥,隐约地希望他活着。离村的路上,几个村民向我走来,惊讶地问:
“为什么打扮成这样?”父亲又问。
“你要去哪里?这条路是禁地。”
杜布拉没有回答,他忙着拾起散落在地上的饰物。
说出目的地后,他们的眼中流露出一丝恐惧,恳求我不要去。在我的坚持面前,他们摇摇头,迅速离开,就像看到了疯子或麻风病人。踏上错综交叉的小路前,我发现我在大叫着:
“为什么?”
“你们怕我吗?你们当然应该害怕。因为我离开这里时是个女人,回来时是个鬼魂。”
他的伪装被强行撕开。我不知道自己是否感到惊讶:躲在面具背后的不是别人,就是我的哥哥杜布拉。我从地上扶起他,父亲送走了愤愤不平的邻居。最后只剩下我们,卡蒂尼久久地看着儿子,问道:
我不紧不慢地顺着通往平原的山坡向下走。我边走边想:我的哥哥加入战斗的时候,确信了解自己的敌人。而我却恰恰相反:我不知道该恨谁。我不知道该为谁而死。也就是说,我不知该爱谁。我羡慕他,羡慕他失去了生活的意义,却找到了死亡的理由。
“我们看看这倒霉蛋是谁!”
其他人对我和杜布拉的恐惧将我们连在一起。人们害怕他的全然不驯。男人和女人都害怕我。男人怕我,因为我是女人。已婚女人怕我,因为我年轻貌美:我可以是她们的过去。单身女性嫉妒我进入了白人的世界:她们永远无法成为我。
几个男人从震惊中恢复过来,鼓起勇气跳上他的背,用蛮力制住他。他们开始殴打他,这时,我的父亲制止了他们:
我沉浸在这些想法里,没有察觉到自己已经到达悲剧的发生地。踏入战场前,我脱下拖鞋。我光着脚,就像走进陌生人家里一样。我穿过死人、呻吟着的人和奄奄一息的人。死人太多,有一瞬间,我不忍再看。我的眼睛瞎了,站在原地,无法动弹。如此多的身体中,只有我的仍然存在。恢复视力后,我发现我的脚被染红了。这时候我才发现,整个大地都在流血,就像地下的肚腹破裂了。
乍一看,它似乎是最怪异最恐怖的野兽。接着,它的身上散发出一种熟悉感。怪物越展现出人形,就越为恐怖。它就是这样。特希戈诺的头上垂着三根鸵鸟的羽毛。皮制的软帽在脑后用一根带子绑紧,使它的头看起来更大。它的脖子上挂着一条黑色牛皮带子,我们称为廷科索。它的腿上、腹部、手臂上都装饰着牛皮带子。它的腰部则系着一条野猫的皮。一开始,它吼叫的声音更像动物而不是人。不一会儿,我们却发现它吼的是祖鲁语,是侵略者的语言。这个发现加重了恐惧。
衡量战争的残忍程度的,并不是墓碑的数量,而是无处安葬的尸体的数量。我思索着这些,在破碎的尸身、豺狼和猛禽之间选择下脚的地方。
没过多久就轮到我们来证实传言的真实性了:一个巨大的影子跃过围墙,闯进了我们的院子,女人和小孩一阵恐慌。
战争最大的创伤是我们永远不会停止寻找所爱之人的尸体。谁会想到我会成为一个注定穷尽一生在灰烬和废墟之间行走的女人?
但是我没有说。因为天一亮就传来消息,一只鬼魅般的野兽袭击了村庄,在街上四处乱窜。这只怪物——我们叫作特希戈诺——攻击村舍,窜进畜栏,留下一片狼藉。
我在荒野里行走,呼喊着哥哥的名字,徒然地希望他能回答我。
特桑贾特洛的信使离开了,房子周围扫过的沙土上没有留下他的一点足迹。我应该去找母亲,告诉她来自地底的消息。但是我没有。我尊重这里消息的迟滞,整日待在家里,打算第二天上午再和母亲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