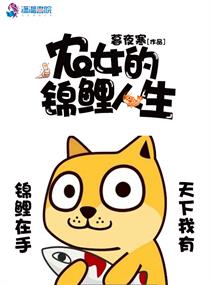弗兰纳里·奥康纳提示您:看后求收藏(350中文350zw.com),接着再看更方便。
呼噜呼噜,拱来拱去,哼哼唧唧。
坐在她旁边的是一个十七八岁的胖姑娘,怒视着一本厚厚的蓝皮书,特平太太看到书名是《人类发展》。女孩儿抬起头,愤怒的目光投向特平太太,好像不喜欢她。看书时有人说话,她似乎是为此而恼怒。可怜的姑娘脸色发青,长了许多痤疮。特平太太心想,这样的年纪有着这样一张脸真是不幸。她冲女孩儿友好地笑了笑,女孩儿却投来更加愤怒的目光。特平太太长得胖,皮肤却一向很好,虽然她已四十七了,脸上却没有皱纹,除了眼角,那是因为她笑得太多。
“把那根水管给我,”她说着便从克劳德手中抢过了水管,“去吧,送那些黑鬼回家,然后歇歇那条腿。”
“嗨,只要有你这么好的性情,”衣着入时的女士说,“胖瘦一点关系都没有。什么都比不上好性情。”
“你看上去像是要吞掉一条疯狗。”克劳德看了看她说,不过他还是下去了,一瘸一拐地走开,没理会她的情绪。
克劳德只是咧嘴笑了笑。
等他走远听不到声音了,特平太太站在猪栏旁,手握水管,看到哪头小猪要躺下,就对着它的臀部冲水。估摸着时间差不多,他应该已经翻过了小山丘,特平太太微微转过头,恼怒的眼睛扫视着小径,他已不见踪影。她回过头来,似乎是打起了精神,耸起肩,深吸一口气。
“哦哦,我够胖的了,”特平太太说,“克劳德想吃什么就吃什么,体重从未超过一百七十五磅,而我呢,就只是看了那些好吃的一眼,就长肉了。”她的肚子和肩膀随着笑声颤抖。“你想吃什么就吃什么,是不是,克劳德?”她转身问他。
“你为什么要对我说那样的话?”她的声音不高,却很凶,比耳语的音量高不了多少,积聚起的愤恨却比咆哮更有力,“我怎么可能既是猪又是我自己?我怎么可能得到了拯救,又来自地狱?”她一只手攥拳,青筋暴露,另一只手紧握水管,胡乱朝老母猪的眼里喷射,根本没听到老母猪愤怒的嚎叫。
“哦,<b>你</b>可不胖。”衣着入时的女士说。
从猪栏可以俯视后面的草场,他们牧养的那二十头菜牛就在克劳德和那男孩儿堆起的干草周围。刚刚剪过的草场向下倾斜至公路。公路那边是他们的棉花地,再过去是一片灰蒙蒙的深绿色树林,也归他们所有。夕阳已没入林后,红彤彤的,俯视着根根树木,如农场主审视他的猪群。
特平太太坐在空出来的椅子上,椅子紧紧箍着她,仿佛一件束身衣。“但愿我能减肥。”她转了转眼球,滑稽地叹了口气。
“为什么是我?”她咕哝道,“这一带的垃圾哪个我没接济过,不管是黑的还是白的。我每天辛苦劳作,还为教堂做事。”
就在那时,里间的门开了,护士的脸出现在门口,叫下一个病人,特平太太还从未见过盘得那么高的一头黄发。坐在克劳德旁边的女人双手抓住扶手,把身子撑起来;她整理了下裙子,慢腾腾地走进护士刚才所在的那道门。
她的身材似乎正适合统领眼前的场子。“我怎么就是猪了?”她质问道,“我到底哪里像它们?”她用水流猛击那些小猪崽儿,“那么多垃圾在那儿。凭什么是我。
“很快就会有人离开的。”特平太太说。她不明白医生挣那么多钱,怎么会连间像样的候诊室都负担不起,他们不过是在医院门口露个头,看你一眼,一天就要收你五美元。这间候诊室比一个车库大不了多少。桌子上乱七八糟地堆着软塌塌的杂志,一只绿色大号玻璃烟灰缸放在一端,里面塞满烟蒂,还有带着些许血迹的棉球。要是让她来管理这地方,那只烟灰缸定会被经常清理。房间前侧的墙边没摆椅子,墙上镶着长方形护墙板,可以看到办公室里护士进进出出,秘书在听收音机。台子上摆着一只金色花盆,里面是塑料蕨类,枝叶几乎拖到地上。收音机里飘出轻柔的福音音乐。
“你要是喜欢垃圾,就给自己搞些垃圾呀,”她抱怨道,“你本可以把我造成垃圾的。或者黑鬼。如果你想要的是垃圾,为什么不把我造成垃圾?”她晃了晃攥着水管的拳头,一条水蛇登时出现在空中。“我可以不再工作,不努力,就那么脏兮兮的,”她嚷道,“整天在便道上晃悠,喝着根汁汽水,含着唇烟,朝每个小水坑吐唾沫,唾沫星子溅满脸。我可以很恶心的。
“或许小男孩儿可以挪一挪。”女士提出了建议,但孩子没动弹。
“你也可以把我造成黑鬼啊。我是成不了黑鬼了,太晚了,”她的语气里含着深深的嘲讽,“但我可以表现得像个黑鬼啊。在路中间一躺,阻断交通。在地上打滚儿。”
克劳德把裤腿放下。
暮色渐浓,一切都蒙上了神秘色彩。草场现出奇异的透明般的绿色,公路变成一带淡紫。她鼓足劲儿准备发起最后一击。这一次,她的声音滚遍了草场。“说去吧,”她喊道,“说我是猪!再叫我一声猪。从地狱来的。说我是地狱跑出来的疣猪。就算是底层栏杆翻到了顶,底还是底,顶还是顶!”
“天哪!”夫人说。
她听到了含混不清的回声。
“被母牛踢的。”特平太太说。
她胸中涌起最后一股怒潮,战栗着咆哮道:“你以为你是谁?”
“哎呀!”那位和善夫人问,“您是怎么弄的?”
一切之色彩,包括田野和火红的天空,都在那一刻燃烧起来,烧得透明而彻底。那个问题越过草场,穿过公路和棉花地,清晰地回到她这里,仿佛树林后面传来的答案。
克劳德把一只脚抬到放杂志的桌上,卷起裤腿,露出大理石般雪白的肥嘟嘟的小腿,腿肚上一片肿起的淤紫。
她张开嘴,却没有声音。
“坐下,”特平太太说,“你知道你的腿不好,不该站着。他的腿上有块溃疡。”她解释道。
一辆小卡车,克劳德的卡车,出现在公路上,迅速不见了踪影。齿轮发出尖细的摩擦声。看上去就像孩子的玩具,可能随时被大卡车碾压,克劳德和那些黑鬼的脑浆将迸裂四散在公路上。
克劳德抬头看了一眼,叹口气,想要起身。
特平太太站在那儿,目光紧盯着公路,全身肌肉紧张,直到五六分钟后,卡车重又出现,回来了。她等待着,等卡车转到他们的土路上。之后就像一尊获得了生命的雕像,她慢慢低下头看着猪栏里的猪。它们都挤在一个角落里,围着微微呼噜的老母猪。一道红光弥漫在猪群四周。它们喘息着,似乎有种隐秘的生命。
特平太太仍然站着。房间里,除了克劳德,只有一个男人。一个干巴瘦的老头儿,青筋暴露,双手僵硬地放在两膝上,闭着眼,仿佛在睡觉,或是死了,或是装睡装死,这样就不用起身给她让座了。她的目光亲和友善地落在了一位衣着考究、头发灰白的女士身上,四目相对,那女士的神情似在说:如果那是我的孩子,他会有礼貌地挪开——沙发足够大,您和他都能坐下。
特平太太就这样一直看着猪群,如在汲取某种来自深渊的,能赋予生命的知识,直到林线后的夕阳彻底沉没。终于,她抬起头。空中只剩一道紫云穿过一片绯红,如公路的延长线般,滑向垂垂暮色。她的双手离开围栏,伸向天空,如牧师般庄严肃穆。幻象之光落入她的眼中。她看见那道紫云仿佛一座宽阔的吊桥,从地上腾起,穿过燃烧的田野。桥上衮衮诸灵熙熙攘攘地走向天堂。他们当中有成群结队的白人垃圾,这辈子总算干净了一回,有一队队穿白袍的黑鬼,还有一列列怪人疯子,叫喊着鼓掌,青蛙似的跳来跳去。走在队尾的那群人,她立刻就认了出来,那是像她自己和克劳德这样的人,他们什么都有一些,上帝还给了他们才智以便正确使用财富。她探身向前想仔细观察他们。他们走在其他人的后面,尊贵而体面,像往常一样保持着良好秩序、常识以及受人尊敬的举止。只有他们走起路来有节奏。但是看到他们那震惊、扭曲的面容,她明白就连他们的美德也要被烧成灰了。她放下手,抓住猪栏木栅,眯着眼,一眨不眨地盯着前方。幻象迅即消失,她却仍站在那里,纹丝不动。
特平太太的手坚定地放在克劳德的肩上,毫不顾忌别人会听到她说的话:“克劳德,你去坐那把椅子。”说着便将他推向了空椅子。克劳德面色发红,秃顶,体格粗壮,比特平太太要矮一点。他坐在了椅子上,似已习惯听她吩咐。
终于,她下来了,关上水龙头,沿着越来越暗的小径朝房子慢慢走去。周围树林里,看不见的蟋蟀已开始合唱,她听到的却是灵魂们向着星辰之野出尘高蹈,口中呼喊着哈利路亚。
特平夫妇走进医生候诊室时几乎没有空座了。候诊室很小,特平太太又是个大块头,她的到来使候诊室显得越发局促。房间中央摆着一张放杂志的桌子,她魁然矗立在桌子一端,活生生地凸显出房间的逼仄与荒唐。她环顾四周,检视座位情况,小而亮的黑眼睛将所有病人尽收眼底。有一把椅子空着,沙发上还有个位置,一个约莫五六岁的金发小孩儿坐在那儿,穿着脏兮兮的蓝色连衣裤,该有人让他挪一挪,给女士让出座位。不过特平太太马上就明白没人会让他腾位置。他瘫坐在沙发上,胳膊耷拉在身体两侧,眼神空洞,拖着鼻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