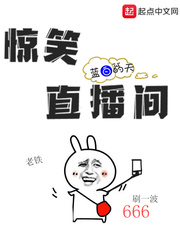章含之提示您:看后求收藏(350中文350zw.com),接着再看更方便。
我从北到南,又从南到北,追踪着冠华。我所到之处,他无处不在,可又处处不见。冠华永远在我心里啊!然而,毕竟是不在我眼前了,毕竟是永远不在我眼前,不在我身边了。
那天,我出门时尚未下雨,因而也未带雨具。一个多小时后就开始淅淅沥沥地下起了小雨。初冬的天气,细雨霏霏,又阴又冷,我拉上围巾,包住头挡挡雨,从南京西路拐进了石门路。为了躲雨,我从一个店铺走进另一个,过了几条横马路走进一家山货店。进门处有张大桌子,摆了许多陶瓷器皿,大概是残缺品和滞销品,减价出售。我随手拿起一个瓷杯,一时不知是做什么用的,大杯中还套个小碗,猛地想起,这是蒸人参用的参盅!一段回忆闪电般出现在眼前,这突然忆起的往事勾起我心头一阵无可名状的痛苦,我竟无法控制自己的感情,拿着这参盅出声地哭了起来。店里的人们奇怪,关切地围过来问我怎么回事。我放下参盅,跑出山货店,狂奔起来。雨越下越大,和着我的泪水往下流淌。跑不动了,可还在哭,还在走。几乎一口气跑到淮海中路,衣服全湿,我无力地靠在一个拐角处喘息……
我独自回到北京,走出机舱,外面是一片明亮的阳光。空气中还掺着一丝早春的寒意,更加感到清新舒畅。心情顿觉开朗。江南一周的雨折磨得我痛苦不已。如今见到遍地的阳光才又喘过气来。
7日上午到上海。刚下过雨,天空布满乌云,地上湿漉漉的。这年秋天,老天似乎与我同悲,冠华去世之后,北京本是金秋季节却接连下了好几场雨。我在上海的四个月也经常阴雨连绵,那是我一生中最难熬的日子。我怕孤独,可又最怕听人们那些安慰的话。没有任何话语能够慰藉我破碎的心。有时我痛苦得快发疯了,就跑到街上去漫游。上海的马路终年熙熙攘攘,人们带着采购商品的大包小包行色匆匆。也有悠闲漫步的,那必是一对对年轻情侣。而我大概是那年冬天上海大街小巷中的一个怪现象——一身黑衣,目光呆滞,无目的地在喧闹的人群中走着,走着,几个小时地走着。我只觉得我会这样地走到生命的尽头。有时我从南京西路一直可以走到外滩,伫立在黄浦江边,痴痴地望着那拍岸的江水。终于有一天,一家店铺里的一件小小的商品深深地触动了我内心的伤痛,促使我决定离开上海前往冠华的家乡——江苏盐城。
一小时后到家,刚拐进小院,一阵惊喜,真想不到今年的春天来得这样早!一周前离家时,院中还看不到绿色,如今却是满院春光。北屋书房前的梨树开满白色小花,它旁边的老海棠也点缀着无数朵粉色的花蕾,千姿百态,美极了。南边的丁香和另一株梨树都含苞欲放,三两天内这院子就将是花的世界了。惊喜之余,我最关心的却是在旁边小院极不起眼的角落里那另外的两棵树。我放下提包,赶紧去那里,看南屋房檐下的老梨树,它却仍是半边吐叶,半边毫无生气。我又去小跨院中,看我们卧室外的柿子树,不觉惊呆了!这棵当年冠华最心爱的也是最茂盛的柿子树,自他离去之后逐渐枯萎,而今年,它伸展到卧室的屋檐下的全部枝干竟都枯死了!那是冠华当年抚弄的枝干,那上面的柿子每年都由他亲手采摘。我望着这枯死的树干,刚进家门时的好心情变成了一片惆怅。这柿树对冠华如此多情,他走了,它也逐渐失去了生命。但我不知道这老柿树的一半枯死是对我有情呢,还是无情?每年我盼着它开花结果,又怕它开花结果。前年它开花时,我对着它又笑又哭,内心两种激情猛烈地撞击着。我想看见柿花,它们让我觉得冠华还在身边;我又怕看见柿花,冠华已经永远不能回来了。如今,他走后的第四个春天,柿花终于没有了。我连当年冠华抚摸过的枝叶也看不见了,它不再给我安慰,也不再给我悲哀,这是对我有情还是无情呢?
11月6日离家前,我一人反锁在卧室里,抚摸着冠华的骨灰盒与他告别。那天我离开北京,单位一个人都未来送我。去车站送我的是冠华的司机老张。老张挥手告别时泣不成声。其实老张给冠华只开了半年车,但冠华病危时多亏他帮助我,最后一天他在病房守了一夜。这是位普通的工人,但有着很不普通的真情实意。
午饭后,独自坐在院中。和煦的阳光下,思绪在回忆和现实中跳跃着。也许上午到家后情绪太激动了,此刻只觉得麻木。在我的大门前,文物单位在去年嵌上了一块石牌说明此房屋属四合院文物保护单位。我此时的感觉仿佛是我也变成了这个四合院内的一件文物。我经历了这院中的几度兴衰,如今当年的主人一个又一个地去了另一个世界:1970年是我母亲,1973年我的父亲行严先生在香港病故。此后冠华迁进来,1983年他又走了。留下的只剩下我一人,唯一的女儿也早在七年前远离家乡,定居在大洋彼岸了。
但是,这个家暂时是待不下去了。来吊唁的亲友们一走,整个院子就剩我一人。冠华走得仓促,家里每个角落都留着他的痕迹。书桌上未及放回书架的书还反扣着,椅子上他脱下的外衣似乎还存有他的体温。这一切在我精神已经高度紧张的情况下,如果剩我一人是足以使我最终丧失理智的。于是,万般无奈,我只好到上海暂住一段日子。
从中午到黄昏,我坐在院子里,温暖的春日阳光使我紧张了一周的神经和肢体都放松下来。坐在小藤椅里,时而微睡;时而又醒来。微睡时似乎见到的是过去的景象;醒来时又看到一院春色。然而不论怎样,思绪却总是离不开那两棵伴随了冠华十年,被他称为老朋友的树……
1983年10月25日,在凄风苦雨中,冠华的遗体告别在北京医院举行。由于种种始所未料的拖延,这已是他逝世后的一个月零三天。望着他那已略为失真的遗容,我真正地感到心碎了,碎得永远无法弥合。三天后,又是一个凄风苦雨的早晨,我从八宝山迎回了他的骨灰,放置在我们的卧室里。这一天,我只觉得恍恍惚惚,躯体在行走,灵魂却像是飘荡在一个空荡无际的深渊中,寻找着冠华的踪迹。书桌上一本胡适选注的《词选》还是不久前冠华翻阅时随手搁下的。我拿起来,翻开书角折起的一页,不知他为何折在这一页?那是韦庄的一首《女冠子》,折角处正是那几句:“不知魂已断,空有梦相随。除却天边月,没人知。”我再也支撑不住,趴在冠华昔日的书桌上,号啕痛哭,哭过之后又是呆呆的、空空的感觉。我这大半生总是好胜,但冠华离我而去之后却是我最懦弱的一段日子。就像这时,我又不禁拿起那一瓶安眠药发愣。如果它真能让我同冠华在永恒的冥冥中重聚并且永不分离,那该是多大的解脱和幸福!然而,我毕竟还有理智,我懂得它只能解脱痛苦却换不来重聚的幸福。我更懂得,冠华要我活下去,为他活下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