兰晓龙提示您:看后求收藏(350中文350zw.com),接着再看更方便。
割下来的部件被天外山的人包了一个油纸包,塞在其中一人的手上。
天外山帮徒:“他说了尘归尘土归土。”
那名陌生的红色人士接了,揣进怀里。他们四个人和那辆载着三名死者的骡车远去时,芦焱觉得分外孤独。
而教堂顶上的时光又一次提起了他的枪。
公路上已经看得见稀稀拉拉的车,破旧不堪,劣质燃油烧出的浓烟比得上黄土地带的扬尘。青山截住一辆马车,上车。
远远的,一辆黑色汽车跟上了青山乘坐的马车,一直跟着青山的两名骑手向汽车挥手示意,离去。
时光在教堂顶玩着枪。一个已经杀了两个人的家伙玩枪,总让下边所有人都觉得被瞄着,尽管他只是在装填子弹。
时光:“何思齐,你是命硬还是命贱哪?一个个都死了,你还在这里喝着风吸着气。”
该来的总归要来,芦焱抬头:“跟石头一样贱。”
时光:“刚拉走的三个死人,可有两个是你的旧识。你们平时背地里怎么称呼?同志?种子?”
芦焱:“一个叫骡子,臭得人都说他是骡子生的。一个叫古老板,卖着大沙锅最贵的水,可要当成酒的话又是最便宜的。”
时光:“鼋鸣鳖应,兔死狐悲?”
芦焱点点头:“我们都是一棵树的。他们都是我的同类。”
时光:“知道我为什么杀了他们吗?”
芦焱:“因为你有这个能耐。”
时光:“因为我肯定他们都是假的。你的命不硬,你也不贱,你还没死,只因为我还没搞明白你到底是个什么货色。不过昨晚上我在想高泊飞的道理,他觉得只要死了,就不是种子也是种子,我觉得只要死了,就算是真的也就成了假的,宁可错杀一千不可放走一个,讲的就是这个道理。干咱们这行好奇心太强不是好事,是不是?”
芦焱叹了口气,等着这早晚会来的一枪:“……老家伙,放自重点,别让我们白死啊。”
时光抬起枪,瞄准开枪,打死了芦焱身外三米之地的一个人。
时光:“好奇心太强不是好事,所以老子不想看你那股子沾沾自喜自以为逃过一劫的德行了。庄麻子,你跟明矾一起进的西北,凭什么我知道他就不知道你?”他又瞄了瞄芦焱,才把枪放下,“算你走运,我还真没搞清你是什么货色。如果你是种子,就赶紧求老天保佑你是真的。假货们砍头只当风吹帽是吧?可换句话说,也就是风吹过都能掉脑袋。”他敲着自己的脑袋想了想,“好像没什么事了?同胞们可以散了,走吧走吧,回家好好过,咱们共建这块乐土。”
人们在他的挥手之下沉默散去,刚散开一点,时光便一声大叫:“藤雄不二!我说走是说我的同胞!说你这个小日本了吗?”
人们愕然站住,并且发现一直只是持枪甚至背着枪的天外山举枪瞄准了人群,顿时一片悚然。
时光:“不二先生,你老兄自卢沟桥之变便混迹中原,屡遭奇险,连根毛都没有伤过。三天前带着两名手下来了两棵树,和高泊飞不和又搬进了欠记。我那两名手下死在你手上的吧?你现在就剩下一条命了,又该怎么还?”
人群鸦雀无声。
时光:“你觉得有意思吗?我是认不出你,可你太好那些奇淫巧技,为了化装方便干脆连眉毛也剃掉了。老子一个一个揪,揪到谁最像王八蛋,不就是你了吗?”
人群中的某一个忽然暴起,将身前的人拉过来挡住可能射来的枪弹。他是站在人群最后方的,房与房之间有一条通往镇外的缝隙,他企图通过这条缝隙逃出两棵树,一边将杂物抛向身后以阻挡可能的追赶者。其实,没人追他,也没人瞄准。
时光唾了一口:“跑得赛兔子他爹,敢情就这么个祥瑞御免。”
藤雄不二逃出镇子。这小子善于留后路,在人迹罕至的土围子外拴了一匹马。他上马便逃,似乎是大有活路。可刚一加速,就觉得马鞍松动,这才发现拴鞍的皮带都被割断了,不二连人带鞍摔了下来,然后他看见荒原上的两骑烟尘。一条套索很精准地将他连肩膀带胳膊套住,另一骑纵马过来,一枪托将他打翻。
天外山的人将不二拉回镇子,他的假发掉在地上,后边的监视者随手捞起。
芦焱看着被拖回来的不二破口大骂。那家伙的化装还真不是吹的,若不是时光说了,恐怕对着面他也认不出这是来刺杀青山的胡子。门闩迈步上前,对着他裆间就是一脚,又劈头盖脸的几拳,最后狠狠地卸断了他的胳膊。不二惨叫。
门闩伸手撕掉了不二一条眉毛:“果然是连眉毛都剃掉的。”
时光:“难怪这家伙出生入死却伤不着一根毫毛,人家出门时根本不带那玩意儿。拖他进去,瞧瞧他是不是真剃得那么干净。”
绝了念想的不二低头就去咬衣领。门闩一拳砸过去,随手把他的衣领撕了下来,从里边倒出一片氰化物,比芦焱的那片很可能过期的玩意儿卖相好得多。不二连呻吟的力气都没了,被横拖倒拽地进了教堂。
已经没人敢动了,看着时光百无聊赖地站着,谁也猜不出他还有什么花样。这回他的花样是洗脸,洗完了之后把脑袋在水里一通摆弄,然后把整盆水从楼顶上倒了下去。水逆着日光飞洒下来,很漂亮,但是每个人都沉默着。
时光:“最后一件事,你们是不是觉得我在造孽?这是水贵如油的大沙锅,方圆百里就这一口井,家里可以没锁,井盖子上却必须上锁,穷人家每月花在水上的钱跟花在吃上的钱一样多。但那是从前。”
他的手下拿着一把斧子向那口永远锁着的井走过去,几斧子下去,断链飞迸。
时光:“从今往后,只要两棵树还是我说了算,谁敢收水钱,我就在这儿就地把他做成干粮。收太平税,做成干粮。收风沙捐,做成干粮。太平是本来就该有的,至于风沙,好像你们收的捐越多,风沙就他妈的越大。”
他说这话时存心看着营盘里的驻军,那头苦着脸,噤若寒蝉。
时光:“都回去吧。下午这个破钟还会再响一次,用不着害怕,我让人运了车粮食过来,你们按人头均分了。可别总指着我发善心,我只帮你们接上这回青黄不接的茬,你们得好好地干活,再这样百业俱废可就怨不着乱世了——有我在的两棵树已经不是乱世了。”
人们愣着,祸福难知,心情复杂。
时光皱皱眉:“滚吧。”
人们散去。芦焱、小欠几个怔忡着想回欠记。
门闩:“你们留在这儿。”
他们几个便木然地戳着。芦焱听着来自教堂里的藤雄不二的惨叫,更多的时候是看着自己脚下移动的影子。时光终于下楼,在门闩的陪同下走进欠记。
青山从马车上下来,站在黄廓县街道上。从离开两棵树之后,巴东来的恶形恶状就一点点消失,到现在,巴东来其人已被他扔在两棵树了。青山活动着腰腿,摘了帽子,当扇子给自己扇着风,尽管阳光强烈,仍然没戴墨镜——他现在像足了一个归心似箭的老人,或者说他本来就是。不做巴东来的青山甚至去帮着同车的老人卸下糖人担子,反正除了一根手杖,他的行李全扔在两棵树了。
做糖人的以问候为谢意:“老爷不是本地人吗?”
青山便说本地话:“咋个不是?屁的老爷嘛。你老哥早出晚返,还趁副糖人挑子,我这出门在外的,混得就剩下这身行头了。灯芯草大老爷嘛。”
做糖人的:“走眼了走眼了,老哥哥原来是少小离家老大回呢。”
青山嗯嗯地应着,见缝插针的眼珠子却盯上了人家糖人担子:“哎呀,你这糖人是得过真传哪,是猴拉稀的手艺吧?”
做糖人的惊一下,喜一下:“对啦。我这不是吹的,不是塑的。这猴拉稀三个字可多少年没听人说出来啦。”
青山得意吹嘘:“那可不是,我是光绪五年就游弋中原的彩门哪。”
做糖人的:“那可是前辈加真人了。”
青山立刻鸡贼起来:“前辈加真人想买你个糖人,便宜些吧?”
那头也鸡贼起来:“这话说的,卖的是真手艺,每个价钱都不一样嘞——真想要当然便宜啦。”
青山掏钱。青山最后的钱放在鞋子里,不光是鞋子里,是鞋子里的鞋垫下,并且还不想掏出来。
青山:“拿旧东西换也行吧?”做糖人的点头,青山便拿出他的墨镜,“这个行吗?”
做糖人的:“这是老爷戴的。我这没家没业走南闯北的,戴这招打呢?”
青山:“这个,遮个风沙,挡个太阳,加个镜子,换你的老猴吃桃和和合二仙。”
这回他拿出来的是自己的帽子,老头摇头不迭。
做糖人的:“那哪行呢?你这帽子也旧了——你不晓得现在糖卖什么价吗?你也吃不完嘛。”
青山就是那么热切而温和地看着,教老头子坐立不安也说不下去。
青山:“这么好的东西哪舍得吃嘞?我拿回家的。”
做糖人的:“吃不了就化了。浪费的。”
青山:“给孙子的,不浪费的——我也不要了。坐一会吧?”
那老头也舍不得弃了这笔生意:“坐一会儿,坐一会儿,天太热了。”
俩老头各自心怀鬼胎,互相偷眼打量。
青山直哼哼:“给孙子的呀,给孙子的。”
这样的哼哼让他的每一个毛孔里都洋溢着幸福,让偷眼瞧他的老头不吭声,却又妒忌到眼红。
从天外山禁动现场之后,欠记屋里就再没人敢碰过,五具尸体仍然留在那一片狼藉的昨日战场。时光、门闩和几个手下里里外外地检查着那些尸体,他们现在与其说是马匪不如说是法医。
门闩指点:“老兵死在高泊飞的机枪下,子弹无眼,只能多加抚恤。骑河车留守后院,窝心马留守外堂。藤雄不二已经供认是他那俩手下杀的,我这下令留守的就难辞其咎了。”
时光:“昨晚黄沙会的俘虏才供出藤雄的消息,你又不能未卜先知。就带了十个人对阵高泊飞六十多人,还要分出两个看守这里,咎你妈的个头啊?”
门闩苦笑:“谢谢。”
时光:“过度无私,也许就是无处不私。存点小心。”
门闩:“是。”
时光不再研究自己人的尸骸,他走向被芦焱扎死的藤雄手下:“就藤雄那凡事撒腿再说的德行,杀了后院的就可以跑了,干吗还来前边杀人?”
门闩:“据欠老板说是要杀那位巴东来阁下。至于为什么要杀,藤雄熬刑的本事跟撒腿有一拼,平均割两斤肉才能挤出一句话。”
时光笑:“好在他总有一百三四十斤。”他拔了拔那家伙身上插的铁钎,“这位还真是死不瞑目。”
门闩:“恐怕到阎罗王那里有得官司打。万里迢迢跑到这里,杀了个六十多岁的老头,却被个瘦到能被老婆打的教书匠穿成了葫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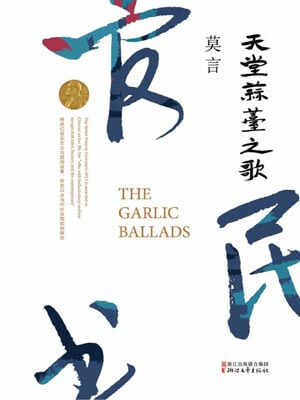
![[网王]邂逅](https://image.51jpg.com/597/597961/597961s.jpg)