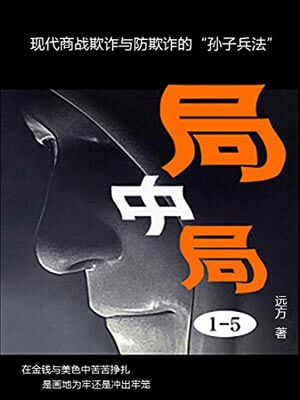斯蒂芬·金提示您:看后求收藏(350中文350zw.com),接着再看更方便。
我坐下来,吃了一个桌语派,先前还一心期待,现在却味如嚼蜡,一边随手翻阅那本昂贵的印刷图册,一边在心里说——我百分百肯定这话不是原创——达利,嘿,问您好。那些画不是张张都能触动我。看画的时候,我时常觉得那是个有天赋的机灵鬼,画却比闲来无事的涂鸦好不了多少。不过,有几张让我精神一振,还有一两张则像我笔下那蜃景般的海螺贝一样令人不寒而栗。老虎飘浮在斜躺的裸体女人之上。一朵飘浮的玫瑰。还有那幅《天鹅倒影成大象》怪得出奇,我几乎不敢正眼瞧……便翻过几页看别的画。
实际上,我是在等即将成为前妻的妻子给我打电话,等她邀请我回圣保罗和女儿们一起欢度圣诞。最后,电话铃响了,当她说这番邀请不算太明智,违背我的初衷时,我遏制住全力反击、破口大吼我也要违背初衷地接受邀请的冲动,让自己说出口的是我理解。然后是圣诞节怎样?当她说很好的时候,言语中已听不到掩护完毕、亟待出击的那个她。我们的对话本来可能将全家欢度圣诞的计划扼杀于萌芽,但现在态势已转。但回家过节似乎也不是个好主意。
挖到底,卡曼在信里不止说过,还用了粗体字强调。我猜想,要是现在走,恐怕没法把收获挖到底,而是索性夭折。我可以再回杜马岛……但未必能回到最佳状态。散步,画画,彼此滋养。我不知道那究竟是怎样的过程,也不需要知道。
但是伊瑟说了呀:要答应,为了我。她知道我会应允,倒不是因为她是我的最爱(我猜想,琳也知道这一点),而是因为她历来知足常乐,很少要求什么。也因为我听着她的留言时,想起了她和梅琳达来法伦湖畔看我时眼泪汪汪的模样,她哭起来的时候靠在我身上,她问事情为什么会走到这地步,为什么不能像往昔那样。因为万事万物都无法照旧如常,我想我回答了,也可能是过了好几天……或夹在某份传真件的段落里。伊瑟十九岁,已经过了享有最后一个童年圣诞的年龄,但再过一个全家团聚的圣诞节却永远也不嫌老。而且,那也是为了琳。她的生存技巧要高明一点,但她又飞去法国了,独自在异乡,如今的我也能感同身受。
好吧,那就定了。我会回去,会好好表现,而且必会把瑞芭也收在行李里,以防怒火再次突袭。愤怒减弱了,但显而易见的是,在杜马岛除了我自己的间歇性遗忘症和该死的跛足,真的再没什么能激怒我了。我给租机公司打电话,十五年来我一直是他们的忠实用户,定好了一架利尔喷气机,十二月二十四日早上九点整从萨拉索塔直飞明尼阿波利斯圣保罗国际机场。我也给杰克打了电话,他说很乐意载我去海豚航站楼,并在二十八日再去接我回来。可就当我把一切安排妥当之后,帕姆来电,通知我圣诞计划全部取消。
6
帕姆的父亲是海军退役军官。他和妻子在二十世纪的最后一年移居加利福尼亚的棕榈滩,住在一个安保严格的封闭小区,那儿还住着一对假模假式的非裔美国夫妇和四对同样假模假式的犹太夫妇。谢绝孩童和素食者。居住者必须投票给共和党人,豢养的小型犬瞪着愚不可及的狗眼,必须戴水晶项圈,宠物昵称必以“妮”或“尼”结尾。塔夫妮就不错,卡希妮就更棒,但瑞菲尼就是彻头彻尾的烂名字。经诊断,帕姆的父亲罹患了直肠癌。我倒一点儿不觉惊讶。把一群浑蛋白种人聚在一处,你准能发现癌症四溢。
这些话我自然没对妻子说,一开始她表现得很坚强,说着说着便泣不成声。“他开始化疗了,可妈妈说癌细胞可能已经转……扩……哦,该死的到底该怎么说啊,我怎么和你一样了!”依然抽泣着的她好像被脱口而出的这句话吓坏了,便又谦卑地说,“我很抱歉,埃迪,我真不该那么说,太恶毒了。”
“没关系的,别在意。”我说,“一点都不恶毒。该说是,癌细胞扩散了。”
“是的,谢谢你。不管怎样,他们打算今晚动手术取出最大的肿瘤。”她又开始哭了,“我真不敢相信我父亲会碰到这种事。”
“放松点,”我说,“当今的医疗科技能创造奇迹。我就是最佳范例。”
她不认为我是个奇迹典范,要不就是不想提我的事儿,总之她只是说:“不管怎样,这儿的圣诞计划取消了。”
“那当然。”可真相是什么?我很高兴。太他妈高兴了。
“我明天就飞棕榈滩。伊瑟星期五过来,梅琳达要到二十号。我想……考虑到你和我父亲一直都合不来……”
当岳父大人恶言攻击民主党人时,我俩差点儿大打出手扭作一团,考虑到这一点,我认为帕姆说得非常含蓄。我赶紧答话:“你觉得我不想跟你和女儿们一起在棕榈滩过圣诞节吧,你说对了。我会在经济上助你一臂之力,希望你们几个能理解我和那个……”
“我简直不敢相信,都到这时候了,你竟然要把该死的支票簿拽出来!”
愤怒重现,就是那么突如其来。臭烘烘的小盒子里突然蹿出丑怪杰克。我很想说大嘴八婆你干吗不去死。可我没说。部分原因是我不能肯定脱口而出的是大嘴婊婆还是八嘴婊子。无论如何,我知道自己说不利索。
不过,差一点就冲出口了。
“埃迪?”她真是咄咄逼人,只要我稍微配合一下,她就能暴跳如雷正式宣战。
“我没打算拽出支票簿搅和什么事,”我说,小心翼翼地聆听出口的每个字。它们各就各位,完全正确。真让人如释重负。“我只是说,我在你父亲的病榻旁露面不太会有助于他的康复。”顷刻间,愤怒——暴怒——高涨到了让我盲目的地步。我再一次成功地遏止言语冲撞,但此刻的我已大汗淋漓。
“好。我明白了。”她停了停,“埃迪,那你圣诞节打算怎么办?”
画夕阳,我心想,说不定能画对路子呢。
“要是我还是个帅小伙,我相信杰克·坎托里和他家里人会邀请我去吃圣诞大餐。”说得好听,其实我压根儿不相信。“杰克是这儿帮我打杂跑腿的小伙子。”
“你听上去好多了。有劲儿了。你的忘性儿还是那么大吗?”
“不知道,我记不得了。”我说。
“别开玩笑了。”
“笑声才是灵丹妙药。我在《读者文摘》里读到过的。”
“你的胳膊怎样了?还有幻存感吗?”
“没有了。”我撒谎,“基本上已经消停了。”
“好。好极了。”停顿,接着又说,“埃迪?”
“在听呢。”此时,我的掌心里有深红色的半月痕,那是死死握拳的结果。
这次的停顿很长。我小时候,电话线路会有呲啦呲啦的杂音,现在已经听不到了,但我听得到我俩之间隔着千山万水的轻叹。就像海湾退潮时的声音。随后,她说道:“我很抱歉,事情到了这一步。”
“深有同感。”我说,等她挂了电话,我捡起最大的一枚贝壳,几乎难以自控地想要砸向电视机屏幕。但我没有,而是蹒跚着走过起居室,打开房门,把它扔向荒芜的小路。我不恨帕姆——不是真的恨——但我似乎仍在痛恨什么。或许是上辈子。
或许只是恨我自己。
7
ifsogirl88致 EFree19
12月23日 9:05am
亲爱的爸爸,医生没透露太多,但我对外公的手术不太乐观。当然现在表现坚强的也许只有妈妈,她每天都带着外婆去看外公,使劲地要“积极乐观”,但你知道她的,不是那种相信黑暗中总有一线生机的人。我想过去看你。我查了航班,可以在二十六号飞到萨拉索塔。会在你那里的下午六点十五分到达。我可以待两三天。求你了,同意吧!我还能亲手把礼物给你,不用邮寄了。爱你……
伊瑟
又及:我有特别新闻号外要告诉你。
我有没有三思,或起码考虑一下直觉里的蛛丝马迹?我记不清了。或许都没有去想。或许要紧的只有一点:我想见到她。于是,我几乎立刻回复了她。
EFree19致 ifsogirl88
12月23日 9:17am
伊瑟:来吧!把行程定下来,我会和杰克坎托里去接你,他碰巧就是我的圣诞老爷爷。我希望你会喜欢我的住所,我叫它“浓粉屋”。但有一点:如果你妈妈不知道,或是不同意,你就不能擅自过来。你知道,我们熬过了一段艰辛时光。我只愿那些不堪回首的日子已成过去。我相信你明白我的意思。
爸
她的回复也是眨眼间就到了。她准是在电脑前等。
ifsogirl88致 EFree19
12月23日 9:23am
已经和妈交代清楚啦,她说可以的。
也想说动琳来着,但她更想在飞回法国前待在这里。这事儿,你别怪她。
伊瑟
又及:太好咯!我兴奋死了呢!:)
别怪她。似乎我的“如果如此女孩”自从会说话起就一直这么说她姐姐。琳不想去烤肉店因为她不喜欢吃热狗……但你别怪她。琳不能穿那种运动鞋因为她班上的同学都不再穿高帮鞋了……所以别怪她啦。琳想要瑞安的爸爸送她们去舞会……但你别怪她。可你知道糟糕在哪里吗?我从来就没怨她。我可以跟琳说,偏爱伊瑟就像左撇子偏爱左手——全都是我无法控制的事,但那只会让事情变得更糟,哪怕是大实话。或许就因为是实话,才更糟。
8
伊瑟要来杜马岛、来浓粉屋啦!太好了,她兴奋死了,其实我也兴奋死了。杰克帮我找了个粗壮的女士每周两次帮我清扫房舍,她叫胡安妮塔。我吩咐她把客房收拾好,还问她能否在圣诞节过后的那天带点鲜花来。她笑眯眯地提议说,可以带点“奶油蛋糕”。现在,我的大脑已非常擅长在词汇方面作发散性的跳跃联想,听她这么说,我只花了不到五秒就琢磨出来了。于是,我对胡安妮塔说,伊瑟肯定会喜欢圣诞仙人掌的。
圣诞夜里,我发现自己把伊瑟的电邮反复重读。太阳西沉,在海面投下一柱绵长而明晃晃的光芒,但起码还有两小时才会日落,而我坐在佛罗里达屋里。潮位很高。就在我的脚下,深浪里的贝壳洄转摩擦,擦出酷似浅浅呼吸乃至密谈般的嘶嘶声。我用大拇指点着附注里的那句话——我有特别新闻号外要告诉你,而右臂——那条不存在的胳膊,痒起来了。我几乎能明白无误、毫厘不差地指出瘙痒的位置。自肘窝处开始,打着旋儿直痒到手腕外侧。越来越痒,痒到我忍不住想用左手狠狠挠一番了。
我闭起双眼,用右手的大拇指蹭响食指。没有声音,但我可以感觉得到,我打了个响指。又用右臂蹭了蹭体侧,也能感觉得到那种摩擦。尽管右手早已在圣保罗医院的焚化炉里烧光了,我仍把手掌压低,抚在椅子的扶手上,用指尖去叩击。没有声音,但感觉却在:指尖皮肤轻触柳条。我敢以上帝的名义对天发誓。
突然之间,我只想画画。
我想要上二楼的大房间,但小粉红此刻显得太远了。我走进起居室,咖啡桌上摆了一摞“手艺人”,我便抓起一本。大部分画具用品都在楼上,但还有几盒彩色铅笔收在起居室书桌的抽屉里,我也过去拿了一盒。
回到佛罗里达屋(我总觉得那儿就是门廊),我坐下来,闭上眼。听着海浪在我身下按部就班,托起贝壳,再将它们摆放成一种新图案,一次又一次,绝无雷同。闭起眼睛时,磋磨声听来就更像密谈:海水在陆地的边缘开合转瞬即逝的唇齿。陆地自身也是转瞬即逝的,如果从地理学的立场放眼四周,你便会相信,杜马不会长存。这些岛屿没一座能长存;到最后,湾流会将它们全部吞没,新的岛屿会在新的位置浮升而起。佛罗里达的真相或许就是这样。陆地很低,而且,是从海里借来的。
啊!但那声响真让人宁静安详啊。催眠一般。
依然闭着眼睛,我去摸索伊瑟的电邮,指尖触了上去。我用的是右手。接着睁开眼睛,用存在的那只手把电邮打印纸撸到一边去,再把素描本放在膝头。翻过封面,把盒里的十二支已削尖的维纳斯牌彩色铅笔全都抖出来,散在我面前的桌上,然后就画起来。我觉得自己是要画伊瑟——毕竟是我日思夜想的人,不是吗?——然后预感一定会搞砸,因为重操画笔后我连个人影都没画过。结果,我画出来的不是伊瑟,但画得却不坏。或许称不上杰作,不是伦勃朗(就连诺曼·洛克威尔也算不上),但确实不赖。
那是个年轻男子,穿着牛仔裤和明尼苏达双胞胎棒球队的T恤。球衣上的号码是48,对我而言,这数字形同虚设;在我过去的那段生活里,我总是尽可能抽出时间去看狼人队的比赛,但我从来算不上是铁杆粉丝。我也没有颜色适合的铅笔精准地画出深得几近棕色的金发。他的一只手里夹着一本书。他在微笑。我知道他在笑。他就是伊瑟的特大新闻。那就是海贝在潮涌托浮、潮退落沙时说的话。订婚,订婚。她有了一枚戒指,钻石的,他买戒指的地点是——
我在用维纳斯蓝色笔涂画他的牛仔裤。现在我把蓝笔甩掉,抓起黑笔,在画纸的最下方写下
赞莉斯
这是条讯息,也是这幅画的名字。命名可以增添力量。
接着,一秒都没耽搁,我又放下黑笔,捡起橙色,添上了一双工作靴。橙色太鲜亮了,好像鞋子崭新时的模样,其实那双鞋早已穿旧,但橙色无疑是正确的。
我抓了抓右臂,穿过右臂,抓到了肋骨上。我含糊地轻骂了句“妈的”。在我身下,贝壳似乎磋磨出了一个名字。康纳?不。这儿有什么不对劲。我不知道这种不对劲的念头打哪儿来,但右臂的瘙痒突如其来变成了一种冰凉的疼痛。
我把这页翻过去,又开始描,这一次只用红笔。红色,红色,那是<b>红色的</b>!笔下如有神助,飞快地勾勒出一个人形,活像刀口下流出鲜血。那是个背影,那人穿着一面红色斗篷,似乎是扇形圆领。我把头发也画成红色,因为那看来像血,而这个人的感觉就像鲜血。像危险。不是对我来的,而是——
“伊瑟,”我喃喃自语道,“是冲伊瑟去的危险。是这个家伙吗?号外新闻男主角?”
男主角身上有什么不对劲,但我不觉得那是让我毛骨悚然的原因。有一点,穿红袍的人不太像男人。很难说准,但没错——我觉得……是个女人。所以,或许根本不是什么斗篷长袍,而是裙子?一条长长的红裙?
我把第一张画翻回来,看着新闻男主角手里的书。我把红铅笔扔在地板上,再把书涂成了黑色。然后我又盯着他看,突然以手写花体在他上方写下
蜂鸟
我把黑笔扔到地上,抬起颤抖的双手,捂住了自己的脸孔。我大声喊出女儿的名字,当你看到有人逼近悬崖或在车水马龙间穿行时才会那样喊。
大概我疯了吧。很可能我已经疯了。
最后,我意识到——那当然了——只有一只手覆在双眼上。幻存的疼痛和奇痒消失了。我要疯了的念头——天啊,我可能已经疯了——却萦绕不去。只有一点是毋庸置疑的:我饿了。饿疯了。
9
伊瑟的航班比预订的时间早到了十分钟。她穿着褪色的牛仔裤和布朗大学的T恤,显得容光焕发,我不明白杰克怎么没在二号航站楼就当场爱上她。她扑到我的怀里,吻遍我的脸,然后开心地大笑,当我撑在拐杖上东倒西歪时又抓牢我。我把她介绍给杰克,假装没看到他俩握手时,小钻石(在赞莉斯买的,我毫不怀疑)在她的左手无名指上闪亮。
“你看上去好极了,爹地。”我们走出航站楼,迈入温暖芳香的十二月的夜色里,她说,“你都晒黑了。上一次还是在莉丽黛儿公园,你们在那儿造娱乐中心。而且你也胖了啊,起码长了十磅。你不觉得吗,杰克?”
“你才是最佳裁判员,”杰克露出微笑,说道,“我去取车。你站久了没事儿吧,老板?要等上一会儿。”
“我没事儿。”
我们站在路边等候,还有她的两个随身包和手提电脑。她笑着,深深凝视我。
“你看到了,是吧?”她问,“别假装没注意到。”
“如果说的是戒指,我是看到了。如果不是参加那种电子游戏大赛得的大奖,那我就该给你道喜了。琳知道吗?”
“知道啦。”
“你妈呢?”
“你觉得呢,爹地?好好猜猜。”
“我猜是……没有。因为她现在一门心思都在外公身上。”
“外公不是唯一的理由,我在加利福尼亚的时候一直把戒指藏在手袋里——只给琳看过,就那么一次。其实,主要是因为我想先让你知道。是不是很阴险?”
“不,甜心,我感动死了。”
我确实是。但我还很担心她,不仅因为她再过三个月才满二十岁。
“他叫卡森·琼斯,是神学院的学生,简而言之——你能相信吗?我爱他,爹地,我就是太爱他了。”
“好极了,甜心。”我应声,但可以感觉到恐惧顺着双腿蹑足而上。别太爱他了,我心里说,千万别爱过头,因为——
她正凑近了看我,笑容正在褪去,“怎么了?出什么事儿了?”
我都忘了她的反应有多快,她又是多么了解我。爱能制造心灵感应,可不是吗?
“没什么,宝贝。呃……屁股有点疼罢了。”
“你吃止痛药了吗?”
“其实……我现在加大了散步的量。计划在一月份彻底甩掉手杖。这就是我的新年计划。”
“爹地,那可太棒了!”
“不过,新年计划都是实现不了的。”
“你的计划就不会。你说了要做什么,就一定做得到。”伊瑟皱起眉头,“在这一点上,妈妈从来不喜欢你。我认为这会让她嫉妒。”
“宝贝,离婚已成事实。别再偏袒任何一方了,好吗?”
“好吧,我跟你说点别的事,既成事实的事。”伊瑟说着,嘴唇抿紧了,“自打她到了棕榈滩,已经出去无数次,只为了见那个家伙。她说只不过喝杯咖啡,互相安慰一下——因为马科斯的父亲去年去世了,而马科斯真的很喜欢外公,诸如此类一大堆理由——但我明明看到她用那种眼神瞅着他,我……我真不喜欢!”现在,她的双唇瘪得都快看不到了,我觉得她看起来真像她母亲,像得可怕。随之而来的想法也很怪,却能安慰我心:我觉得她会好好的。即便这位神圣的琼斯抛弃她,我相信她也会好好的。
我已经能看到我租的那辆车了,但杰克把车开过来还得有一会儿。接客处的车无不是停停走走。我把拐杖的上端靠在腰间,腾出手来抱了抱我的小女儿,她大老远从加利福尼亚跑来看我呢。“别对你妈妈太苛刻,行不?”
“你难道就不关——”
“这些天来,我最关心的就是你还有梅琳达,你们是不是快乐。”
她的眼睛下面有黑眼圈,我看得出来,不管年轻与否,长途旅行已把她累着了。我想,明天她会睡个大懒觉,那很好。如果我对她的男朋友的感觉正确——我希望不是那样,但又认定是——随后的一年里她还会有很多不眠之夜要熬呢。
杰克已经开到佛罗里达机场的航站楼入口了,也就是说,我们还有点时间。“你带了男友的照片吗?好打听的老爸想看一眼。”
伊瑟的脸一下子亮堂起来,“那还用说。”从她红色的皮钱包里抽出的照片收在透明的塑胶套里。她把封套一掀,把照片递给我。我估计,这一次我没有流露出内心所想,因为她那满心欢喜的笑容(真的有点像傻笑)一丝没改。我呢?如鲠在喉,又好像吞下了一梭子铅弹,总之是人类的喉咙应付不了的家伙。
倒不是说卡森·琼斯让我想起了圣诞前夜的画。这一点,我早有心理准备,尤其是看到伊瑟手指上晶晶闪亮的小玩意儿之后。令我震惊的是那张画与这张照片简直就像彼此的复制品。就像我把槐米、匙叶草或冬青树的照片夹在画架背后那样,好像我也临摹过这张照片似的。无论是他身上的牛仔裤,还是脚下的旧靴子,都像得不能再像了;偏深的金发乱蓬蓬地支棱在双耳后边、覆盖了前额;手里还有一本书,而我已经知道那准是本《圣经》。最切中要害的一点便是明尼苏达双胞胎队的球衣,左胸口分明写着号码:48。
“谁是48号?你怎么碰巧在布朗大学认识了一个双胞胎队的球迷?我以为那儿都是红袜队的球迷。”
“48号是托瑞·亨特,”她答,瞧着我的眼神仿佛在说,你是天字第一号傻瓜吗?“学生休息大厅里有一台超大的电视机,七月赛季里红袜和双胞胎对垒时,我也去大厅里看比赛,那地方人多得挤死人,才是夏季赛事就那样!不过卡森和我是唯一穿上双胞胎队衣的粉丝——他穿着托瑞的T恤,我戴着队帽。所以啦,我们就坐到一块儿,然后嘛……”她一耸肩,后面的故事尽在不言中。
“他的爱给了谁,就宗教而言?”
“浸信会。”她有点挑衅地看着我,好像她刚刚说的是食人族。我自己什么信徒也不是,虽然身在“无信教堂”的首席位置,但我对浸信会教友并无芥蒂。我不中意的信仰只有一种:声称自己的上帝比你信仰的神更神通广大。“这四个月来,我们都一起去教堂,每周三次。”
杰克把车停好了,伊瑟弯腰抓起包袋拎手。“他打算在春季学年休学,加入一次正宗的福音团之旅。这次巡游很地道,福音书啦什么的一应俱全。这个团叫作‘蜂鸟’。你真该听他唱福音歌——简直像个天使。”
“那还用说。”我说。
她又亲了我一下,轻轻地吻在脸颊,“我能来这儿真是太高兴了,爹地。你高兴吗?”
“高兴得你都无法想象。”说着,我发现自己已在心里许愿:让她疯狂地爱上杰克吧!那样,一切麻烦都会自动消解……至少能将我心中的困扰一扫而空。
10
我们没办法吃一顿豪华的圣诞大餐,只有一道杰克买来的太空鸡,再加蔓越莓浇汁,配袋装沙拉和米布丁。伊瑟每一道都吃了双份。我们交换了圣诞礼物,并对彼此赞叹一番——每个人都得到了最想要的!——我带伊瑟上楼看看小粉红,并把我的大部分艺术功课都展示给她看。但我画的她男友和那个红裙女人(如果是女人的话)则被束之高阁,藏在我卧室的壁橱顶上,它们得一直在那儿,待到我女儿离开为止。
我把十几幅画——大都是夕照海景——裱在纸版画框里,沿墙脚一字排开。她看了一圈,停下脚步,然后又看了一圈。那时已是夜里,我的超大观景玻璃窗外一片漆黑。海潮正在退远;你只能从持续不断的叹息声中得知海湾就在脚下,海涛就在这里滚滚缓冲沙岸,退去时悄无声息。
“真的都是你画的吗?”终于看完,她问,转身看我,看得我浑身不自在。只有当你严肃地重新评估某人时,才会有那种眼神。
“真的都是我画的。”我说,“你觉得如何?”
“很好啊。或许该说,不只是很好。这张——”她弯下腰,非常慎重地捡起那张橘黄色夕阳笼罩海螺贝、压在海平线的画作。“这张真他妈……对不起,非常诡异。”
“我也有同感。”我说,“但说真的,这也没什么新鲜的,只不过有点超现实主义,把夕阳伪装了一下。”接着,我又万分愚蠢地加以附注:“哈啰,达利!”
她把《海螺贝的夕阳》放回去,又拿起《槐米的夕阳》。
“有谁看过这些画吗?”
“只有你和杰克,还有胡安妮塔。用她的口音来说,这些都是泥塑饼。还有些诸如此类的话。杰克说,那就是说它们怪吓人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