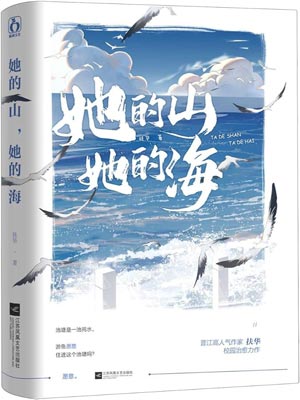曾根圭介提示您:看后求收藏(350中文350zw.com),接着再看更方便。
“不好意思,我既没有炸弹的知识,也不会使用手枪。”
“我们才不是要拜托你这种事。”
“那要我做什么?”
“我们想请你动手术。”
“手术?”
“当然就是变脸手术啊。”
“这样不就跟你们的主张互相矛盾了吗?你们不是强调我们跟你们是平等的吗?”
“是这样没错,你们跟我们的不同之处只在于外观上的差异,除此之外没有任何差别。”
“既然如此,为何还要动手术?”
“这次连东京都增设了特别区,也修订了法律,以协助我们自立生活的名义,将我们收留在那个地方,而且是强制性的。”
“强制性?”我第一次听说,“可是比起穷困的贫民窟,那里比较好吧。”
“前提是如果特别区真如政府当局所说是梦想共同体吧。”
“意思是为了不让你们在那个特别区被杀掉,才要我动手术吗?”
“你似乎不相信我说的话,但这是事实啊。政府里面也有人认同我们的思想,所以透露情报给我们。政府当局如果派出特务队或警察开始逮人,光靠我们的组织是无法守护那些人的。因此,为了率先保护孩子们的安全,虽然是情非得已,但手术是最有效的手段。”
“我想回去了,我帮不上你们的忙。”我对日比野说。
我并不感到害怕,因为日比野的眼神跟那些为达到目的不择手段的人不一样。
“那可不行,你──”
日比野以手示意,制止女人讲下去。
“医生,说谎骗你,还把你带来这种地方,我很抱歉。喂,就让他回去吧。”
“可是,日比野先生──”凤眼女似乎不同意,但一对上日比野的眼睛便把话吞了下去。
“医生,若改变心意请跟我联络。如果你愿意动手术,有很多人的性命会因你而得救。”日比野咳了几声便走出了房间。
之后我的眼睛又被蒙起来,坐上车行驶一段路后,他们在诊所附近放我下车。
口罩男的家。叮咚,叮咚。
婆婆从主房登场。
“他不在啦,我不知道他去哪里,不是叫你别再来了吗?”
让老子见一见口罩男吧。
“不准给我守在门外。如果无论如何都要见我儿子就带搜查令来,我也会请好律师的。”
掐死你啊,请什么律师嘛。
“别再来了。”
才不要。老子明天还会过来。
老子无论如何都要见口罩男。
一连好几天都被婆婆赶出去,老子也很着急,着急得不得了。
“大叔。”女高中生走过来,拿了本女性杂志在老子面前甩了甩。
在干什么啊?
“大叔,是你吧,你看看这个。”她又甩了甩女性杂志。
“这本周刊杂志,周刊头条,灰色套装,写信约我的是大叔吧?”
约炮的。堕落的青少年。
不是老子约的,吵死了。老子冷冷地说。
女高中生抽抽鼻子,脸一皱,“搞什么啊。”
是犬女。
其实写信约你的就是大叔。态度突然一转的老子。
“果然。”穿短裙化浓妆的女高中生说,“马上走吗?我没多少时间了。”
老子不发一语跟着她。
女高中生一进到旅馆里就开始脱衣服。
“先付头期款吧。”
手伸出来要钱的女高中生。
老子每次一说话,脸就皱起来的女高中生。
她果然是个犬女。
老子嘴巴很臭吗?喂,说清楚讲明白!
老子随身带着牙刷,也带着口腔清洁口香糖和漱口水,口腔喷雾剂也每一小时喷一次。
这样老子的嘴巴还是很臭吗?
下个瞬间,老子的拳头不知怎的就往犬女高中生揍下去,犬女高中生的脸歪掉。
老子一把抓住她的咖啡色头发,把犬女高中生拎起来。
再给鼻子一拳,鼻子被打扁了。
这样就不臭了吧。
老子坐下来点着香烟。犬女高中生在地上熟睡。
用香烟烫那张脸以示惩罚。刺鼻的恶臭飘荡整个房间。
没关系,只有老子闻得到。
夜晚的搜查会议结束。
课长吊着眉叫我过去。
“你在干什么啊?”课长很生气。
“署里接到投诉了,对方是个很麻烦的老女人。她投诉说有个刑警每天都在她家附近徘徊,那个人是你吧?”
是那个强势的婆婆。给老子记住。
“听说你一直缠着说要见那家的儿子,你究竟在搞什么鬼?”
老子想见那个口罩男,无论如何都要见到他。
“搜查?别开玩笑了。为什么每天在家睡大觉的儿子会是这个事件的嫌疑犯?”
睡大觉?胡说八道的强势婆婆。口罩男明明会在深夜时在住家附近到处游荡。
但老子仍向课长道歉。老子鞠躬哈腰,露出卑微的笑容。
课长用轻视的眼神看我。
“你从明天起不用来搜查本部了。”
坐在眼前的青年露出促狭的笑容,那嘴角感觉的确很熟悉,但就算听到青年的名字叫作正树,记忆中的那层薄雾也没有立刻散去。
最后将这层雾吹散的那阵风,是他和我说话时的眼神。他的眼睛时不时飘来飘去,简直像是先来探路的犯罪者的眼神,这一点跟小时候完全一样。
正树比我的女儿里香稍长三四岁,小时候住在家附近。当时仍是“我们”跟“他们”没有任何芥蒂地生活在一起的时代。
正树常和其他几个孩子来家里玩,当时发现他回去后家里一定会有东西不见了,但我以为是小孩子的恶作剧,也就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可是长大后正树的行为却越来越恶劣,逐渐成为附近的问题人物而遭到大人们的冷眼相待。
里香死亡之后也没机会跟他直接见面,所以完全不知道正树在这附近住到了何时。
“你长大了呢。”虽然纳闷正树的来意,但我脸上仍堆着笑容。
“对啊,医生也完全没变呢。”
他长得比我高了。他像在物色东西,滴水不漏地扫视着房间的视线却跟孩童时期一样。
正树一直没有切入正题,于是由我先开口。
“你为什么今天要来找我?”
正树没有回答,只是咧着嘴笑。
“找我有事吗?”
“嗯,前一阵子我见到里香了。”
“什么?”
“真令人怀念呢。”
“不可能有这种事。”
“为什么?真的是里香,我不会弄错的。”正树嘴角挂着笑意,观察我的反应。
“里香已经死了。”
“那我见到的是鬼魂吗?”
“有可能只是长得像她的人吧。”
“我可不这么认为。医生,方便的话我想喝个酒什么的。”
我从橱柜里拿出威士忌和酒杯,放在正树前面。
“‘森泽里香’是里香现在的名字。”
“……”
“医生,请您跟我说实话。”
“给人家做养女了。妻子过世,我也生病了。这种状况下,单靠男人是没办法养孩子的。”
“哎。”正树的声音听起来不以为意。
“……”
“还有一件不可思议的事。”
我的额头上冒出汗。
“里香应该和我一样是天狗,可是为什么前一阵子见到的里香却变成了猪呢?我记得里香的妈妈应该也是天狗,伯母很漂亮呢。”
我伸手拿咖啡。
“医生,您的手在颤抖呢,没事吧?”
“那不是里香,不可能有这种事。”
“这样的话我就通报政府当局让他们来调查。住处我也知道,我可以这么做吧。”
“……”
“医生,我不想喝这种便宜的威士忌,能喝那个白兰地吗?”正树指着橱柜说。
“想喝什么自己拿吧。”
正树拿出三瓶白兰地,两瓶放入自己的包中,另一瓶直接叼在嘴里,对着瓶口喝。
“最近我的生活连酒都喝不起了。”
“不好意思,我约诊的时间到了。”
“打扰您了吗?既然您不告诉我原本是天狗的里香为何变成猪的话,那我就回去了。”
“别再说什么天狗、猪的这种话!”我的声音不禁大了起来。
“哈哈哈,您是反对歧视吗?真不愧是身为知识分子的医生呢。”
“给我回去。”
“这可办不到,您若不告诉我将天狗变成猪的魔法,我是不会走的。”
“我哪知道这种事。”
正树一只脚抬在桌上,身体凑向前。
“喂,你可别小看我。”
我对他们没有任何偏见,所以才会不顾周遭的反对和朋美结婚。说他们的智商低,只不过是那些没有教养的人所灌输的观念。我们跟他们之间除了外表之外没有任何不同。然而,即使生物学上的解释是这样,但偏见这种观念根本不需要有科学根据或合理的说明,就像传染力强的病毒一样,一旦蔓延出去就难以根除。
自从妻子朋美死去,家里只剩我和年幼的里香后,我的身体很快就垮了。说我“血液遭到污染”,反对我和朋美结婚的那些亲戚,我根本不奢望他们会给予帮助。
我的老朋友中有对夫妻一直没有孩子,那两人对人类很尊重,经济方面也很宽裕。
当然,那对夫妻也跟我一样对他们没有偏见。如果是歧视主义者,我就不会把宝贝女儿托付给他们,而且他们也不会接受里香。
他们说里香原本的模样就可以。可是当时的我开始对逐渐改变的社会感到惶恐。升学、就业、结婚等,社会上所有状况都对他们的歧视日益明显。
考虑到里香的将来,我决定动手术。这是我的医生生涯当中,唯一进行过的一次变脸手术,而我也坚信在当今的世道中,当时的决定并没有错。自此之后,我再也没见过里香。
“为了里香的将来,希望你能当作什么都没看到。”我握住正树的手恳求说。
“该怎么办呢?这得要看医生怎么做了。”正树话中意有所指,“毕竟通报当局,我也一文钱都拿不到。”
“钱是吗?”
“看诚意了,毕竟我们又不是不认识。只不过目前的时势本来就苦不堪言,而我们天狗又和你们不一样,没有任何资源,如果能支援我就是帮大忙了。”
那次之后,正树每次来家里都会厚脸皮地跟我要钱。可是说也奇怪,我竟然开始期待他的到来。
因为正树过来时,一定会提到里香目前的生活状况。从他的角度来看那是一种威胁,表示他会盯着里香不放,但我却能通过他得知长久以来见不到面的女儿的近况。把里香送给人家当养女时,我已经下定决心不会再见她。里香已经死了,我以这样的想法活到现在。正树的存在对这样的我而言,宛如一扇小窗,能够窥看到女儿现在的模样。
被搜查本部赶出来的老子。没有工作的老子。
大家都在嘲笑老子。把老子当没用的废物看。
老子进到署里的资料室。
二十七年前的随机杀人事件。被害者以及口罩男的名字。
未解决刑事案件。时效。
关于当时的搜查资料,老子反复读了好多遍。
一群白痴刑警。让犯人溜走了。
找到被害者的照片。
悄悄收进口袋里。
进到电脑室。
口罩男的事情始终挥之不去。
老子看着照片。
还是很想见到真人。
想象中的口罩男的脸闪过眼前。
再也忍不下去了。
两居室的脏乱的公寓。隔壁房传来孩子的声音。渗透到墙壁里,生活环境的臭味。老子和女人面对面坐着。
忘记换袜子了,老子很在意自己的脚臭。
女人是口罩男的前妻。
“和那个人分开之后,就再也没见过他了。”
不想去回忆的表情。
“那人还住在家里吗?”
还在,但他不见老子。老子很想见见口罩男。
女人很疲劳,打工结束所以很累。对人生也感到筋疲力尽。
女人泡了速溶咖啡。一边喝咖啡一边说话的前妻。
一边喝着那个黑色饮料,老子一边侧耳细听。
“我和第一任丈夫离婚后就去酒店上班,那人是店里的客人。他被公司的同事带来酒店,看起来很认真上进,事实上也的确如此。女人似乎都不靠近他,而公司同事也是为了捉弄他才带他来的。我对他稍微温柔一点似乎让他有所误会……之后就变成一个人来店里,我们很快就发生了关系。虽然觉得这人很奇怪,但我因为一个人带孩子也烦了,这个人刚好可以托付终身。”
资产家的富家公子迷上带着拖油瓶的酒店小姐,原来如此。
“刑警先生应该也了解为什么说他很奇怪吧。”
不了解。老子还没见到口罩男。
“店里的女孩子也都觉得他很恶心。”
恶心。啊,实在好想见口罩男。
女人突然站起来,把窗户打开。
喂,为什么打开窗户?又不热。臭吗?老子的脚臭吗?
你也是犬女吗?老子下意识握紧拳头。
“可以吗?”女人拿出香烟。
原来要抽烟啊,老子松了口气。
“因为他家很有钱,所以我老被说是贪图他们家的财产,他们家对我有孩子的事似乎也很不高兴。由于那人之前的相亲全都连战连败,担心再这么下去结不了婚,所以我们总算还是结了婚。不过,若说我完全不觊觎他们家的财产也是骗人的。”
你一开始的目的就只有这个吧。
“可是虽说家大业大,但钱包全都握在那个臭老太婆手里,那人对自己的母亲唯唯诺诺,我也不是省油的灯,所以每天都争吵不休。原本想忍到那老太婆归西,但因为女儿的那件事就离开家了。”
口罩男与这个女人的女儿。婚后很快就出生的女儿。
然而却发生伤害事件。被口罩男打伤的女儿,至今仍在住院中。
“就是说啊,女儿住院到现在他一句话也没说,愣在那里像是别人家的事情一样。现在是由我娘家的母亲和我轮流到医院照顾她。因为那件事的关系,害我女儿变成那样,但那个老太婆还一直怪罪是我的教育方式有问题。别开玩笑了!”
女人很愤怒。老子表情认真地听着。
“明明答应我要付女儿的医药费和儿子的学费,但那个吝啬的家如果不打电话催,就不会汇钱进来。”
果然是个强势的婆婆。
门开了。
“我回来了。”穿制服的初中生站在那里。
“他是我儿子。”
眼神凶狠,态度嚣张的小鬼。
“离婚时说要负担全部的学费,我就赌气让大儿子进私立学校就读。”
这制服果然是私立学校的。令人不爽的制服。
“刑警先生,那个人做了什么吗?”
中华新京拉面店,老板用围裙擦了擦手,走到老子面前。
光头的拉面老板,身材微胖,可能是拉面吃太多了吧,他太太很担心,时不时瞄向这里。
老子说出来意,拉面老板的表情终于安心下来。
拉面店老板一边看着天花板,一边回想着以前的事。男人点点头。想到了吧,那快说啊,关于口罩男的回忆。老子想了解口罩男的事情,再小的事也不打紧。
“嗯嗯,他啊,我想起来了,就是被随机杀人魔伤害的那个人吧。是的是的,我当然记得。事件发生在小学四年级的时候吧。被伤成那样的他真的很可怜,事件发生以前这孩子明明很开朗,但那次之后整个人都变了,变得很阴沉。他渐渐都不出门,被伤成那副德行会变成这样也是无可厚非。刚开始大家出于同情都对他很好,但毕竟是小孩子吧,后来开始有人捉弄他,逐渐演变成被霸凌的状况。可能和个性阴沉也有关系。他曾经跟我抱怨过‘我什么坏事都没做,为什么会搞得这么惨?’上了初中后也成为霸凌的对象。”
“女朋友?没有没有。别说女朋友了,在学校跳民族舞蹈时都没有女生愿意跟他牵手,远足坐巴士时,也没有人愿意坐他旁边的位子,在教室里大家也都无视于他的存在。说他很恶心,其实并没有什么特别的原因,只是因为大家都这么做,自己也跟着加入了霸凌的行列。谁叫他每天都臭着脸来上学,而且还戴口罩。那人果然是被随机杀人魔伤害之后才变得这么奇怪的,因为之前都会跟我们一起开开心心地打棒球。”
一本正经的大叔出现在老子面前,恭敬地递名片给老子。额头上冒着些许汗滴,太阳穴上的黑痣长着一根长毛。看起来像是认真严谨地穿衣服和走路的公司职员。可是这种家伙会性骚扰,会在电车中偷摸女高中生。
“对,他曾是我的职员。该说是有点怕生呢还是个性阴沉,反正他就是不适合跑业务,所以一直待在内勤。结果他也是同期人员中最慢熬出头的,而且以他的个性,要管理一个团队也很困难。”
“听到他这样伤害自己的女儿时我相当惊讶,毕竟他的个性很稳重。征兆吗?唔,这我就不知道了。”
“有没有特别的印象吗?倒也没有。啊,有了有了,我跟同期社员参加尾牙时是坐在他旁边,偶然巧合地聊到希特勒的话题,他突然话多了起来。听说他房间里满满都是关于第三帝国的书,那可能也是单纯的流言,但这部分也是大家对他退避三舍的原因之一。是的,是刻意避开他的,尤其是女孩子,她们说他很恶心。我觉得他很可怜,但想必也是外表的关系吧。他几乎一整天都戴着口罩。虽然其他人都说不是因为外表才疏远他,但那都只是场面话。”
我一直很担心那对母女,可是解放战线的日比野没有再来告诉我关于那两人的消息。既然我已经拒绝协助他们,我也知道他不可能理会我的请求,但每次电话铃声响起,我仍不禁期待是对方打来的。
偶然在中央公园看到那对母女被带出来,正是这个时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