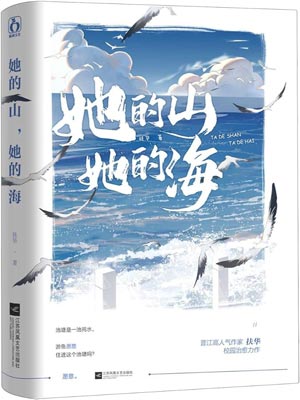松本清张提示您:看后求收藏(350中文350zw.com),接着再看更方便。
白根谦吉把手提包拉近身边,从中取出一个相当厚的横式信封,介绍说这是他这个外行人拍的拙劣照片,说着递给畑中。
都是四寸大小的照片,共六张。第一张是公墓全景,位于山坡上的墓地如梯田般层层排列,松林与杂树林环绕四周,远处有白色的山。翻到背面一看,有白根写的说明:“福冈县苅田町公墓全景”。
接着是一尊御影石材质的低矮墓碑。有一层台阶,碑前虽然放着线香与烛台,但墓碑看起来古旧泛黑、斑斑驳驳。尚不及观察这些,“释正心童子之墓”这一行浅刻字迹已映入眼帘。由于石碑老化,刻字逐渐变浅,多处模糊难辨。还有一部分像弃置山中的石头一样,长满了地衣青苔。能看出白根拍照时煞费苦心,才终于成功重现了镶刻字的阴影浮凸。照片背后写着:“释正心童子之墓。高七十公分,台座三十公分”。
下一张是墓碑背面。没有任何文字,风化得很严重,简直像表面遭人削过一般。这大概是多年乏人照料、任其荒废的结果。
第四张是墓碑侧面,是刻字的特写镜头。这一张也成功地拍出了凹凸分明的字迹。
殁于明治四十三年(一九一〇)八月二日
再看背后,注解为:“东侧。宽十二公分”。第五张是“西侧”,没有任何刻字。
最后一张是从正面拍摄的香炉。这个比墓碑更模糊,御影石已全面风化,还缺了一角。翻到背面,却不见白根注解,看来香炉似乎不需注明。
“这个就是宗玄寺住持信上所说,引发谣传的那个释正心童子的墓碑吗?”
畑中把六张照片摊在桌上说。
“是的。根据道听途说,滞居小仓时期的森鸥外,曾与在他家扮演‘婢女阿元’的木村元生下一个私生子。”
畑中并不惊讶。
因为看着白根拍的“释正心童子之墓”照片,宗玄寺的山田真圆在信上所写的“(那个谣传)恐怕会颠覆尊台所写的《小仓的鸥外》”那句话骤然浮现,畑中已经想象到那是什么了。同时,他发现山田真圆也是相信“谣传所言不虚”的众人之一。
会如此推测,是因为山田住持并未透露更多,且言外之意似乎在暗示即便畑中再访今井,他也无可奉告。如果住持不相信这个“谣传”,应该会当成笑话坦然告之。之所以语焉不详地刻意回避,还质疑他的文章,说什么会推翻他那篇曾提及“婢女阿元”的《小仓的鸥外》中的论点,这一切都是因为住持相信私生子的说法是真的。
“那么,今井、行桥,抑或苅田、小仓一带,至今仍流传着那个谣传吗?”畑中又拿起一根烟问道。
“我只是个旅人,无法调查到那么深入的地步。不过,山田住持既然在信上那么写,我想至今应该还有这种说法吧。”
“那你又是怎么想的?”
“这个嘛……我算是半信半疑吧。”
“半信半疑?那……你还抱着一半的怀疑喽?无论做文章、评论还是什么事,都讲究实证主义的你,居然会对这种毫无根据的谣传半信半疑,这太奇怪了吧。”
畑中郑重地看着白根。
“我就知道您会这么说。”
畑中的视线移向那张拍着石塔侧面的照片。
“殁于明治四十三年八月二日。没有出生年月日。”
“墓碑上通常不刻生年。不过,既然是‘童子’,年纪应该顶多只有两岁吧。”
“也没有刻俗名吗?”
“俗名,和立碑者之名通常都刻在墓碑背面。不过您也看到照片了,墓碑背面已风化剥离,一个字都不剩了。”
“说得也是。”
畑中定睛看着照片,咕哝着“真奇怪”。
“哪里奇怪?”
“如果墓碑背面风化剥落了,怎么还能清楚辨认出‘释正心童子’这行隶书的字迹?”
“您果然敏锐。”
“怎么了?”
“不,正如您所言,背面并不是自然风化造成的剥离,是人为的。”
“人为的?你是说有人故意把字磨掉了?”
畑中惊愕之下抬眼一看,只见白根表情复杂,手指伸进长发里一通乱抓。
“光看我拍的照片可能不够清晰,如果实际用肉眼近距离观看,就能断定那绝对是被磨掉的。而且不是石匠的手法,是外行人拿锤子或铁锤胡乱敲毁的,所以看起来凹凸不平。再经过将近九十年的岁月侵蚀,才会看起来像是风化造成的。”
“释正心童子的俗名与建坟者之名是被故意毁掉的?”
“可以这么说。”
“为什么?”
“可能是有人基于某种立场,不想留下那些刻字吧。”
有人故意把墓碑上的刻字铲除,那不就等于,除了夭折幼童的法号之外,墓碑上的所有痕迹都被清除了吗?
畑中掏出一根烟叼在嘴上,但半晌未点火。接着又拿下烟,用夹烟的手抚摸着下巴。
“白根老弟,你相信那个谣传吗?释正心童子是鸥外滞居小仓时期与阿元生的孩子?”畑中把打火机凑近香烟问道。
“我不相信谣传,除非说得我心服口服。所谓的道听途说,我一概不听。”
“你所谓的心服口服,是要根据什么线索呢?”
“当然还是鸥外的《小仓日记》。”
“你是指鸥外用纸贴覆的那段描述阿元夫婿是望族友石定太郎的文字吗?”
“全书只有那一处出现了那么大规模的删除。最终版的其他部分和之前的版本并无差异。”
“那么,除了那段诡异的删除之外,你还有什么别的发现吗?”
“明治三十三年四月十五日,记载着‘阿元自产婆家归来’。这天,鸥外解雇了老婢阿幸。”
“那是因为那个老婢生性贪婪,连东家的白米和蔬菜都偷,被解雇也是理所当然。”畑中翻开笔记本说。那里写着他从《小仓日记》摘录的备忘录。
“就算是这样,看起来也好像是鸥外迫不及待地想赶在阿元产下女婴从产婆家回来之前把老婢撵走。”
“听起来你话中有话,好像在暗示,如果把阿元接回家,老婢就会成为碍眼的电灯泡。”
“有些迹象让人不得不这么怀疑。明治三十二年九月一日的日记上记载着:‘马夫睡在马店,睡在家里的只有余与婢,因此不得不同时雇用二婢。’可是,无论是谁,都没能待上太久,唯一留下来的就只有大婢阿元。住在隔壁的房东宇佐美家,也不再让女佣过来陪伴过夜。明治三十三年一月二十三日,由于产期已近的阿元要另去他处,所以‘雇用婢平野雅,略有姿色’,但也很快就辞退了。因此,有段时间睡在家里的只有鸥外与阿元,直到雇用了老婢阿幸为止。”
畑中看着笔记本上的摘要,默默抽着烟。
“因此,阿幸才有这个借口向鸥外告状,说阿元与马夫私通。但她真正怀疑的其实是主人与阿元的关系吧。阿幸是个四处帮佣、经验丰富的女人,对这方面十分敏感,猜疑想必非常犀利。我认为鸥外先生是怕这名老婢泄密才将之解雇的。”
“我看是你太多心了吧。”
“或许吧……不过,也许不是。像鸥外这样的大人物,既然写日记,就应该会预感到日后可能会被公开出版,因此写时必然会顾及个人颜面。他的《小仓日记》不就还特地请人重新誉写过吗?!”
“照你这样说,岂不是不可能从《小仓日记》中找到正确线索了?”
“那倒也不至于。即便经过修饰,毕竟鸥外写得很诚实。”
“此话怎讲?”
“老婢阿幸走后,家中只剩阿元一人。从东京带来的马夫田中寅吉依旧睡在马店,睡在家里的只有主人与阿元。看了这个,很难不勾起想象,一般人应该不会把这种事写进日记里。”
“那你是怎么想的?你认为鸥外与阿元的确发生过关系吗?”
畑中死死地盯着白根的眼睛。
这时畑中想起阿元产下女婴,回到鸥外位于锻冶町的家之后,阿元的家人便摆出亲戚的姿态,陆续登门造访过夜的相关记载。那简直就像在暗示另有隐情。
白根没有直接回答这个问题。
“虽然《鸥外全集》中提及旧婢阿元之夫友石定太郎家世背景的部分都被删除了,但在‘后记’中注明了那部分文字的内容。既已用和纸刷满糨糊牢牢贴上,又怎么能看得到底下的文字?难道有后人撕下和纸,看到了底下的文字吗?”白根说着,回视畑中。
畑中听到这话,不禁语塞。阅读“后记”时,他也曾产生过和白根相同的疑问,但当时他认为,既是一流的出版物,想必是用了什么高超技术加以复原。
这时,只见白根从皮包里取出一张纸。
“这是《小仓日记》关于明治三十三年十一月三十日那段记载的影印本,是我从现收藏此日记的鸥外纪念馆影印下来的。”
畑中凝视着交到他手上的影印本。
紧接在“三十日,旧婢阿元来访,谓曰”下面,隐约可见七行文字。虽然只是隐约透出,但尚可辨识。“初至夫家,从曾根停车场……”以下的一百三十九个墨字隐约可见,因为贴在上面的和纸极薄。
日记的墨字是请他人誉写的楷书体。
“这真是太意外了。”畑中认真地打量着说,“果然还是得看实物才知道,没想到竟然用这么薄的和纸。”
“我看到这个时也大感意外。我原本也以为是用最厚的和纸遮蔽,好让人无法辩读底下的文字。”
“鸥外为何没有用厚纸呢?”
“日记中还有好几处用薄纸贴覆的部分,这似乎是鸥外的癖好。不过其他部分都很小块,算不上删除。像这样一口气删除长达七行,而且是用这么透明的薄纸遮盖曾经信赖的旧婢阿元所说的谎话,似乎有欠慎重,不像鸥外的作风。不说别的,就因为此文被收录在《全集》的‘后记’中,不就引起工藤德三郎、畑中先生,还有我的怀疑了吗?”
“你的怀疑?”
“是的。不只阿元谎称与望族友石定太郎结婚的部分,阿元离开鸥外宅后的下落,也勾起了我的好奇心。”
“你去查了?”
“通过某人调查过,但那毕竟是明治末期的事,花了我不少时间,这也正是我迟迟未跟您联络的原因。”
“那……你查出来了?”
“隐约知道一点轮廓了。久保忠造在明治二十三年三月与阿传成婚,明治三十五年十月离婚。阿传殁于三十七年三月。然后,忠造又于明治三十九年四月与阿传的妹妹阿元成婚,明治四十年八月与阿元离婚。”白根垂眼看着记事本说道。
“等一下!听起来简直像笔糊涂账,能不能写成年表给我看?”白根点点头,当场拿起铅笔写下——
〇(明治)二十三年三月,久保忠造与阿传成婚。
〇三十五年十月,与阿传离婚。
〇三十七年三月,阿传死亡。
〇三十九年四月,忠造与阿元成婚。
〇四十年八月,与阿元离婚。
“嗯,这下我总算弄清楚了。”
畑中一动不动地凝视着“年表”。
“《小仓日记》明治三十三年十一月二十四日记载——‘婢女阿元辞去’,鸥外还咏过一句:‘勤快的下女出嫁,蜗居家中避寒。’一个星期以后,即同月三十日,阿元来访鸥外,谎报已与松江村区的望族子弟友石定太郎成婚。然而,她实际上究竟去了哪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