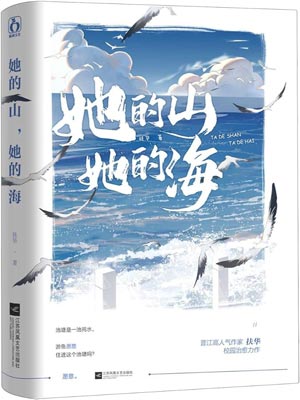安东尼·赫洛维兹提示您:看后求收藏(350中文350zw.com),接着再看更方便。
“他没出现。”
“也许他根本就不打算赴约。他最后一次介入你们的生活是破窗而入,从你们的保险箱里偷走了五十英镑和一件首饰。这个时候,我就觉得他的行为极其不同寻常了。他不仅知道选择哪扇窗户,而且居然弄到了钥匙,那是您的妻子几个月前丢失的,那时他还没有来到这个国家。他更感兴趣的不是谋杀,而是钱财,因为他竟然半夜三更地站在这座房子里,这不是很有意思吗?他完全可以上楼把你们俩杀死在床上——”
“我醒过来,听见了他的动静。”
“确实如此,卡斯泰尔夫人。可是,那个时候,他已经打开了保险箱。顺便说一句,我猜想,您和卡斯泰尔先生睡在不同的房间,是吗?”
卡斯泰尔的脸红了。“我不明白我们的家事跟这个案子有什么关系。”
“但是您没有否认这点。很好,让我们继续讲述这位古怪的有点儿优柔寡断的夜盗者。他逃到了伯蒙齐的一家私人旅馆。这时,事情出现了令人想不到的转折。我们一无所知的第二位谋杀者追上了奇兰·奥多纳胡——我们依然只能假定是他——把他刺死了,不仅拿走了他的钱,还拿走了能证明他身份的所有东西,只漏掉了一个香烟盒。但它本身说明不了问题,因为上面印的姓名首写字母是WM。”
“您说这些是什么意思,福尔摩斯先生?”凯瑟琳·卡斯泰尔问。
“我只是向您说明,卡斯泰尔夫人,从一开始我就觉得这番讲述完全不合逻辑——除非您换一个前提:到这个家里来的不是奇兰·奥多纳胡,他想要联系的不是您的丈夫。”
“可是这太荒唐了。他给了我丈夫那张纸条。”
“却没有在教堂露面。如果我们站在这位神秘访客的位置上,或许会有所帮助。他想跟这个家里的某个成员私下见面,但是事情没有这么简单。除了您和您的丈夫,以及那位姐姐,还有各种各样的仆人——柯比夫妇、埃尔西和帮厨的小杂工帕特里克。他一开始远远地注视,最后带着一张纸条走近房子,纸条上的字写得很大,没有折叠,也没有信封。显然,他的意图不可能是上门投递。或许,很有可能的是,他希望看见想要联系的那个人,然后把纸条举起来,让对方从吃早饭的那个房间的窗口看见上面的字,不需要摁门铃,不需要冒险让纸条落到别人手里。只有他俩知道,他们可以过后私下商量事情。然而,不幸的是,在那个男人有机会达到目的之前,卡斯泰尔先生就出人意外地提早回家了。那么他是怎么做的呢?他把纸条高高举起,然后递给了卡斯泰尔先生。他知道吃早饭的房间里有人正注视着他,现在他的意思完全变了。‘来找我,’他仿佛在说,‘不然我就把我知道的一切告诉卡斯泰尔先生。我会在教堂跟他见面。我会在我喜欢的任何地方跟他见面。你阻止不了我。’当然,他没有到教堂去赴约。他不需要那么做。警告一下就够了。”
“可是,如果他不想跟我说话,那么想跟谁说话呢?”卡斯泰尔问。
“当时谁在吃早饭的房间里?”
“我的妻子。”卡斯泰尔皱起眉头,似乎急于改变话题,“如果这个人不是奇兰·奥多纳胡,那么是谁呢?”他问。
“这个问题的答案非常简单,卡斯泰尔先生。他是比尔·麦科帕兰,平克顿律师事务所的侦探。考虑一下吧。我们知道麦科帕兰先生在波士顿的枪战中受了伤,而我们在旅馆房间发现的那个人右边脸颊上有一道很新的伤疤。我们还知道麦科帕兰跟他的雇主康奈利斯·斯蒂尔曼闹翻了,因为斯蒂尔曼拒绝支付他觉得应得的那么多钱。于是他怀恨在心。还有他的名字——比尔,我可以想象,这是威廉的简称,而我们发现的香烟盒上的缩写字母是——”
“WM。”我插嘴道。
“完全正确,华生。现在事情就完全清楚了。让我们从考虑奇兰·奥多纳胡的命运开始吧。首先,关于这个年轻人,我们知道什么?卡斯泰尔先生,您的叙述出奇地全面,为此我要向您表示感谢。您告诉我们,罗尔克和奇兰·奥多纳胡是双胞胎,奇兰个头较小。他们在胳膊上文着对方的姓名首写字母,证明他们之间非同寻常的亲密关系。奇兰的脸上没有胡子,沉默寡言。他戴一顶低顶圆帽,可以想象,使人很难看清他的脸庞。我们知道他身材纤瘦,只有他能够挤进通到河里的阴沟,成功逃跑。但是,特别引起我注意的是您提到的一个细节——圆帽帮的土匪们都住在南海角简陋肮脏的出租房里,只有奇兰一个人享受独立的房间。我从一开始就纳闷儿为什么会这样。
“当然,考虑到我刚才摆出来的各种证据,答案一目了然。我很高兴地告诉你们,我得到了凯特琳·奥多纳胡夫人的证实,她仍然住在都柏林的萨克维尔街,开一家洗衣店。是这样的。在一八六五年的春天,她生下的不是一对孪生兄弟,而是一对孪生兄妹。奇兰·奥多纳胡是个女孩。”
此言一出,顿时一片绝对的沉默。冬日的静寂挤进房间,就连壁炉里的火苗,刚才还在欢快地跳跃,现在也似乎屏住了呼吸。
“一个女孩?”卡斯泰尔惊讶地看着福尔摩斯,嘴唇上浮现出一种病态的笑容,“率领一伙土匪?”
“一个女孩要在这样的环境里生存,就必须隐瞒自己的身份。”福尔摩斯回答,“其实是她的哥哥罗尔克在领导匪帮。所有的证据都指向这个结论。不可能有别的选择。”
“这个女孩在哪里呢?”
“很简单,卡斯泰尔先生。您跟她结婚了。”
我看见凯瑟琳·卡斯泰尔的脸色变得煞白,但她没有说话。坐在她旁边的卡斯泰尔突然身体僵硬。他们俩使我想起了在寒鸦巷看见的那些蜡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