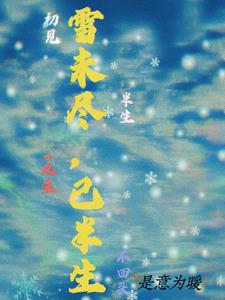戴维·格兰提示您:看后求收藏(350中文350zw.com),接着再看更方便。
但是,随着庭审的进行,反对他的证据越来越多,这位后现代主义者也越发朝着实证主义者的方向发展,绝望地试图说明检方证据链中的漏洞。巴拉指出,没有人曾看到他绑架、杀害谢尼亚夫斯基,或者将其沉入水中。“我要说,我从没见过达留什,在场也没有任何一个证人能确认我认识他。”巴拉说。他对检方提出控诉,说他们随意抽取自己个人生活的若干片段,然后拼凑成了一个故事,与实情相去甚远。检察官们在进行“神话创作”,或者用巴拉辩护律师的话说,在编造“小说情节”。被告认为,警方和媒体都被耸人听闻的故事,而非事实真相吸引住了。(举几个该案报道的标题为例:比小说更离奇的真相和他写下了自己的谋杀。)
巴拉浸润于后现代主义的“作者之死”观念已久,即作者在对文学作品含义的理解上并没有超过其他任何人的权威。然而,当检方对陪审团提出《杀人犯》中某些可能与犯罪相关的细节时,巴拉却抗议说,他的小说被误读了。他坚持认为,玛丽之死只是“哲学之死”的象征。他还试图诉诸作者的权威。他后来对我说:“这本书是我写的!我知道自己是什么意思。”
9月初,案件交由陪审团审理。巴拉没有出席。但是,在一份声明中,他说:“我相信法庭会做出正确的选择,撤销对我的一切指控。”之前被提升为警监的弗罗布莱夫斯基来到了法庭,希望亲耳听到判决。“就算你很确定真相是什么,但总归不能确定其他人会不会和你想的一样。”他告诉我。
最后,法官和陪审员回到了审判庭。巴拉的母亲焦急地等待着。她之前从来没看过《杀人狂》,里面有一段是克里斯幻想强奸母亲。“我开始看了,不太好读,”她告诉我,“如果是别人写的,我可能就不读了吧,但我是他妈妈。”巴拉的父亲第一次现身了。他之前读过这本小说,虽然有些部分不太明白,但还是认为这是一部重要的文学作品。“你看十遍,二十遍,每次都有新收获。”他说。在给父亲的那一本上,巴拉给父母写了一句话:“谢谢你们……宽恕我所有的罪孽。”
霍延斯卡法官宣读判决书时,巴拉笔直地站着,一动不动。然后是清晰无误的一个词:“有罪”。
弗洛茨拉夫监狱是一座灰色的煤渣砖建筑,像是苏联时代的遗物。我把访客通行证从墙上的一个小洞里递进去时,一个没有感情的声音命令我去大楼正前方,结实的大门摇晃着打开了,里面走出了一名在阳光下眨着眼睛的警卫。搜过身后,我穿过了几个阴冷的房间,最后到了一个小会客室,里面放着陈旧的桌椅。波兰监狱的条件是出了名地糟糕。由于人满为患,一间囚室往往要住七名犯人。2004年,弗洛茨拉夫监狱的犯人发起了为期三天的绝食运动,抗议过分拥挤、伙食低劣、医疗不足的问题。监狱暴力是另一个问题:有人告诉我,就在我去几天前,一名访客就被囚犯捅死了。
会客室角落里有一位消瘦英俊的男人,戴着金丝眼镜,身穿一件海军蓝的画家工作服,外面套着一件“威斯康星大学”字样的T恤衫。他捧着一本书,看上去像是美国留学生。我过了一会儿才认出来,原来他就是克里斯蒂安·巴拉。“很高兴你能过来,”他跟我握着手说道,把我带去了一张桌子边上,“这是个大粪坑,就跟卡夫卡写的一样。”他的英语清晰可辨,但口音很重,“s”的发音像是“z”。
坐下后,他靠在桌边,我能看到他面颊深陷,还有黑眼圈,鬈发根根竖立,好像他用手指焦虑地抓过一样。“我被判了二十五年有期徒刑,就因为写了一本书——一本书!”他说道。“太荒谬了。真是胡说八道。请原谅我的用语,但事实就是如此。你看,我写了一本小说,一本疯狂的小说。它低俗吗?是的。淫秽吗?是的。下流吗?是的。冒犯吗?是的。这是我有意为之的。这是一部刺激性的作品,”他停了一下寻找例子,接着说,“比方说,我写过,克里斯从一个女人的子宫里生出来,都要比我——”他感觉自己说走嘴了。“我是说,叙述者,比叙述者跟她做爱容易。你看,这是有意要冒犯,”他继续说道,“我的经历跟萨曼·鲁西迪是一样的。”
说话的时候,他把手头的书放到了桌子上。那是一本破破烂烂的《杀人狂》。我问到巴拉不利于他的证据——比如手机和电话卡——时,他变得闪烁其词,有时甚至有阴谋论的味道。“电话卡不是我的,”他说,“有人要陷害我。我还不知道是谁,但外面有人要害我。”他把手放在我的手上:“你看不到他们在干什么吗?他们编造了这个现实,逼迫我住进里面。”
他说已经提出了上诉,引述了审判中逻辑和事实上的不一致。例如,一名验尸官说谢尼亚夫斯基是淹死的,另一人却说是被勒死的。法官本人也承认,她不确定罪犯只有巴拉一人,抑或另有共犯。
我问到他《杀人狂》的情况时,巴拉来了精神,回答直接而详细。“这本书的宗旨不是我本人的宗旨,”他说,“我不是反女性主义者。我不是沙文主义者。我并非冷酷无情。在很多地方,克里斯是我的反英雄。”他多次指着我的便签本说“把这段记下来”或者“这是重点”。他看着我做笔记时,不无惊奇地说:“你看到这件事有多么疯狂了吗?我编造了一件从未发生的谋杀。”在他的这本《杀人狂》上,几乎每页都划了线或做了旁注。后来,他给我看了几张纸,上面画着复杂的图表,说明了他在文学上受了谁的影响。显然,他在监狱里对这本书更加沉迷了。“我有时会给狱友们朗读几页。”他说。
审判中有一个问题从来没有被回答。这个悬而未决的问题是:一个人为什么要先杀人,然后把它写进小说里,好方便别人来抓他呢?在《罪与罚》中,拉斯科利尼科夫提出,最精明的罪犯也会犯错误,因为他“在犯罪时会体验到某种意志和理性的失败……一种浮夸的、幼稚的轻率会取而代之,而此时思考和审慎正是最必要的”。然而,《杀人狂》是在谋杀发生三年后出版的。如果犯人真的是巴拉,那么起因就不是“意志和理性的失败”,反而是意志和理性的过剩。
有些观察者推测,巴拉会不会想要被抓住,这样至少能从负担中解脱出来。在《杀人狂》中,克里斯提到了“负罪感”,还有脱下“沉默的白色手套”的愿望。虽然巴拉坚持说自己是无辜的,但将这本小说理解为自白倒也并无不可。弗罗布莱夫斯基和当局相信,巴拉最想要的就是不朽的文学地位,于是认为不能分开来看他的罪行与写作。庭审过程中,谢尼亚夫斯基的遗孀恳求媒体不要把巴拉描绘成艺术家而非杀人凶手。由于巴拉被捕,《杀人狂》在波兰一炮走红,几乎每家书店都有卖。
“新版要出来了,会有一篇后记,主题是庭审和事件的来龙去脉,”巴拉激动地对我说,“其他国家也有兴趣出版。”翻着自己那本书,他补充道:“这样的书还从来没有过。”
在我们谈话的过程中,他对“完美犯罪”意兴阑珊,倒是对“完美故事”兴趣浓厚。按照他的界定,他迈过了文学前辈划定的审美、现实与道德边界。“我跟你说,我正在写《杀人狂》的续作,”他说的时候,眼睛都在放光,“书名叫De Liryk,”他又重复了几遍,“这是一个双关语,既有歌词(lyrics)的意思,也有谵妄(delirium)的意思。”
他解释说,他在被捕前就已经开始动笔了,但警方把他的电脑没收了,书稿都在里面。(他正在尝试把文件取回来。)当局告诉我,他们在电脑里发现的证据表明,巴拉正在收集斯塔莎新男友哈利的信息。“单身,三十四岁,八岁丧母,”巴拉写道,“似乎在铁路公司上班,可能是火车司机,但不确定。”弗罗布莱夫斯基和当局怀疑,哈利可能是巴拉的下一个目标。巴拉知道哈利上网络聊天室后,就在网站下面用假名发了一条信息:“不好意思,我想找哈利。有霍伊诺夫的人认识他吗?”
巴拉告诉我,他希望在上诉法院判决出来后完成第二部小说。实际上,我和他谈话几周后,上诉法院推翻了原判,让许多人感到不敢置信。虽然上诉委员会认为巴拉和凶手之前存在着“不容置疑的关联”,但得出的结论是,“逻辑证据链”仍然存在漏洞,例如验尸官互相矛盾的证词,这些漏洞需要解决。委员会拒绝释放巴拉出狱,但要求重审。
巴拉坚持认为,不管发生什么,他都会完成De Liryk。他看了看警卫,好像害怕他们听见似的,然后身体前倾,小声对我说:“这本书会更加惊世骇俗。”
2008年2月
2008年12月,重审结果出来了。他再次被判有罪。他目前正在服刑,刑期二十五年。
<a id="zhu1" href="#zw1">[1]</a>小说《化身博士》中的角色,海德先生与杰基尔博士同为一体,只是善恶截然二分。
<a id="zhu2" href="#zw2">[2]</a>Amok,即他的小说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