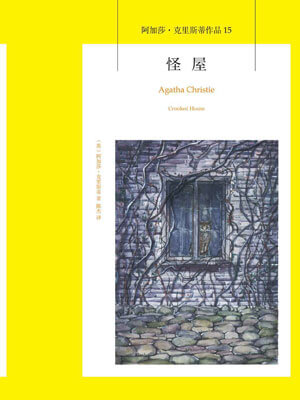我们所知的世界末日 The End of the World as We Know It (第2/5页)
斯蒂芬·金等提示您:看后求收藏(350中文350zw.com),接着再看更方便。
总共有十九个人。每个人都有名字。
温德姆的妻子有阅读的习惯,她喜欢在床上看书。入睡前,她总是会把书签夹在书里做个标记。那个书签是温德姆送给她的生日礼物,卡纸质地,顶上系着根丝带,书签上的图案是一道彩虹高挂在白皑皑的雪山上。上面还写着“记得微笑,上帝爱你”。
温德姆不怎么喜欢读书,可如果他在世界末日到来那天拿起妻子的那本书,一定会发现开头几页特别有趣。开篇第一章,上帝就带着所有正统基督徒上了天堂。其中包括正在驾驶汽车、火车与飞机的正统基督徒,这导致无数人的死亡与个人财产的重大损失。倘若温德姆读过这本书的话,他就会想起在他UPS货运车的保险杠上有张贴纸,上面写着“警告,一旦提被<a id="ch1-back" href="#ch1"></a>,该车即为无人驾驶。”每当看见这张贴纸,温德姆就会想象出汽车相撞,飞机从空中坠落,病人被丢在手术台上的场景——基本和他妻子书中的描写完全吻合。
温德姆每周日都会去教堂,但他不禁好奇那不信基督的亿万人会有什么下场——不管是自主选择不信,还是恰好出生在诸如印度尼西亚那样的地方。他好奇地想,要是他们在过马路时恰好从那些汽车前经过,或是在灌溉草坪时将被飞机砸中会怎么样?
但我说的是:
在世界末日到来的那一天,温德姆没能立刻理解发生了什么事。闹钟一如往常地响起,他开始了新一天的例行忙碌。在客用浴室里冲个澡,把咖啡灌进热水瓶,在水槽边上吃完早饭(这次是一块稍稍有些变质的巧克力甜甜圈)。然后返回卧室,与妻子道别。
“祝你今天过得愉快。”他像平常一样靠近她,稍微晃了她一下,力度恰到好处,不至于将她唤醒,而只是让她微微挪一下身子。十六年来,除去联邦法定假日和夏季的两周带薪假期之外,这项仪式天天上演,温德姆早就驾轻就熟,几乎每次都能让她身体略微挪动,但又不会被完全叫醒。
因此,当妻子今天早上并没有把脸埋进枕头里,对他报以微笑时,他大感意外,甚至可以说是震惊。此外还有个表现也极不正常——她没有说“嗯”。她既没有带着懵懂的睡意发出最常听见的那声懒洋洋的“嗯”,也没有像偶尔感冒头痛鼻子不通气时发出无精打采的“嗯”。
什么“嗯”都没有。
空调停止工作了。温德姆第一次注意到屋里有种古怪的气味——那是种若有似无的有机臭味,像洒出来的牛奶,又像是没洗过的臭脚。
温德姆站在黑暗中,开始生出一种不祥的预感。跟他在莫妮卡家客厅里看着客机一遍又一遍撞向世贸中心时的恐惧感截然不同,那次是一种强大但基本无关个人的恐惧——之所以说“基本”无关个人,是因为温德姆的三表哥就在位于世贸大楼的康托·菲茨杰拉德公司工作(那位表亲名叫克里斯,温德姆每年都要在通讯录里翻找他的地址,寄出庆祝他救世主生辰的贺卡)。而今天,当妻子没说“嗯”时,温德姆的不祥预感则是强大而绝对关乎个人的。
温德姆关切地弯下身子摸了摸妻子的脸,手感像是在抚摸一个蜡人,冷冰冰的毫无生气。就在这时——确切说来就是这一瞬间——温德姆意识到世界末日降临了。
之后发生的一切都只是细节而已。
除了疯狂的科学家与腐败的官僚之外,末世故事中的角色通常分成三类。第一类是强韧的个人主义者。你们知道这种人,他们自力更生,独来独往,会使枪炮,还擅长给产妇接生。
在故事最后,他们总是走在重建西方文明的康庄大道上,而且这些人通常聪明过人,不会重蹈覆辙。
第二类是后末日的强盗恶棍。这类角色通常成群结伙地跟那些坚韧不拔的幸存者对着干。如果你碰巧爱看末日题材的电影,那你那对这些人的喜好一定不会感到陌生——身穿紧身衣,留着朋克发型,骑着改装得极具个性的座驾。与前一类幸存者不同,这群恶徒对从前错误的发展道路格外青睐,而且对强奸和掠夺机会的大量涌现也并不反感。
第三类虽然跟前两类比起来属于小众,但也相当常见,他们就是悲观的愤世之徒。这些人与温德姆一样,酗酒;与温德姆不同的是,凡事都让他们提不起兴趣来。当然,温德姆也有自己的痛苦,但绝不是因为无聊。
我们还是得谈谈那些细节:
温德姆发现至亲死去时的反应同大部分人如出一辙。他拿起电话,拨打了911。电话线路似乎出了故障,另一边无人接听。温德姆深吸一口气,走进厨房,试着用分机拨打。还是没打通。
当然,既然是世界末日,所有负责接电话的人也都死了。不妨这么想象一下,他们都被潮水卷走了。在1960年,巴基斯坦的一场暴风雨真的夺走了三千人的生命(当然,并不是说应该接听温德姆911求救电话的接线员真的被淹死了,也不管这些人后来究竟遇到了什么——重要的是,在这一刻还活着的人,下一刻也许就会死去,和温德姆的妻子一样)。
温德姆放弃了电话。
他跑回卧室,笨手笨脚地给妻子做了大约十五分钟的人工呼吸与心脏复苏,然后他再次放弃。他走进女儿的卧室(她十二岁,名叫埃伦),看到女儿仰面躺在床上,嘴巴微张。他俯下身子摇晃她,打算告诉她刚刚发生了极为可怕的意外——她的母亲死了,结果发现同样可怕的事情也发生在了女儿身上。
温德姆吓坏了。
他跑出大门,朝阳此刻刚将地平线染红。他邻居的自动灌溉机还开着,喷头在一片死寂中发出嘶鸣。当他跑过草坪时,被水雾喷了个正着,脸就像被一只冰冷的手扇了一巴掌。接着,冻得瑟瑟发抖的他站在邻居家的门廊前,用双拳捶打房门,大声朝门里尖叫。
过了一会儿——他也不知道是多久,一股可怕的平静感袭上心头。周围一片死寂,只有发出沙沙声响的洒水器将一缕缕水雾喷进街灯投下的光圈里。
然后,在他眼前出现了一幕场景,那堪称真正的先见之明。他看见郊外的房舍无声地在眼前延展,看见了无声无息的卧室,在床单底下蜷缩着几个同样无声无息的沉眠者,再不会醒来。
温德姆咽了口唾沫。
接着,他做了一件二十分钟之前无法想象的事。他弯下腰,从砖头缝里拿出备用钥匙,进了邻居的家。
邻居养的猫从他身旁走过,哀怨地喵了两声。温德姆正躬下身子想抱起它,就又闻到了那股气味——模糊而难闻的有机臭气。但这回既不像发臭的牛奶,也不像臭脚,而是更加难闻。像是脏污的尿布,或是堵塞的马桶。
温德姆直起身,不再管猫。“赫姆?”他喊道,“罗宾?”
没有人回答。
温德姆走进房门拿起电话,拨打了911。他听铃声在听筒里响了很久,之后他没心思好好挂电话,直接把听筒扔到地上。他在这座死寂的房子里四处走动,把一盏盏灯打开。在主卧门前,他迟疑地停下脚步。那股恶臭在这里愈发浓烈。现在不会弄错了,那就是屎尿混在一起的臭味,是全身肌肉突然全部放松而造成的排泄物。当他再次开口说话时,压低了声音:“赫姆?罗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