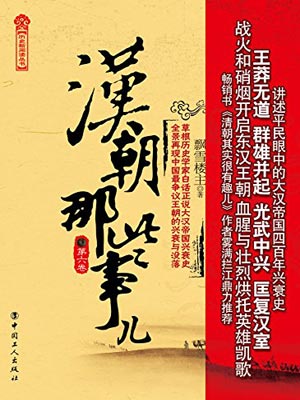塞巴斯蒂安·巴里提示您:看后求收藏(350中文350zw.com),接着再看更方便。
恋爱的时候,我们曾经亲吻过。那仿佛是在很久以前,我们坐在圣史蒂芬公园少得可怜的椅子上,爱尔兰的春天,阳光忽隐忽现,让人捉摸不定,散发出淡淡的热力,我们在阳光下手牵着手,或者躲在露天音乐台的阴影里,缠绵在彼此的怀抱中。我喜欢他的亲吻,他的吻像一朵温暖的花儿在我胸中慢慢舒卷绽放。到了夏天,炽烈的亲吻如烈焰烘烤,我的乳房和他的胸脯贴在一起,汗水涔涔,这种时候可不怎么美妙。
我们到这儿来的头几个星期,寒风彻骨,窗外传来湖水的巨大喧响,屋内黑暗中掺杂着脏兮兮的枪灰色,与我们有一墙之隔的汉娜和她丈夫正发出阵阵鼾声,我们本可以拼命进入对方的身体,就像是地球上第一对男女情人,然而,当我们紧挨着躺在床上时,却恍若隔世,仿佛是哪个神父给我们下了咒语。
现在,我真真切切地感觉到,那其实也是恐惧的一部分,虽然我们漂泊在美国,正被人四处搜寻——这是再清楚不过的,虽然塔格说他确信我们有可能已经摆脱了追踪,但我们已经不再像以前那样情投意合,反而是这种突然从天而降的亲密关系,让我们莫名其妙地产生了隔膜。
就我而言,我本可以不那么提心吊胆,因为他是个亲切和善的高个子男人,但是,刚到美国的那段时间,他突然变得冷漠、疏离,心思不知道落在什么地方。在某种意义上,那也许是因为他正大难临头,已经感觉到死亡一点点逼近,至少自己的生活发生了巨大变化。他甚至没有时间联系上远在科克的母亲,我觉得,每当他想到自己的母亲孤身一人待在家乡,对他现在的情况一无所知,对他突然消失的原因也完全蒙在鼓里时,他一定很不好受。
我想,他心里一定很不是滋味,正是在这时候,我开始暗自琢磨——他会不会认为,我们俩之所以陷入眼下的困境,在某种程度上是我造成了这一切,更确切地说,我开始思量,这到底是不是我的过错。因为我是土生土长的维克罗郡人,他在维克罗的所作所为人们便格外留意。一般来说,警察通常在远离自己居住区域的地方执行公务,这样就不会有人知道他们的名字,而塔格却因我而暴露了身份。全是由于我的缘故,他的名字才为人所知,一辆卡车经过维克罗,车上的人荷枪实弹,也许一路上还嘻嘻哈哈,毫无疑问,那是一群肆无忌惮、没心没肺的家伙,然后发生了伏击,当地的几个小伙子当场丧命,看来“黑棕团”早有防备——这山野风景里可怕的一幕,因我而加上了一个名字,一切全都是我的错,都是我的错。关于这些,我一句话也没有对塔格说过,但我还是摆脱不了干系。正是这种事情夹在我们中间,让我们生分起来,就像是一团乱七八糟缠绞在一起的毛线,剪不断,理还乱,虽然我们表面上亲密无间,躺在窄窄的床上,迫不得已只能臂膀紧挨着臂膀,他的身体散发出的热力,在冰冷刺骨的房间里,对我有着难以抗拒的诱惑,他的红胡子从面部微微隆起,看上去就像是都柏林基督教大教堂里的墓碑上雕刻的人物。
甚至在我写下这些文字的时候,心里一直充满了热望,期盼回到那个时间,那个地点,我会转向他,紧紧地抱住他,让他明白,只要一个简单的动作,一切隔阂都会冰消雪融,作为有血有肉的人,这大概是我们最起码能够做的。房间里一团漆黑,只需要点起一根蜡烛就能驱散黑暗。我多么希望,我多么希望我们没有浪费掉那么多厮守在一起的宝贵时光。
不过,我们的情绪慢慢松弛了下来。其中的缘由大概是,虽然塔格靠干苦力挣来的为数不多的几美元外加几美分,比起“黑棕团”的薪水确实少得很,但在我看来非常了不起,因为这证明了我们能在这里继续生活下去的能力,并且开始带给我们一种安全感。父亲通过邮箱编号给我寄来一封信,把莫德和她的未婚夫马修举行婚礼期间发生的大大小小的事情告诉了我,这对我来说如获至宝,虽然他的讲述只有寥寥几句,就像例行公事——这是他的一贯风格,但我的想象力填补了所有的空白。在想象中,我仿佛看见莫德脸上浮现出很少一见的微笑。我希望她时常把笑容挂在脸上,因为她的微笑很美丽——如果说难得一见的话,我希望她和她的丈夫相亲相爱,虽然我不知道这有多大可能,我对一切都茫然无知。
那封信我读了一遍又一遍,每次心里都自然会泛起一阵忧伤,一阵思乡的痛楚,当然,还有一丝妒忌。
不过,当芝加哥从冬季和春季的寒冷中摆脱出来时,塔格和我总算开始变得融洽。
“我要说,我喜欢这个地方。”他说,“我喜欢这里。”
生活在美国当然要来得轻松自如一些,因为我们在这里没有任何历史。慢慢地,我意识到,作为父亲的女儿,不知不觉中我从小女孩长成一个年轻姑娘,这是一段充满痛苦的历程,一件事情总是和另一件事情相抵触——我父亲对国王深怀敬意,而塔格的父亲则是爱尔兰志愿军的成员,二者水火不容;威利投入那场战争和他的死是多么强烈的反差,甚至连维克罗郡的生活和都柏林的生活也格格不入,还有大巴从乡下运到城里来的白色石楠花,最终也会变成黑色,形成一个鲜明的对比,枯萎黯淡的小小花朵诉说着时间的脚步,时间的飞逝。就连我自己来到世间也是一个矛盾,母亲在给予我生命的同时自己却离开了人世。
那时候,我还不知道,在这里,在美国,有哪些东西是相互抵触的。
塔格不单单开始喜欢芝加哥,甚至在他提到“家”这个字眼儿的时候,他开始用来指我们住的那间破破烂烂的木屋,而不是指科克或者爱尔兰,现在我们已经有能力给表姐一点儿钱,勉强充作房租。慢慢地,我们接触到的周围事物开始延伸开去,形成了一个自己的王国——躁动不安的密歇根湖仿佛自以为是大海,城市里层层叠叠的建筑也开始成为我们谈话中和梦境里的地标。
接着,发生了一件不寻常的事情。
一个星期日的早晨,我们俩并排躺在床上,脑子里一片空白,完全出于人类纯粹的本能,我们不约而同地转向对方,开始温柔地亲吻,继而变得狂热,就像两只猛醒的野兽,不知不觉中,我们死命抓住对方,扯掉身上的衣服,紧紧地搂抱在一起,然后他进入了我的身体,这一切就像深冬季节从湖面上突然一路席卷而来的暴风雨,我们是那么幸福,那么快乐,那么年轻,在湖边那间小木屋里,任何人都能领略的诗歌最终让我们恣意领受了一遍,两个人完全融化为一体。在那一刻,我们俩都深深地明白,不管怎样,我们都会结婚,这根本不需要说一个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