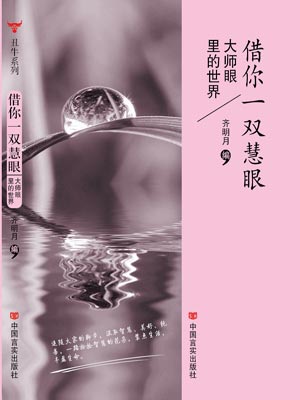塞巴斯蒂安·巴里提示您:看后求收藏(350中文350zw.com),接着再看更方便。
事实是我不应该在加纳。我应该在斯莱戈的家里,给我的孩子们整理东西。我应该在那里,哪怕就在边上站着,也随时可以提供帮助,随时可以给出建议。那是一位父亲可以做到的。然而,我却潜伏在非洲,像个衰弱的传教士,既没有教堂也没有什么目标,只不过是一再推迟我离开的时间。怪不得当我告诉奥科先生我打算再留一段时间的时候,他充满善意的脸上露出了奇怪的神色。我为什么要这样?我在这儿的工作已经结束了。
而我的心,我的心碎了。我知道的。近四年来,我带着这颗破碎的心勉力生活,但是情况只是越来越糟,好像引擎上有个故障疏于修理,结果损耗了其他部件。现在我必须尝试修理它,必须这样。我必须回顾发生的一切,找到它破碎的地方,请求美好事物之神让我愈合,如果可能的话。将它写在已不复存在的黄金海岸工程桥梁公司的会议记录本上。那么回到爱尔兰的这名男子将会变成更好的人,一个健全的人。这是我现在的祈祷。
一个小时前,我起身从桌前走到阳台。微风穿过沉闷的院子,如果我没记错的话,这阵风代表着雨之将至。
我内心一片纯白,但那也无济于事。
因为我无法隐藏自己脸上的颜色。
说起诚实。路易斯·阿姆斯特朗<a id="jz_5_1" href="#jzyy_1_5"><sup>[5]</sup></a>去年正好就在阿克拉,在各地的自由之锅正搅起风浪的时候,从天堂降落,像是黑人之神,在奥苏举办了大型露天演唱会。书包嘴大叔笑呀,笑呀。汤姆会多么想要在现场啊,我是说我弟弟汤姆。汤姆·奎伊可能当时就在那里,我得去问问他。白人主妇们为那纯粹的音乐而欢笑,几步之外,黑人主妇们也同样为此而欢笑。
我第一次和曼说话之后的那个周末,我开着奥斯汀汽车驶回斯莱戈的家,并向我母亲说起了曼。我记得我后悔“抄小道”穿过泥泞的高地,记得当时那带着尘土味和烤面包气味的皮质座椅。也说了这有多么绝望,多么不可能。
“怎么不带她去看放映展出,你这个傻瓜。”母亲说。她在客厅里,正把感兴趣的剪贴画报粘贴到剪贴本上。那小房间一片黑暗,但不知怎的,你能在那片奇特的黑暗中洞悉一切,好像我们暂时变成了猫。这种黑是我想起母亲的时候会想到的黑。或许当我写下这些话的时候,她正坐在那里。
“什么?”我说。
“放映展出,杰克。”
“妈呀,现在没有放映展出了,那是‘电影’。”
我母亲并不老,但是她故作老成。她有一头美丽的红发。她生我的时候才十七岁。汤姆在斯莱戈的电影院工作,所以她很清楚我在说什么。可能她更稀罕旧东西。
“仁慈的时间啊,我还知道什么现代的东西?但是我告诉你,杰克,当她开始了解你,一切都会迎刃而解。”
“她绝不可能和我这样的人去看电影。”我说。
于是我又去等她了,就像是真正的大盗迪克·特平<a id="jz_6_1" href="#jzyy_1_6"><sup>[6]</sup></a>。
她看到我的时候甚至没有和我说话,只是向着我发出了类似于“嗨”的声音,仿佛是在说,我早知道你会在这儿。她可曾期待过?无论如何,她神情明媚雀跃,她见到我似乎挺开心的。我的心一下子沉到我锃亮的黑靴子里,随后又一下子蹿到我头顶的软毡帽里。那一刻,我对地质学或是工程学毫无兴趣——一周之前它们还是我生命的两大激情所在。那一刻,对我而言只有“曼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