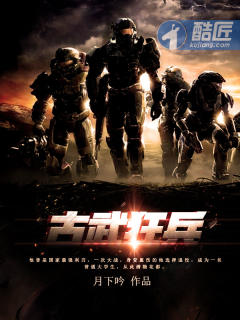塞巴斯蒂安·巴里提示您:看后求收藏(350中文350zw.com),接着再看更方便。
那些四通八达的小路多么沉静,所有的石头都那么安详,每个坟墓旁边的地上都插着我熟悉的铁牌号码,那是跟水泥小庙里妥善保存的坟墓登记簿完全对应的。一缕夕阳的余晖还挂在沿途可怜巴巴的小树林里。小树在死亡的阴影里成长,都肢体孱弱,营养不良。我竖起大衣的领子,紧紧裹着自己,然后不假思索,几乎处在与现实脱节的状态,向围绕着小庙的一圈坟墓走去。
然后他又长时间地坐在那里,沉默不语。他坐了那么久,好像已经成了屋里的一个病人!好像他就住在这儿,除此之外无家可归,无所事事,无依无靠。
那里依然竖立着古老的尖顶,残败的柱子,模糊的人像,可能是某个久远年代里希腊的战斗英雄,小庙的铁门在笨重的门轴上半开着,露出令我无限向往的灯光,里面的火炉和油灯都铭记着爸爸。我不顾一切地,或者说,不计后果地,朝着灯光迈进,我的心鼓励我继续前行,再次占据那温暖的一角,与爸爸团聚,重叙旧语。我从半开的门走了进去。
“是的,是的。”
屋里的一切都原封未动,勾起我对爸爸的温馨回忆。他的水壶还放在东倒西歪的炉台上,旁边的炉栅里炭火忽明忽灭,他的搪瓷杯,还有我的杯子,都还放在桌上,那几本登记簿和账簿都摞得整整齐齐,还有条砖地面上磨损的足迹。我睁大了眼睛,仰起脸,坚定不移地相信他就会来到我的身边,安慰我,指引我,一切从头。
“是吗?”
突然,我的背心被猛推了一把。在爸爸的避风港里发生这种事令我大吃一惊。我向前趔趄了几步,差点摔倒,所有内脏都闪了一下才保持住平衡。我转过身,看到门里站着一个陌生人。他过紧的毛衣几乎撑不住里面的大肚皮,看上去像店里卖的那种膨胀出壳的大面包。他的两腮却古怪地凹陷,显得他表情苛刻,眉毛又长又密,像上了年纪的人,虽然他也就五十多岁。不对,不对,这个人我认识,当然认识。他是接任爸爸职位的裘·布莱迪。
“麦科纳提夫人,你对创伤记忆进行了非常形象的描述。”
冈特神父不是告诉过我吗?我怎么都当成耳旁风了?老天爷,我怎么跑到这儿来了?你可能说我是得了失心疯,已经误入歧途了。他可没有一点求婚者的风度,一点边都不沾。他看起来气势汹汹,两眼通红,这我在爸爸葬礼上就注意到了。我一直忙着怀念爸爸,竟然把冈特神父替他提亲的事全抛在脑后了。
“我记得黯黑的场景,失魂落魄,嘈杂的声音,仿佛教堂里悬挂的黑暗恐怖的画。不知为什么,上面什么都看不清。”
都说女人善妒,可能吧,但男人怀恨在心的时候更可怕。恐惧从冰凉的地砖上升起,钻进我的心里,我魂飞魄散,以至于,我不得不承认——请原谅一个老人对恐惧真实的回忆——我控制不住尿了裤子。虽然小庙里光线微弱,我想他还是看到了,不知是否为这个原因,他发出了一声狞笑。他的笑声仿佛是狗在害怕被踩到时发出的嚎叫,一种警告性的笑声,如果笑声可以用来发出警告的话。记得是在哪本书里读到过,人类的笑起源于远古时代的龇牙咧嘴和鬼脸怪相?当时的情景就是证明。
然而他不知为什么又垂头丧气了,一副心灰意冷的样子,像地底下的鼹鼠。我之所以回答他的问题,主要是为了让他振作起来。
他说:“你还不要我。”这是他有生以来第一次跟我说话,真不可思议,“自甘堕落,你个没信仰的野丫头。”
我笑望着他。他像一个小男孩撞了膝盖,这会儿疼痛逐渐消退。疼痛与泪水之后的欢快。
他向我紧逼过来,不知有什么企图。在他的动作里,我看到一种原始的、抑制不住的暴力天性。死寂的坟场,静默的小庙,昏黑的傍晚,我身上藏着什么他迫切想要的东西。他一步步向我逼近,他的心念似乎也一步步发生变化,脸上的人性消失殆尽,某种在人类拥有灵魂之前的黑暗私欲在他眼里蠢蠢欲动。从当前这个遥远的距离回头看去,他当时就是要把我置于死地,个中情由我却不得而知。我一不小心误入了裘·布莱迪的人生故事,至于他跟冈特神父策划了什么惊天动地的事业,我一无所知。我原本是来找爸爸的,不想却碰到了我的刽子手。忽然,我使出浑身的力气大叫起来。咆哮!
“利特里姆是个很怪的字眼。不知原意是什么?估计是爱尔兰语。当然,肯定是的。”
他身后竟然尾随着一个人。这么僻静的地方还有另外一个人,真是不幸中的万幸。这时裘·布莱迪已经迈出了最后一步,来到了我的面前,紧紧扣住我细瘦的脖子,好像这是他在这个世界上最渴望的事,迫不及待地把我拽向他的身边。我下意识地注意到,他在裤子的拉链处一阵乱翻,好像要把里面什么东西释放出来,老天啊,救救我,我才十六岁,虽然略解风情,但也就止于走在街上被小伙子们招惹,对男女之事我还不甚了了。在斯莱戈同龄的女孩子中间,我可能是最天真的一个,我这会儿边写边清楚地记得,我的第一个念头是他可能会从裤子里掏出一支枪,或一把匕首,这么想也不足为奇,因为就在这里,我曾亲身经历了短兵相接,枪林弹雨。
“就是。”
好像应验了我的心思,裘·布莱迪身后新来的那个人真的端着一杆枪,像一根沉重的大扁担,他照着裘·布莱迪的后脑一记横扫,动作仿佛是挥起镰刀披荆斩棘。我站在那儿,吓得魂不附体,但还是把一切都看在眼里。第一下没能扫倒裘·布莱迪,他只是跪在了地上,我瞬间瞥见他两腿之间挺硬的下体,令人作呕,我赶紧用双手蒙上了眼睛。新来的人用他的枪又扫了一次。我不禁自问,这个地方是不是人人有枪,还是我命里注定跟枪有缘?